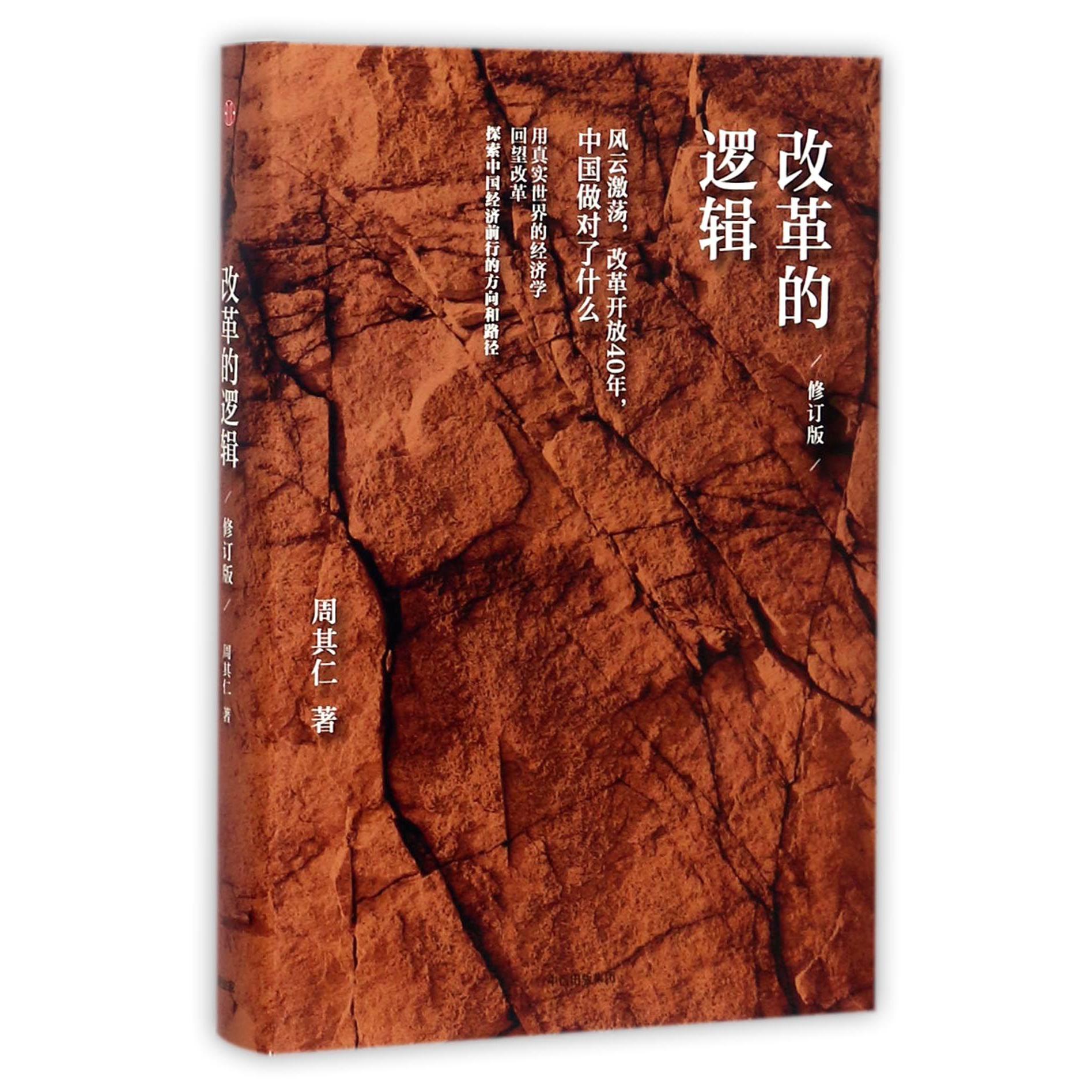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7.70
折扣购买: 改革的逻辑(修订版)(精)
ISBN: 978750867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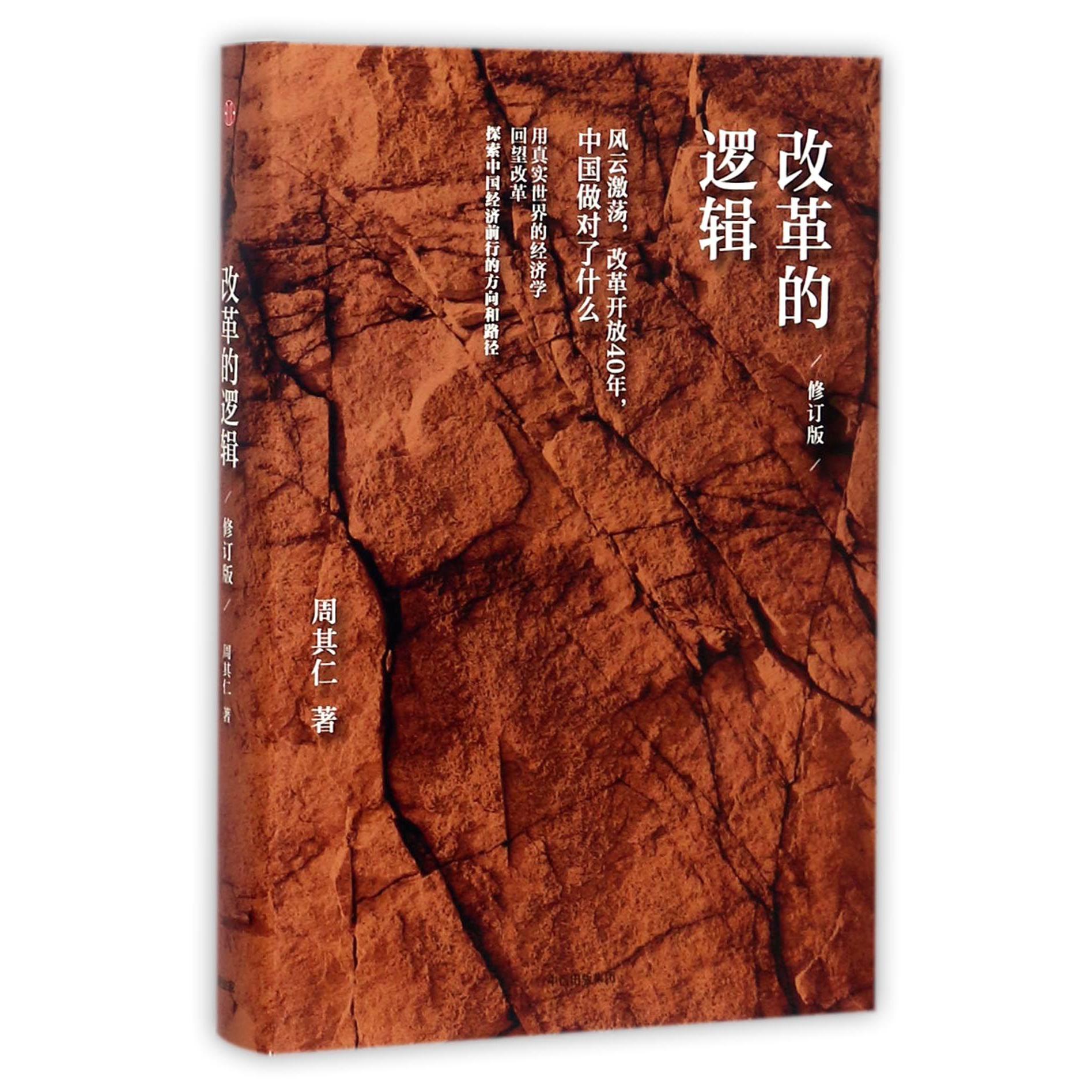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教授,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2011年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公共经济学家等荣誉。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 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 :“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 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 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 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 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当时已经97岁高龄 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 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 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 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 《再论中国的前途》。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 然是盗版的:开本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 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 样。 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张五常这样介绍 :“科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 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 篇大作,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 (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 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 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假设 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 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却立 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 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 前,我没有机会上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毕 业生,经历了3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 乡。等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苏联 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10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 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 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10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旋涡中 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 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 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 本、美国、欧洲各国、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现代 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 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 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 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 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 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 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 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 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 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 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 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 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 了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 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 ,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 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 、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对真实世界的认知 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 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 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 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 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 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 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 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 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 剧的第一幕。 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 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 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 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 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 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 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包产到户出现在 “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 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 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 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 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 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 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 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 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 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 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 显然,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 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 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 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