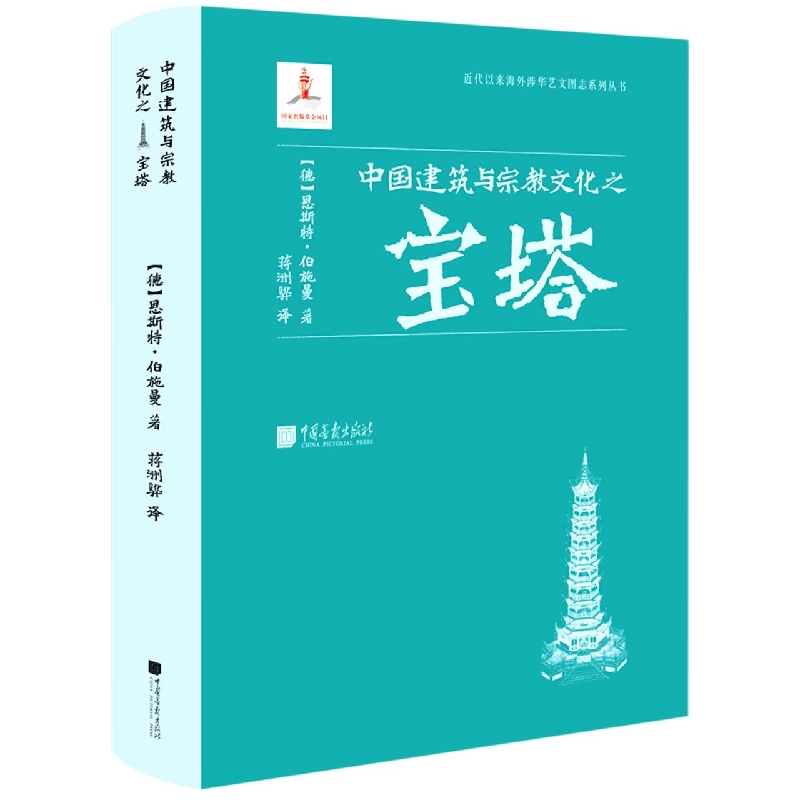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画报
原售价: 198.00
折扣价: 114.90
折扣购买: 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之宝塔
ISBN: 97875146207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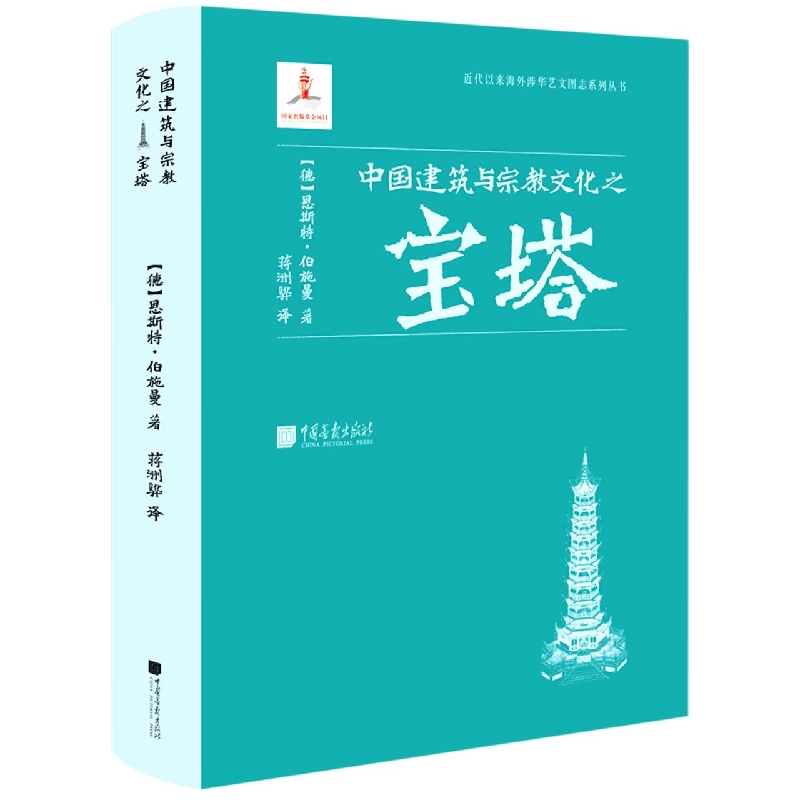
恩斯特?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学术界公认的第一位全面考察中国古建筑、第一位以现代科学方法记录中国古建筑、第一位以学术著作形式向西方社会传递中国古建筑与文化内涵、第一位在西方社会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奔走呼号的德国建筑学家,中国建筑摄影鼻祖。出版有《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之普陀山》《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之宝塔》《中国建筑与宗教文化之祠堂》《中国建筑》《中国建筑与风景》《中国建筑陶艺》等。 蒋洲骅,毕业于德国哥廷根大学跨文化日耳曼德语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江苏省常熟理工学院德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与德语教学法,对中德文化交流及中国传统文化在德国的传播多有涉猎。
第六节? 琉璃塔 琉璃塔与我们介绍过的其他宝塔主要的不同在于造塔的材料,区别于我们至此介绍过的砖塔、石塔和铁塔;另一方面则是它与众不同的外形,它和墓塔一样有较早的起源,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继续发展成不同式样,因此有一部分琉璃塔会在下一节“墓塔”中详细介绍。同时本节也会介绍琉璃这种材料给整个景观带来的独特效果,包括宝塔结构的巨大变化以及建筑群崭新的布局方式。同时也会简单介绍琉璃塔的变体宝塔,它们外形更为小巧,但同样极富魅力。实际上一些小型的纪念碑也有许多层,形似宝塔,因此将中国的建筑艺术放在佛塔这个较窄的框架下去探讨,似乎能够得到一些新的结论。 大型砖塔只是宝塔灿烂发展历史中的一步,作为大型建筑首先要保证结构的牢固性,另一方面才是材料。只要砖塔外部使用彩色琉璃装饰,整座宝塔就会显得格外富丽壮观,对于高楼来说同样如此。像这样在砖塔外面覆上琉璃的宝塔式样我们简称为琉璃塔,琉璃塔的造型主要是前文介绍的叠层塔或层塔。如果宝塔的形制特点远远超过其用材特点,比如北京的天宁宝塔或者承德的喇嘛塔,这些琉璃塔就会归类在介绍对应形制的章节中。 直到宋朝,中国才开始在建筑上广泛使用琉璃这种材质,但它无疑在唐朝时期就已经开始被当作建筑材料。然而目前我们并不知道任何现存的唐代琉璃建筑,只能通过文学作品看到它们在当时的灿烂形象。在建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中国从宋代初期就在当时的新都城开封府建造的宝塔上大规模地使用了琉璃,963—967 年建造的铁塔(参见图272)以及 977 年建造的繁塔(参见图 67)上都用到了琉璃。后者的琉璃后来因风化和改建而掉落了,也因为它较为突出的级塔造型,我们已将它放在级塔一节中介绍过了。而琉璃塔最为典型和精美的例子,是已经倾塌的南京瓷塔,它建于明初,后期有几座较小的宝塔应该就是仿照它的式样修建的。琉璃塔得到大规模的兴建要到 18 世纪康乾时期,现存的著名琉璃塔也多建于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建造的宝塔中,经过重建或翻新的宝塔比明朝初建时的琉璃要多一些。其中有一些已经在前文中介绍过,比如山西的奉圣寺宝塔(参见图 92)和平阳府宝塔(参见图 49),另一些宝塔我们在本节中会介绍,比如承德园林中的宝塔(参见图 291),它只有一部分覆有琉璃,和它位于南京的榜样形成对比,后文中我们会进行具体分析。 1. 河南开封府铁塔 在宋朝古都开封府的东北角屹立着一座高大的宝塔(参见图 272),它位于古老皇宫的东北方向,作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与远处东南方向城墙上较矮的魁星楼遥相呼应。宝塔所属的佑国寺曾经占地很大,远近闻名,但很早以前就已经仅剩残垣断壁,如今则完全荒殁无踪了。宝塔初建于繁华昌盛的宋初时期,前文讲过的开封相国寺宝塔也是同时期(参见第 62 页)的建筑,仅仅比铁塔晚了十年。两座宝塔都是宋朝皇帝为了显示国力强盛而下令建造的大型建筑。下文提及的铁塔及其寺院的历史来源于河南府志、《中国佛教史迹》以及《鸿雪因缘图记》,而第三部文献显然也有对其他史料的引用,将宝塔的初建时间误写作 1041—1048。以下是我对这些材料整合以后的记述: 这座宝塔全称铁色琉璃宝塔(参见图 272),呈铁褐色,建于宋代乾德年间(963—968),宝塔位于河南甘露寺内,寺院最初建于后晋天福年间(936—942),当时叫等觉禅院。到乾德年间寺院才转移到现在的位置,并更名为甘露寺。同时人们在寺中修建了一座宝塔,这座寺院就以宝塔的名字得名铁塔寺。到元末 1368 年,寺院毁于战火,直至明代洪武十六年(1383)才得以重建。也有史料称这次重建时间为 1395 年。明英宗第二次登基后的天顺时期(1457—1464),寺院更名为现在的佑国寺,而另一处史料记载,寺院直至乾隆治下的 1750 年方才更为现名。在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或三十三年,即 1553 年或1554 年,宝塔历经了一次大规模翻修。到了明末,寺院毁于一场洪水,仅有宝塔留存了下来。清初顺治二年,即公元 1645 年,一位高官募资将寺院重修一新。在乾隆 1750 年御驾亲临之后,寺院又修葺了一次;根据麟庆的文章,最近的一次修缮是在 1831 年。沙畹带回了一些宝塔的照片,其中有一个落款写着建于 1383 年,即寺院被战火毁坏后重建的时间。《鸿雪因缘图记》的作者则误将现存的宝塔当成了初建时的宝塔。根据当地人的口述,洪武年间宝塔经历了一次修缮,他们认为宝塔是宋代的建筑。宝塔外墙浮雕的细节确实与明代风格比较相近,但许多雕像特别是琉璃大佛,肯定是宋朝时期的作品。我们在一些佛像、浮雕和铭文上发现了不同的日期,分别有正德七年(1512)、嘉靖八年(1529)、嘉靖三十二年(1553)、嘉靖三十六年(1557)、万历十八年(1590)、万历四十二年(1614)、乾隆四十年(1775),这些年份都是捐款建塔的时间,其中有一处提到,一位皇子下令建造了四十八尊阿弥陀佛琉璃像。这又回到了饱受争议的宝塔的保存问题上,史料文献中将古塔直接称作铁色琉璃塔,并给出了确切的建造时间。而宝塔几乎不可能在公元 14 世纪遭到毁坏,否则地方志或其他史料中一定会有或至少会有简单的记述,因为其他的修缮和翻新都有文字记录留存。既然文献中找不到重建的信息,那么我们仍将宝塔的初建时间记为 963—967 年。 这座八角宝塔极其修长(参见图 273),而中国人在画作中把这种瘦削高挑表现得更为夸张(参见图 279)。宝塔底层边长为 4 米,边到边的通径长 9.75 米,而两边回廊间的通径则为 10.5 米,塔高约为 48—50 米。喜仁龙估测的高度为 56 米,显然过高了;关野贞测量的 70 米以及徐家汇工艺院模型中的 72 米则更不可能。宝塔底层上方是一层相当厚实的腰檐,看上去十分古朴,上面另有十二层塔身,自下而上高度急剧减小,除第一层外的塔檐均为重檐。从塔檐结构上看,铁塔的形制非常接近叠层塔,一般也确实将它归类于此。 八角形塔身的外墙仅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开有券门,向内通向一个小小的四方形塔室。一到五层的塔檐伸出塔身不远,由两层最简单的石质斗拱支撑,上下两层正对交叠。下层斗拱下方是紧密的窄条木椽构成的塔檐,每条边都有一条略微向下的弧度。六层到十层的塔檐下只有一层斗拱结构支撑,而到了最上方的两层,塔檐则完全略去了斗拱结构。贴紧塔身的塔檐结构使整座宝塔直立的轮廓十分流畅,几乎没有凹凸的弧线。像这样修长且紧凑的宝塔,顶部攒尖一般弧度并不明显,而塔刹也通常为简单的宝珠造型。底层宝塔中有四个 1.7 米见方的小型内室(参见图 274),从正门进入的内室有一个宽仅 70 厘米的狭窄阶梯,一直向上,中间设置了许多半平台。沿着阶梯攀爬,绕着中间六米厚的内塔盘旋而上,周围几乎不见亮光。阶梯由砖和石灰岩制成,经过多年的使用已成黑色,被磨得很亮。陡峭的阶梯隐藏在拐角的后面,通向下一层宝塔。十二层的阶梯尽头是一尊铁佛,再无通向顶层的阶梯。 宝塔的制造工艺极为精湛,砖砌、琉璃和浮雕都十分精美(参见图 275)。塔砖高七厘米,砌得严丝合缝,轮廓清晰,在造型复杂的部分也通过完美的技艺顺利完成了设计的要求。细长券门上方的拱形由打磨成半圆形的砖块砌成,而且表面还雕刻有精细的多层纹饰浮雕。由正门进入的内室高 2.2 米,顶部是八角形尖顶,轮廓清晰。方形内室的转角处设计了悬空的三角形衬石,使内室呈现为一个边长七十厘米的八边形。棱线由平滑的瓷砖砌成,与九层隆起的砖结构紧密相连,塔顶在九层砖结构之上又多加了两层。 宝塔外墙整体覆盖着琉璃和华丽的浮雕(参见图 276),大部分塔身呈现铁褐色,中间有锯齿状的绿色和黄色,甚至有些淡青色和黑色的部分,塔顶则覆盖着明黄色琉璃。墙面由二十至三十五厘米宽、二十厘米高的琉璃砖砌成,每块砖上都有一对佛像壁龛,壁龛上沿儿以双层类似哥特式拱顶收口,基面则饰有佛像、飞天、龙以及其他装饰图案。这些琉璃砖四周是四厘米厚的青砖构成的方形饰带。横饰带上雕有植物枝蔓、卷须以及莲瓣,垂直饰带上每块砖都雕有一个姿态优美的人像,高约二十厘米。两种造型的饰带砖交替出现(参见图 277):一个身着甲胄,手持细棒,置于面前,叫作韦驮天将,是佛的护法神,在佛殿中一般都位居前列;另一个人像身着宽袖长袍,竟然被称作张良,这位汉代的名臣在这里以八仙之一的身份出现,我们很难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很有可能是民众将这位吹笛退兵的张良与善音律的佛等同起来了。旧的琉璃有许多地方都脱落了,其他的部分都保存得非常好。 从《中国佛教史迹》中展示的一幅巨幅照片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苏州和长江下游其他地区及浙江在宋代建造的宝塔相比,铁塔的底层要高大得多。实际上不仅开封附近的郊区常发洪水,开封城内也频发水患,因此当地的土层经屡次冲刷比原来变高了,看上去宝塔好像陷入了黄土中一般。如果对地质层的变化做更详细的研究和实地探查,应该会给公元 967 年的这次土地层变化带来很有趣的启示。宝塔的正门入口仅六十厘米宽,现在的高度仅 1.5 米,地表下面应该埋着通过台阶进入正门的平台,或至少有一个塔基。入口的券门上方是四层叠涩,下方还有一个少见的云状浮雕。整座宝塔的转角处都用砖砌成宽大的圆角,且仅稍微探出墙面少许。砖面上雕着龙、狮等纹饰图案。这种砌砖的工艺与之后才出现的哥特式砖建筑有着令人惊奇的相似性。 宝塔底层正殿的侧面是琉璃砖砌成的佛龛,其中首先是接引佛爷,佛龛正中的基石上立着一尊一米高的佛像(参见图 278),通身覆有黄色和白色琉璃,从佛像身上的服饰线条形制来看,是宋代的风格。在阶梯半平台侧面的墙面上,甚至是阶梯旁边的墙面上,都镶嵌着一些小方砖,上面雕刻着极其精美的佛像和图形,覆有黄色琉璃或黄铜,有些方砖独立分布在不同位置,有些则被砌在一起。 铁塔建造得极为坚固扎实,但同时造型又极为修长冷峻。它属于宝塔建筑艺术中最美也是最完整的实例之一,虽然几经翻修,但仍体现了中国北方宋代宝塔建筑的重要特点。至于中国文人是如何看待及理解这种建筑的,以及如何将佛教思想及中国传统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在宗教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寻求平衡,在原型与映像之间寻求信仰的,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中有一篇文章(参见图 279)或许能给出一些答案,因为他在文章中对这座佛塔的内在意义也作出了阐释。文章的开头写的一些事件与本书前文介绍的宝塔历史有一些重复的地方。 铁塔眺远 乾隆十五年高宗临幸,敕赐今名。独是僻在省城东北隅贡院之后,游踪罕至,香火冷落。岁庚寅,杨海梁先生助捐重修贡院……九月杪亲往查验,顺道过寺,则见塔峙钟残,殿荒僧老。寻径至塔院,仰视十三层,层各一门,其十一层有树倒垂,蔚然苍古。乃开塔门燃炬入,则见塔心中实,磴道盘旋,悉以铁琉璃瓦为之。规制与他塔异矣。振衣而上,登三层,近指贡院。号舍翼张,堂轩鳞次。五层见城内公署市阛,人烟繁庶。七层见城外平野菜畦,谷陇相间,有堤横亘西北,宛宛相属。九层遥望黄河如带,近俯雁字,进退离合,若相离,若相背。余神凝其间,几忘其事。登十二层,天为之宽,地为之阔,目力所及,直接青霭。十三层有铁佛据门,不可登,乃循级而下。至院回视,夕阳在山,落霞森射,琉璃辉映,黝色变金。俄而西山化碧,又闪为紫。归白吾母,闻殿宇难庇风雨,发愿庄严逾岁竟复旧观矣。 德国建筑师恩斯特·伯施曼于1906年,从北京出发,历经四年时间,先后游历了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十几个省,行程数万公里,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专业系统地考察,留下了8000多张照片、2500多张草图、2000多张拓片和1000多页测绘记录。回国以后,他根据这次考察所获的资料,连续出版了多部论述中国建筑的专著。 伯施曼留下的这些带有详细数据的照片、拓片及临摹的图画,成为很多文物古迹少见甚至是唯一的原始资料,为研究它们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依据,并为文物古迹修复、古城复建等工作提供了珍贵的参考数据。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与林徽因等人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都深受伯施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