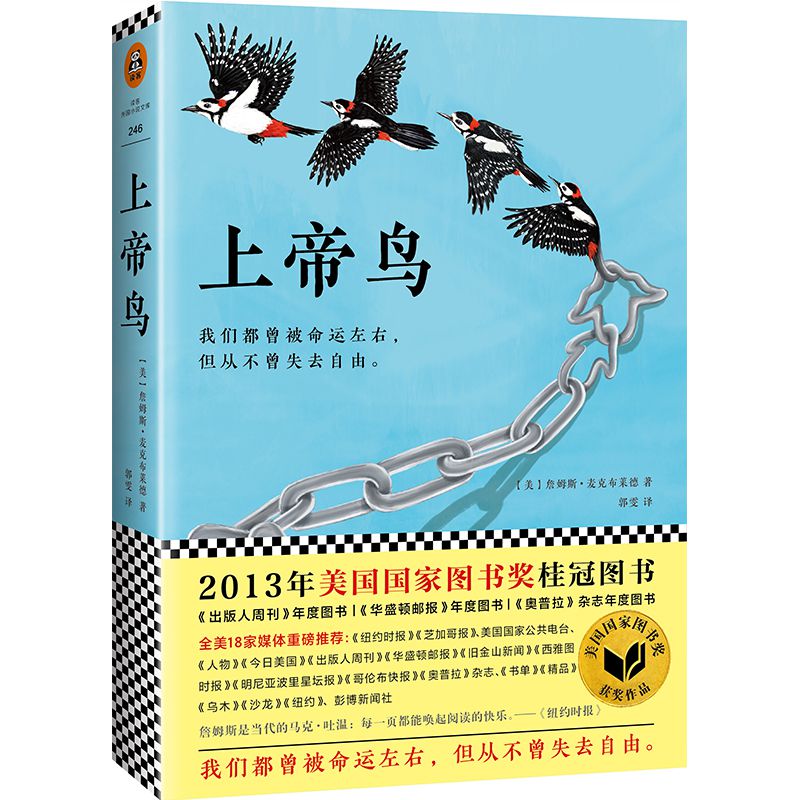
出版社: 文汇出版社
原售价: 52.00
折扣价: 30.20
折扣购买: 上帝鸟
ISBN: 97875496236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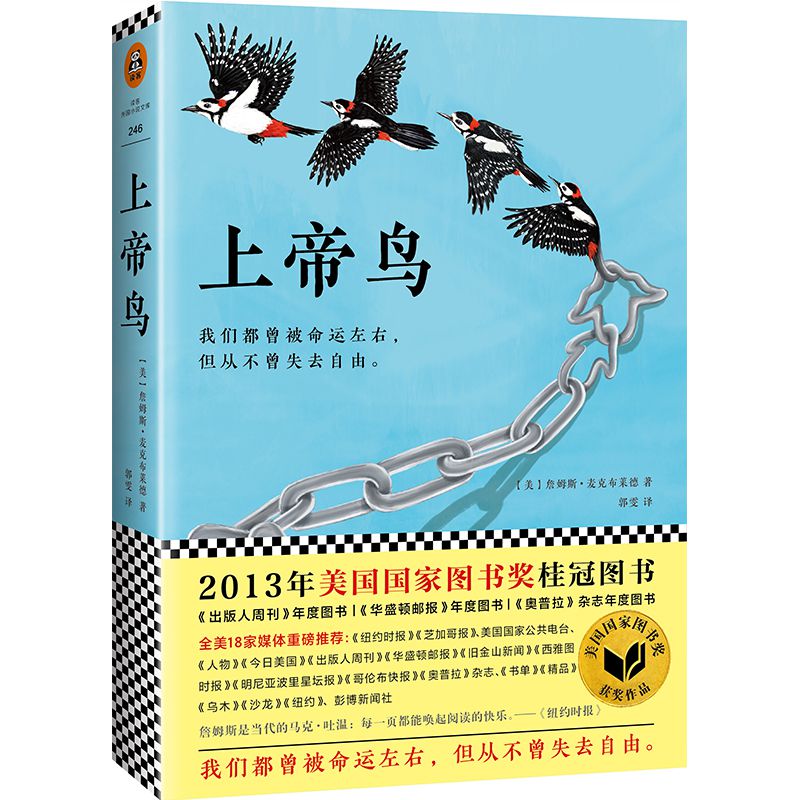
詹姆斯·麦克布莱德(James McBride, 1957—),美国文学大师,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硕士,纽约大学客座作家,拥有数个荣誉博士学位。因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及风趣幽默的叙事风格,被誉为“当代的马克·吐温”。 其代表作《上帝鸟》荣获2013年美国**图书奖,入选《出版人周刊》《华盛顿邮报》和《奥普拉》杂志的年度图书,获得来自《纽约时报》《芝加哥报》、美国公共电台等全美18家媒体的重磅**。《上帝鸟》重述了一段美国历史,展现了美国的过往,情节出人意料、扣人心弦,令人热泪盈眶。 2016年9月22*, 时任美国总统授予詹姆斯“全国人文勋章”, 表彰他的作品以人性化的方式探索了复杂的美洲种族问题,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展现了美国历史的那些动人故事。
《上帝鸟》第二十七章节选:《逃亡》 进*之*的前**,我们装好马车,没搞什么仪式就离开了镇子。上尉递给安妮一封信:“这是给你妈和兄弟姐妹的。按照上帝的意志,过不了多久,我就见到你们啦。”他对我说:“再见了,洋葱头。你打了仗,打得漂亮,一旦你的黑人兄弟重获自由,我就会见到你,要是上帝愿意那样做的话。”我祝他好运,然后一行人便离开了。我登上马车,坐在干*堆底下。沿着马车侧面放着一块木板,底下是覆盖着我的干*,安妮便坐在木板上,而赶车的萨尔曼跟他嫂子,奥利弗的老婆玛莎,坐在车头。 我们出发了,安妮就坐在我的头顶上,辚辚的车轮声中,我听得见她抽泣的声音。过了一阵儿,她停止哭泣,突然说:“等大功告成,你的同胞们会重获自由的,洋葱头。” “是的,他们会的。” “你就可以远走高飞,拿着把提琴,唱着歌儿,完成你的心愿了。大功告成之后,你就可以一辈子到处唱歌了。” 我想对她说,我愿意追随她到任何地方,一辈子为她歌唱。甭管是十四行诗,还是**小曲还是什么歌颂上帝的牛仔小调儿,只要她喜欢就好;只要她开口,我什么歌儿都能学。我想告诉她,我要浪子回头,我要重新做人,我要拿出我的英雄本色。可我却不能,因为我的本色并非英雄好汉。我只是个懦夫,靠撒谎过活。仔细想想,这个谎撒得也并不太坏。身为黑人,你就得对白人笑脸相迎,**如此。你得知道他想要什么、他需要什么,挖空心思讨好他。而他却不必在意你想要什么。他也不管你需要什么,也不管你的感*如何,也懒得关心你是个什么人,因为你跟他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在他眼里,你只是个**,是个物件儿,比如一只狗、一把铁锹或者一匹马。你的需要和**一点儿都不能流露出来,不管你是姑娘还是小伙儿,是娘们儿还是爷们儿,高矮胖瘦,是圆是扁,爱酸还是吃辣,也没人对你知冷知热的。有什么区别呢?在白人看来,没区别,你不过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然而对于你来说,对于你的心来说,这的确是有区别的。一想到这点,我便心酸起来。要是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他那副皮囊也舒服不了。辨不清自己的身份,你就跟一粒豆子一样可怜。不管你外表长成什么样,也好过这样。派克斯维尔镇的西博妮娅让我明白了这一点。我琢磨着,正是在密苏里那会儿,因为眼睁睁看着西博妮娅和妹妹莉比上了绞刑架,我的生活轨道才发生了改变。“做个男子汉!”人家要绞死他们的时候,西博妮娅这样对那个摔倒在绞刑架前的小伙子说。他们让他跟其他人一样浑浑噩噩,把他像破衬衫似的挂在晾衣绳上,可他挺住了。他做到了。他让我想起了老家伙。人家绞死他之前,他的神色不同以往,好像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景象。老家伙脸上永远是这副表情。老家伙是个疯子,可也是个好心肠的疯子,他做不到心平气和地跟他的白人兄弟们一样,他做不到跟你我一样,跟着狗群一起狂吠,因为他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他笃信《**》。他是个神圣的人,疯得不像样,纯真得要命,随便谁都能被他忽悠晕了。可至少他知道自己疯癫,至少他知道自己是谁。光是这一点就比我强。 我傻呵呵地躺在马车里的干*堆下面,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怎么也想不出我应该是个什么人,也不知道这辈子该唱什么调调。安妮的老爹是我心中的英雄。他是主心骨,我们黑人同胞的命运全负担在他的肩头。他背井离乡,去追寻心中的信仰。我没什么信仰。我就是个**,只想混口饭吃。 “我琢磨着,等打完仗我就要唱点歌。”我憋出一句话,“到处唱唱。” 安妮转过了头,眼中噙满泪水,不知想起了什么。“我忘记告诉爹杜鹃花的事了。”她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什么杜鹃花?” “杜鹃花。我在院子里种了一些,长出来,是紫色的。爹说如果真是那样,就告诉他,说那是个好兆头。” “这么说,他可能会看到的。” “不。他不会往那儿看。他们在院子后头,靠近灌木丛的地方。”说着,她终于忍不住,又痛哭失声。 “就是一朵花嘛,安妮。”我说。 “不光是一朵花。爹说好兆头是天堂发出的信号。好兆头很重要。比如弗雷德里克的上帝鸟。就是因为这个,他才总是在队伍里用这些鸟毛。这不是一般的羽毛,也不是一般的暗号,是兆头。这些东西不会轻易忘了,就算遇到困难也不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会记得你的好兆头。你不会忘记的。” 我的全身弥漫着一种**恐怖的感觉,我蓦然想起,“列车员”说在桥上截住火车的时候的暗号得告诉老家伙,而我忘了个一干二净。他说过要告诉他暗号的。他会说“是谁”,对方得回答“耶稣来了”。要是没听见暗号,他就不会交出他的人。 “老天爷。”我说。 “没错吧,”她痛哭着说,“是坏兆头。” 我再也没对她说什么,而是静静地躺在那里,听她失声痛哭,只有上帝听得见我的心脏痛苦万状,怦怦跳动。我想,去他的。我才不会从那干*堆里爬出去,光天化*之下穿过路上的层层哨卡,在弗吉尼亚和宾州之间有数不清的逃奴稽查员,我可不想一一躲开他们回到费里。我会给劈成碎片的。我们已经走了三个小时了。我感觉太阳的热力从地底下钻冒出来,穿透我身下的马车地板。我们一定已经抵达钱伯斯堡,马上要进入弗吉尼亚州界了,而弗吉尼亚州又偏偏是个蓄奴州。 安妮又痛苦了一会儿,之后渐渐平静下来。“我知道你还想着费城,洋葱头。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到北埃尔巴来。”她说,“也许我们可以合伙开一家学校。我知道你的心。北埃尔巴是个安静的地方。废奴。我们合伙开学校。我们可以找——我可以找到一位朋友来帮忙。”说到这里,她突然又痛哭起来。 这下完蛋了。我躺在干*堆底下,觉得自己还不如加拿大那些只会吹牛的卑鄙的牧师和医生什么的,他们答应参加老家伙的战争,却肯定不会来。在安妮的痛哭声中,我的羞愧排山倒海一般压下来。我们一公里一公里地前进,我的羞愧也随之滋长蔓延,巨石般压在胸口。我到了费城之后怎么办?谁会爱我?我只有孤零零的了。而在纽约她要过多久才会发现我的本来面目?用不了多久。再说,要是连你自己都闹不清自己是谁,别人又怎么会爱你?我扮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女孩时间已经太长了,我已经喜欢上了这种感觉,我习惯了,习惯了用不着扛东西,也习惯了别人觉得我不如男人力气大、反应快,不如男人那么坚强而替我开脱。然而问题就在这里。你装得了一时,却改不了自己的本性。你只是假装而已。你不是真的自己。说到底,我只是个黑人,黑人得扮演黑人的角色:躲躲藏藏,笑脸相迎。假装身上有枷锁算不了什么,可枷锁终有解开的**,之后呢?自由又有什么用?跟白人一样?白人的生活就都是对的吗?按照老家伙的想法,也不尽然。那时我所想到的就是,在生活中,你要时时刻刻做自己。也包括要去爱什么人。要是你不能做自己,又怎么能爱上别人?这样的人怎么会拥有自由?这个想法压在我的心口,像一把老虎钳。我垮了。我拜倒在那姑娘的脚下,我承认,自己用全部的心灵爱着她,要是因为“列车员”没有听到暗号,她的父亲就会丧命,那我这一辈子都会被他的责难压得透不过气来。她那个**养的爹!还有那“列车员”!那道貌岸然、无知狂傲、长得像头大象似的浑蛋!还有那些反对蓄奴制的家伙没一个好东西!我脑子里乱哄哄的。一想到老家伙要因为我而丢了老命,让我觉得比失去安妮的爱*难*十倍,要是她知道了我的本来面目,一定会厌恶我,一个男扮女装的**,不配做个男子汉,还妄想要爱她!她根本不可能爱上我,甚至不会喜欢我,不管她之前多么真心实意地拿我当好闺蜜。她爱的只是一个幻象。要是我像个懦夫似的躺在干*堆底下,而不是显出男人本来的样子,回去说出那几个字,哪怕只能帮他延续五分钟的生命,那么我的下半辈子双手将沾满她父亲的鲜血——老家伙虽然愚蠢,可我的命值钱,他的命也值钱,而且老家伙还多次为了我的缘故冒着生命危险。去***! 因为我的所作所为,使我的双手沾满上尉的血,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我*不了。 安妮屁股底下那块木板支在两块薄板上,我用双手推开两厘米左右,从稻*堆里坐了起来。 “我得走了。”我说。 “什么?” “叫萨尔曼停车。” “不能停车。咱们在蓄奴州境内呢。回到*堆里去!” “我要回去。” 她还没过来,我便从木板底下钻出来,一把撸掉软帽,把裙子扯到腰部以下。她的嘴张得老大。 “我爱你,安妮。我不会再见到你了。” 随着一个轻捷的转身,我抓起褡包,从马车后部一跃而出,滚到大道上。安妮的叫喊声响彻在我周围的树林里。萨尔曼一扯缰绳,朝身后的我喊了句什么,然而那喊声却好比石沉大海一般,我已经顺着大道,远走高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