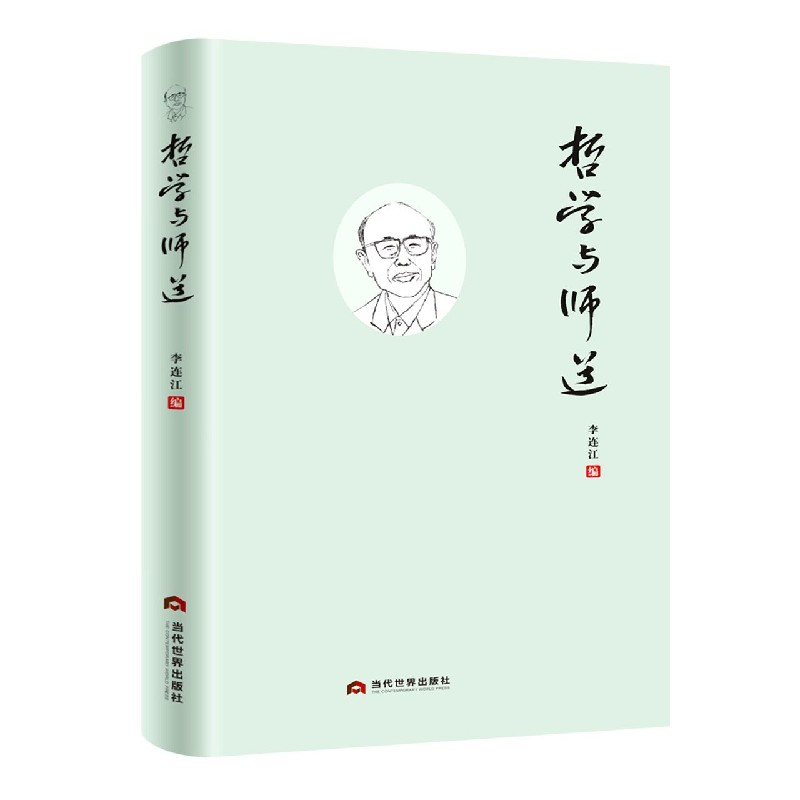
出版社: 当代世界
原售价: 49.00
折扣价: 30.90
折扣购买: 哲学与师道
ISBN: 97875090154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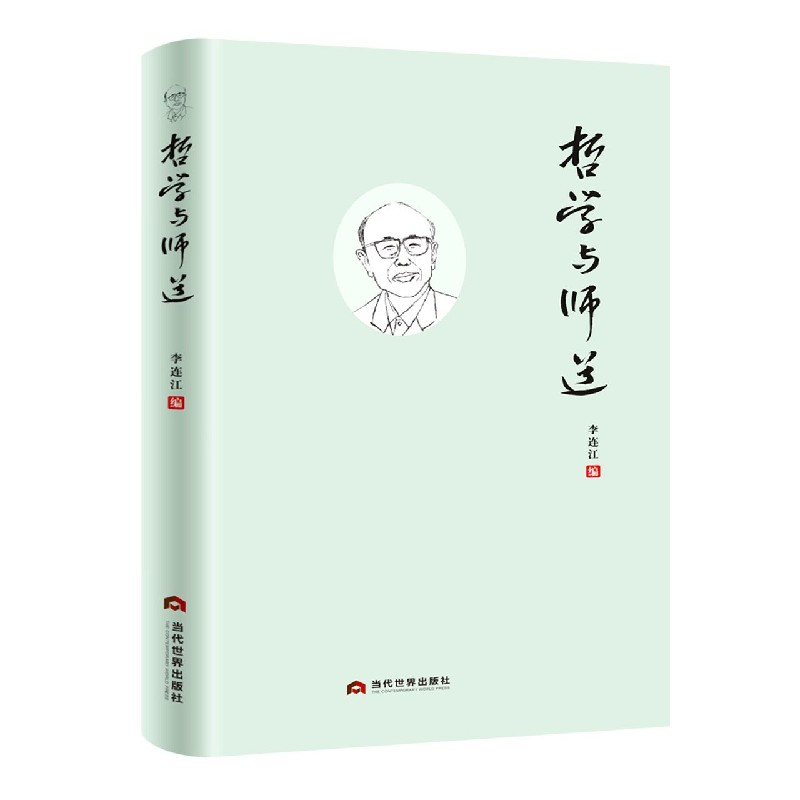
李连江,南开大学哲学系1978级学生,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
车铭洲:郑先生说:“我知道,学生总是希望老师领着读书,但是教师指导研究性工作,主要的责任不是帮助学生读书,实质上,读书也是无法帮助的。学生必须自己读书,在读书中读懂书,在读书中学会读书,这项功夫是不能由别人替代的。你已经读了不少书,肯定有体会了。而且,同样一本书,不同的人读,会读出属于各人的新东西,这正是读书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教师若给学生讲书,讲出的只能是教师个人的一种观点,很可能会妨碍学生产生他自己的新观点,也就失去了读书的真正价值。” 车铭洲:关于教师,记得黑格尔说过这样一句话:“伟大的刺激和鼓舞是一个教师的主要功劳,主要影响方式。”我想,这样的教师才是真正的所谓“大师”,才是大学真正的“中流砥柱”。 车铭洲:当了五十多年教师,我有两点体会。一个是,我认为教师的功劳不是教知识,而是鼓舞学生。知识可以教,但要靠学生自己刻苦研究才能学到;能力不能教,只能靠学生自己锻炼提高。学生学知识,长本领,出成就,都靠学生自己。教师起什么作用呢?教师的责任主要是影响学生。用什么影响?就是以书本上的知识为手段,帮助学生树立自己的学习目标,激发学生的创造精神,鼓励学生艰苦努力,帮助学生认识自己的潜力,促使学生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如果说教师培养学生,这就是培养。其实,这只是帮助,不是培养。我的第二个体会是,学生造就老师。老师的成就有学生的贡献,不是教师自己本来就那么优秀。必须有优秀的学生,教师才能进步。这是我坚信不疑的。我这个思想,现实的模型就是和尚撞钟。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大学里有学生,有教师,谁是钟?谁是和尚?和尚肯定是学生,钟是老师。钟自己不能发声,学生要是不撞,钟就不响。老和尚是个钟,老师是个钟,看着很神秘,就是不响;大敲大响,小敲小响,不敲不响。教师刺激学生,学生就会跟教师研讨,有研讨,就能出成就。老师的智慧是学生敲出来的,学生很优秀,总是敲打教师,教师就进步了。我受过很多学生的启发和教育。写这两本书,我也受到学生很多启发。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写书,我一开始也不会写书,是教书启发了我。为了教好书,教师都要精心准备讲稿,这就是写书。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写,但是有学生听课,我知道我必须写,写一写,就会写了,真写了,就真会写了。 伊永文:车老师总是和蔼可亲,他未和我发过火,我也未见他和别的青年学生发火,他总是循循善诱,不以己见压人,将学生置于一个平等的可讨论的位置上,疑义相析,共同探讨,服从真理,使人如沐春风,精神舒畅。 常健:我向老师诉苦说读不懂,车老师说:“那就再读。”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到车老师那里诉苦说还是读不懂,车老师的回答依然是:“再读!”回过头来我体会到,原来最笨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的方法。这样,“读读读”这“三字真经”成为我以后指导自己学生的法宝,每次与学生谈起学习方法,总会提起车老师的这三字真经。 武斌:当时车老师正在写一本《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的著作。闲聊中,他经常给我讲一些书稿中比较得意的内容或写作的心得。在他完稿之后,我请他允许我替他抄写书稿,以尽弟子之道。其实我心中另有打算,想利用这个机会体验一下这本书是怎样写出来的,完整地把握一本书的结构和意蕴。于是,我用了一个多月的课余时间,工工整整地抄完了这部20多万字的书稿。随着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地抄写,我逐渐熟悉和跟上了老师的思路,逐渐了解了他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表达方式,也似乎在体验着他从事中世纪哲学研究和写作这部著作时的工作状态、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一本书抄下来,我对自己将来从事写作活动也有了几分信心和把握。 穆建新:最后我的毕业论文就写了存在主义,没想到的是,车老师竟然给了我“优+”的评分,还加上了一段肯定的评语。这明显是对我这样一个落后生的鼓励和对我今后学习的一种激励。毫不夸张地说,车老师的这个评定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学习兴趣的提高和学习态度的积极,更重要的是,他推动了我人生道路上一个由自卑到自信的转变和飞跃。 王之刚:记得上车老师第一堂课时,他开场白的第一句话就是“知识分子爱睡觉”,“何以证之?有史为证”。然后就讲了一个故事:一天,孔老夫子上课,有学生课上打盹,孔老先生不高兴了,发起怒来,质问学生为什么上课睡觉。学生无言以对,只有接受批评。又一次,孔老先生让学生背书,学生们叽叽喳喳开始背起书来。一会儿,老先生居然在学生背书时打起瞌睡。于是,那天受到批评的学生质问孔老先生,为什么学生背书,老师不听,反而睡觉。孔老先生很生气,说道:“我没睡觉!”学生问:“没睡觉,为什么闭眼睛?”孔先生说:“我有事!”学生问:“什么事?”孔先生不耐烦地说:“我见周公去了。”学生知道老师崇拜周公,心想既然见周公去了,属于确实有事,不再发问。第二天,学生上孔老夫子的课,又睡起觉来,孔老夫子又去质问学生为什么不背书。学生这回学聪明了,说:“我也有事!”“你有什么事?”老夫子厉声质问道。“我也见周公去了。”孔老夫子心里明白这是说谎,问道:“周公和你说什么了?”学生答道:“他说昨天没见到你。” 杨龙:我的女儿从记事的时候起,就跟我去车爷爷家。她小的时候喜欢听大人聊天,在车先生家她也是个听众,更为吸引她的是先生家的猫。记得车老师有句“名言”:“爱动物才会爱人类。”先生对中国人的处事方法了如指掌,对教育界的事情尤为了解,每每在分析教育部或学校的大事的时候,总能提出精辟的见解,令我茅塞顿开。至今我还记得一些车先生的“语录”,比如“民主就是麻烦”——非常精到地点出了民主的一个基本特点。 朱光磊:车铭洲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学家。车先生还是一名与时俱进的教育家。在人才队伍建设上,车先生主张大学教师应将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应既是一个教育家,又是一个研究家;既要懂得教育教学的规律,掌握教学的艺术和方法,又要在教学的同时做高水平的研究工作,以创新精神将学科前沿理论向前推进。在教育教学上,车先生强调“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一定要教育出一流的本科生”,要“专心、专业、专长”,以获得自身进一步的发展。车先生的这些与时俱进的办学理念,在南开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江怡:车老师一直教导我们,若想学好外国哲学,必须要学好外语,这是我们的武器;没有掌握好这个武器,我们就无法了解真正的外国哲学。他一直鼓励我们要学好外语,有机会就出国去看看,到国外去学习深造。所以,很多车门弟子毕业后纷纷走出国门,到美国或其他国家留学——这已经成为车门弟子的重要标志。 朱国钧:在考哲学原理时,我对所有的题目都很有把握,也自认为答得很不错,未想到成绩出来却只有60多分。所以,我对哲学原理这个成绩耿耿于怀。当我想跟车老师解释我的哲学原理成绩不应该那么低时,车老师却很不在意地说了一句:“那不重要。”然后话锋一转说:“你的英语成绩不够好,要多下功夫。”车老师这不经意的一句话,对我而言,完全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一下子醒悟过来:原来那不重要!做学问的第一条就是分清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对于不重要的,就要放得下。就这样,当我还没有被录取为车老师的研究生时,车老师就在不经意间给我上了第一课, 而且是让我终身受益的一课。 梁骏:记得宣布“班导师”后,车老师“走马上任”,他来到班里,推心置腹地与大家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车老师个子不高,脸庞清瘦,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很像是南方人。他深情地对我们说:“大学的时光非常宝贵,你们一定要多加珍惜,充分利用,切莫虚度年华。哲学上的流派繁杂,人物众多,思想观点各异,典籍浩如烟海,所以,同学们在‘泛读’的基础上,一定要‘精读’。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某一个方向或问题,锲而不舍地深入下去,就像打井那样,钻头必须打到一定的深度,才能见油。学习哲学也是如此,浅尝辄止,肯定是挖掘不到宝藏的。此外,同学们一定要在外语学习上多下功夫,多花时间,多记单词和词组,没有过硬的外语能力,就无法尽快地了解外部世界,无法掌握最新的知识,无法借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李连江:有志于学,车老师称为“想学” ;笃志于学,车老师称为“真想学”。1986年,哲学系学生会组织了一次座谈,主题是怎样学英语。我听说车老师主讲,就去听。主楼317教室坐得满满的,气氛热烈。主持人致开场白,请车老师发言。车老师接过话筒,开口就问:“各位同学想不想学英语?”听众显然有几分意外,坐在前排的几个同学小声说:“想学啊!”车老师接过话: “想学?真想学还是假想学?真想学?那就学啊! 只要学,怎么学都能学会! ” 王正毅:善待学生。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没有什么职业比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的职业更崇高的了——这就是教师。不管教师自己的学问如何高深,能将每位学生培养成不但有知识和智慧,而且还有情趣的人,都应该是教师至高无上的成就,这是我与先生多年共事所得。先生性情温和,这与他学术的严谨多少有点冲突,尤其是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学生的志向不同,因而对待学术的态度自然不同;学生的脾气性格不同,因而处事方式亦相异,但先生总能以欣赏之心对待每位学生。共事多年,从未从先生口中听过对任何学生的不满。相反,每当学生有事相求时,先生总是尽力帮助。 韩旭:让我真正一睹车老师演讲风采的是一次全校范围的公开讲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间能容纳几十人的教室里挤进了上百人的场面。我早就耳闻车老师讲课很精彩。 眼见为实。在那堂讲座上,车老师深入浅出,幽默又充满智慧的话语使得课堂气氛十分活跃,笑声不断。哲学课能讲成这样,让我叹服!作为车老师的学生,我们为自己的老师深深地感到自豪。 苏福兵:和这种简朴环境相契合的是车老师的随和,天热时他就穿一件白棉布跨栏背心,下面是宽松的短裤,脚上一双塑料拖鞋,不时轻踩在身前的茶几上,一点没有大学者的做派。对我一个小县城来的新生,研究西方哲学的教授还不得西装皮鞋、不苟言笑且云里雾里的?可眼前的车老师除了一副眼镜以外,和邻居家叔叔没什么两样,只是他谈吐中充满了智慧,多么深奥的东西都能用平易的语言表述出来,嘴角还总是带着笑意,有一种慈眉善目的感觉,让人愿意安静下来聆听。 尹艳华:1989年我如愿考取了车老师的在职研究生,同时调入政治学系负责团总支工作。考虑到需要一定的时间熟悉新的工作环境,我主动向时任系主任的车老师提出延迟一年入学。车老师却说:“女孩子能早上最好还是早上吧,年龄大了生活上的压力会更大!”车老师的这两句话是如此平实,却让我感动得几乎泪目,终生感怀!硕士在读期间,车老师再次赴美访学,但是对我们这些学生都做了妥善的安排,最终我们都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在我之后的人生历程中,车老师一直都是重要的见证人和提携者。我结婚时,车老师是我的证婚人;小女出生时,师母细针密线亲手缝制了虎头枕,让我给孩子枕着,保佑孩子平平安安。这不仅是师生之情,更如父母之于儿女晚辈的亲情! 刘宏伟:作为一名本科生,我当时所知道的是,先生在同学们的心中是神一般的存在。当年经常能看到先生走在北村与主楼之间的路上,衬衫比外套长一截,当时觉得这种穿衣风格好另类却有道骨仙风,没想到若干年后这成了一种时尚。后来在课堂上听先生讲课,先生总是能用生动诙谐的方式将晦涩的西方哲学讲得入脑入心,讲台上的水杯就是先生讲课的道具。至今仍记得先生讲当代青年的迷惘与困惑,举的例子竟然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听到这首歌,我的脑海里浮现的都是当年课堂上同学们会心而笑的情形。今天想来,先生当时的年纪正是我如今的年纪,但我感觉自己已然跟不上潮流的前浪,年轻人的怀旧金曲在我这里是未曾听过的新歌,而先生却是一直与时俱进,高深的学问也能以年轻人易于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 罗金凤:最好的教育是什么?卢梭在其著作《爱弥儿》中说道,“最好的教育就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学生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发挥了潜能,这才是天底下最好的教育。”换句话说,最好的教育,就是你几乎忘记了学到的所有知识,但唯独铭记了精神。我想车先生给予我的就是这样最好的教育:二十六年过去了,当我也年过半百,忆往昔,依然热血澎湃;对未来,依旧信心满满。 王倩:记得回国探亲时,孩子最喜欢去看望大学问家车爷爷和比姥姥还亲的车奶奶。到了先生家,孩子给车奶奶画画,还问车爷爷为什么从英国来的钢琴主考官竟然是主修长笛的,逗得先生开心大笑。孩子每次都有好多的趣事和问题要告诉车爷爷和车奶奶,先生和师母都耐心地认真听,并不时地开心大笑起来,那温馨的场面至今难忘。车先生很爱孩子,先生和师母当年送给孩子保护眼睛的LED台灯和精美的记事本陪伴了孩子整整小学六年。孩子十多岁时就跟车先生讨论美国大选、新加坡及东南亚的发展,车先生跟我说,这是个有想法有抱负的孩子,以后让他学习政治与国际关系,当领袖。当时觉得那只不过是大人们一时的茶余闲话,没想到今年孩子真的就拿到这个专业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应了车先生当年的慧眼预言。 王立文:那是一种极致的思维训练。因为英文不灵光,读一些翻译过来的著作,从字里行间揣测西方哲学家们的微言大义,有句成语叫披沙拣金,这“沙”真的浩瀚如海,或许金子还没有拣到,我们已经把很多石头当成金子。先生上课的特点,是提前开书目,让学生先讲。结果,同一本书、同一部分内容、同一个文本,居然理解得千差万别,有时甚至正好相反,先生没发话,我们先打起来了。好在,先生并不责怪,仿佛都在预料之中,把我们所讲的内容,一条一条地聚拢,最终把整个脉络梳理清楚。这个时候,我们才领悟到什么是学问打通了的功力。 王永红:赴美以后,每次打电话给车老师,他都不仅关心我的学业﹑工作和生活,而且还将我的专业研究领域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在国内发展的状况及时告诉我。我那本《美国贫困问题与扶贫机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车老师仔细地进行了阅读,并告诉我他的看法。他提醒我如果有机会,应当将书中的一些好思路具体应用到中国社会中来,帮助政府和大学研究机构建立一些相关项目,以期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光荣:车老师没有一板一眼地面试,他把重点放在指导上。在一间空荡荡的小办公室,他坐在一张普通的小课桌前,和颜悦色地让我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开始面试。轻描淡写地问了几个小问题后,就开始讲研究生期间如何学习,鼓励我不仅要学哲学和英语,还要学好高数,不要以为学文科的就学不了理科,只要下功夫,都学得了;不论学什么都不能满足于一般大众水平,学到高水平才有用。他说,英语通过六级,只代表考试水平,要下功夫练好听说读写,能读原著,能用英语跟外国学者直接交流,能同声翻译。车老师循循善诱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告诉我面试结束,回去后立刻制定计划开始学习。 奚先来:车先生是我大学期间的系主任,至今我对车先生的印象也是我大学时他的模样,一个个子不高、瘦瘦的、头发稀少、戴一副眼镜、背着一个黑色类似电脑包、说话慢条斯理、智慧火花频现、行走在南开校园的小老头。我毕业留校工作多年后在校园里碰见他,他还是那个模样,岁月在车先生身上似乎是停滞的。因此,有老师写回忆车先生的文章,说他是智慧之树常青,对此,我深有同感。 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 师道的真谛是爱学生 以为国育才为灵魂 以正面鼓励为主体 以智慧点拨为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