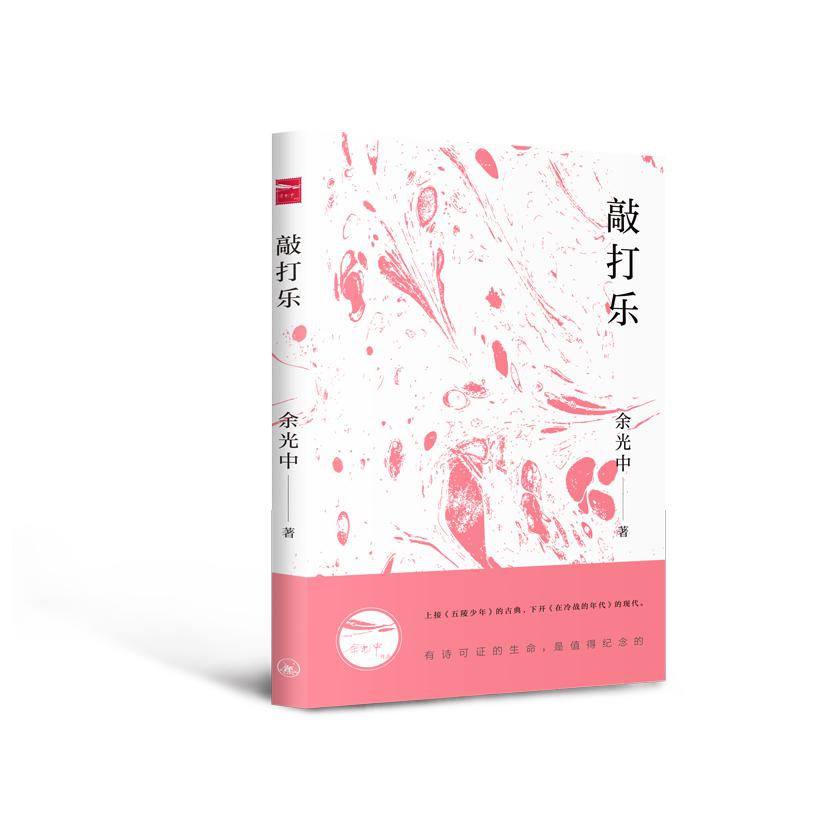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三联
原售价: 36.00
折扣价: 24.20
折扣购买: 敲打乐
ISBN: 97875426655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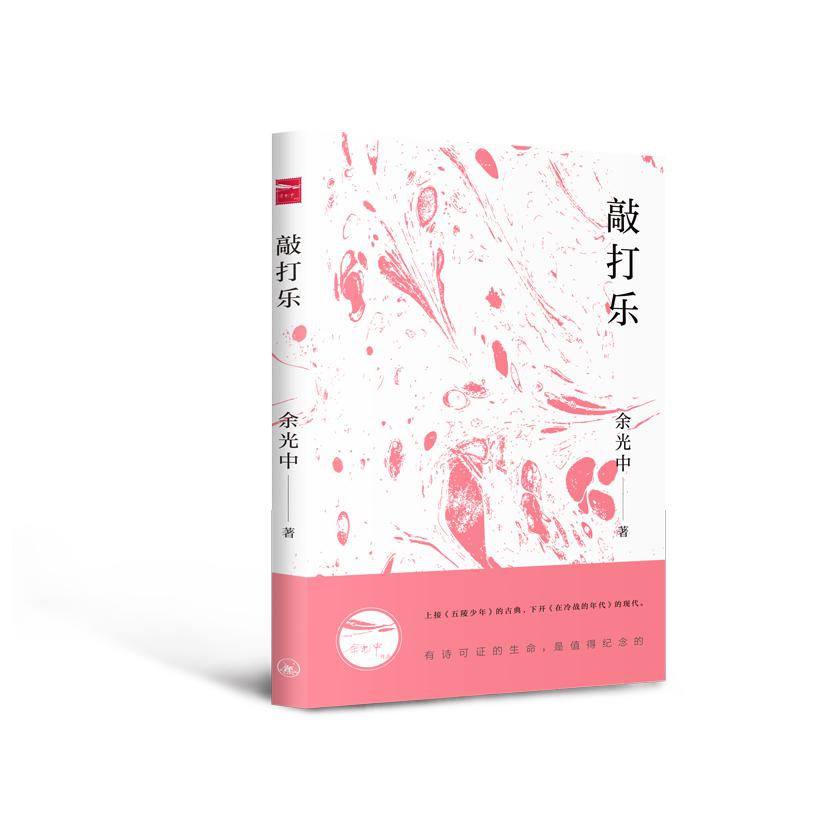
余光中(1928—2017),**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祖籍福建永春。 1952年毕业于**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先后任教**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大学、**政治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称四者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代表作品有《乡愁》《乡愁四韵》,散文如《听听那冷雨》《我的四个假想敌》等,广泛收录于语文课本。
新版自序 《敲打乐》是缪思为我所生的第八胎诗集,里面的十九首诗全是我在一九**至一九六六年间再度旅美时所写。两年之间,得诗十九,不能谓之丰收,不过比起我第三次旅美,也是两年却只得诗六首的产量来,情况仍然较佳。近*逝世的英国诗人拉金(Philip Larkin, 1922—1985),据说晚年平均每年只写两首诗。这么说来,我在《敲打乐》的时代也不算是怎么歉收了。其实这些作品的诞生,也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例如前面的五首都写于一九六五年的四月与五月,而后面的十二首都写于一九六六年的春天与初夏。那两年我驶遍了美国北部各州,车尘从东岸一直扬到西岸,其间以住在盖提斯堡1的五个月,和住在卡拉马如的十一个月,生活比较安定。所以这本诗集后面的十四首都成于卡拉马如;前面的五首则成于盖提斯堡。不过在那座俯视古战场的七瓴老屋顶楼,我还写过《九张*》《四月,在古战场》《黑灵魂》《塔》等四篇散文,因此盖提斯堡的那半年,缪思待我算是不薄的了。 远适异国,尤其是为了读书或教书而旅居美国,就算是待遇不薄,生活无忧,但在本质上始终却是一种“文化充*”。再加上政治上的冷落之感,浪子的心情就常在寂寞与激昂之间起伏徘徊。这里的十九首诗,记录的大致就是这样的情怀。其中也许还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比较偏于感性,例如《灰鸽子》《单人*》《雪橇》等作;另一类则兼带知性,如果读者不识其中思想及时代背景,就难充分投入,例如《犹力西士》《黑天使》《哀龙》《有一只死鸟》《敲打乐》等作。 在那两年里,**年不仅去国,而且无家,那种**的孤独感,有时令人心如冰河,未必有益于缪思。《神经网》《火山带》《灰鸽子》《你仍在中国》等几首所写,就是这样的一个远客对家中爱妻的悬念。《火山带》的末段说到在灯光下面对圣人的经典,那是指作者当时教中国古典文学,夜间备课的心情。《灰鸽子》虽然写于卡拉马如,却是追忆作者在盖提斯堡时的感觉,故以废*为背景,而与灰鸽形成对照。《你仍在中国》是写作者的妻女赴美探亲的手续未备,迄仍滞留在海关的另一边,致令作者苦待经年;末二行正是两地悬殊的地理与气候,而诗末所注*期,正是我们的结婚纪念*。 有些论者一直到现在还在说,我的诗风是循新古典主义,与现实脱节云云。什么才是现实呢?诗人必须写实吗?诗人处理的现实,就是记者报道的现实吗?这些都是尚待解答的问题。不错,我曾经提倡过所谓新古典主义,以为回归传统的一个途径,但是这并不意味我认为新古典主义是**的途径,*不能说我目前仍在追求这种诗风。看见一位诗人在作品里用典,或以古人古事入诗,就说他是逃避现实,遁于古代,未免是皮毛之见。问题不在有没有引经据典,而在是否用得恰当,有没有赋经典以新的意义。我以古人古事入诗,向来有一个原则,就是“古今对照或古今互证,求其立体,不是新其节奏,便是新其意象,不是异其语言,便是异其观点,总之,不甘落于平面,*不甘止于古典作品的白话版”。例如本集的《犹力西士》一首,用的虽然是奥德赛的故事,但正事反说,是古人咏史的翻案手法,“一个伤心的岛屿”说的正是六十年代当*的现实。恐怕只有粗心的读者才会以为这首诗是在写希腊。 《黑天使》写的是勇敢的先知,文化思想的真正斗士。那时年轻的作者壮怀激烈,充溢着那一代的“文星意识”,心目中也真有这么一位先知的形象。后来发现那形象只是一时的假象,乃决定只用黑天使这形象,不须附加任何副标题了。**重读此诗,觉得“我是头颅悬价的刺客”那一段,豪气仍然可惊,换了现在,恐怕是写不出来的了。《哀龙》所哀者乃中国文化之老化,与当时**保守人士之泥古、崇古。《有一只死鸟》的主题与《黑天使》相近,写的仍是一士谔谔的那份情*,其事放之四海而皆然,固不必囿于苏联,所以也把旧有的副标题拿掉了。 引起误解甚至曲解*多的,该是主题诗《敲打乐》了。这首长诗自从十八年前发表以来,颇有一些只就字面读诗的人说它是在侮辱中国。这种浮面读者大概认为只有“山川壮丽,历史悠久”以及“伟大的祖国啊我爱你”一类的正面颂辞,才能表达对**的关怀。这种浮词游语、陈腔滥调,真能保证作者的情*吗?在悲剧《李耳王》里,真正热爱父亲忠于父亲而在困境之中支持父亲的,反而是口头显得淡漠的幼女。中国人常说“孝顺”,其实顺者有时未必是大孝。爱的表示,有时是“我爱你”,有时是“我不知道”,有时却是“我恨你”“我气你”。 在《敲打乐》一诗里,作者有感于异国的富强与**,本国的贫弱与封闭,而在漫游的背景上发为忧国兼而自伤的狂吟,但是在基本的情*上,却**和中国认同,合为一体,所以一切国难等于自身*难,一切国耻等于自身蒙羞。这一切,出发点当然还是爱国,而这基本的态度,在我许许多多的作品里,尤其是像《地图》和《蒲公英的岁月》一类的散文里,我曾经再三申述。《蒲公英的岁月》甚至以这样的句子作结: 他以中国的名字为荣。有**,中国亦将以他的名字。 奇怪的是:仍然有一些论者竟然断章取义,随手引述《敲打乐》诗中的句子,对作者的用意妄加曲解。这首诗刊于六十年代中期,当时的言路不像**开放,所以有些地方显得有点隐晦,恐亦易起误会。例如“菌子们围以石碑要考证些什么”那一段,说的正是我们文化界的抱残守缺。又如“整肃了屈原”一段,说的固然是“**”前夕的大陆,但是未必没有我们自己的联想:当时《文星》月刊奉命停刊,该刊末期的言论我未必全然赞同,但是这么一本原则上代表知识分子心声的刊物,竟然不能再出下去,对我当*在异国的心情仍是一大挫折。又例如下面这一段: 从威奇塔到柏克丽 降下艾略特 升起惠特曼,九缪思,嫁给旧金山! 原是指六十年代中期,美国的江湖派诗人反对博学而主知的艾略特,宁可追随惠特曼自由奔放的诗风,而当时的青年文化也逐渐从东岸移向西岸,以旧金山为中心。惠特曼在《*叶集》里曾经豪情大发,叫缪思从希腊移民去新大陆,开拓新诗的天地。我说“九缪思,嫁给旧金山!”正是用惠特曼的口吻把此意向前*推一步。竟有一位哲学教授把这句诗解为作者有意奉献自己给旧金山,足以反证他根本没读过《*叶集》,不了解惠特曼。 我在写《敲打乐》时,还没有注意到美国的摇滚乐,诗以敲打为名,只是表现我当时激昂难平的心境。诗句长而标点少,有些地方字眼又一再重复,也是要加快诗的节奏;这样的紧迫感在我的诗里实在罕见。此诗曾经我自己英译,收在《满田的铁丝网》(Acres of Barbed Wire)译诗集里。后来又经德国作家杜纳德(Andreas Donath)译成德文,收进一九七六年为纪念汉学家霍夫曼而出版的专书《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经济》(China: Kultur, Politik und Wirtschaft Festschrift für Alfred Hoffmann)。 《当我死时》这首诗曾经收入许多诗选;我在香港的时候,发现大陆也有好些刊物加以转载。香港作曲家曾叶发先生,早在一九七五年,曾将此诗谱成四部混声合唱曲,并在崇基学院亲自指挥演唱。 写于二十年前的这些诗,**读来,仍能印证当*深心的感*。诗,应该是灵魂*真切的*记。有诗为证的生命,是值得纪念的。这些诗,上接《五陵少年》,下启《在冷战的年代》,通往我六十年代后期的某些诗境,形成了我中年诗生命的一个过渡时期。本集曾经收入《蓝星丛书》,初版于一九六九年,十七年来迄未再版,坊间也久已*踪,所以得窥全豹的读者很少。现在幸得九歌出版社重新排印出版,再呈于读者之前,真可以说是为二十年前的我招魂来归了,一笑,一叹。 余光中 一九八六年元旦于高雄西子湾 余光中先生曾以一曲《乡愁》为大陆读者熟知,其文学成就不止于诗,于散文、评论、翻译、编辑方面也是华语文坛坐标。也无怪人以“璀璨的五彩笔”来形容余光中的成就:紫色笔来写诗、金色笔写散文,黑色笔写评论,红色笔来编辑文学作品,蓝色笔来翻译。**的这套书,正是他的诗、散文、评论与翻译的集合,“五彩笔”如何妙笔生花,读者正可在本套丛书中得见。 余光中的诗歌作品境优美自不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