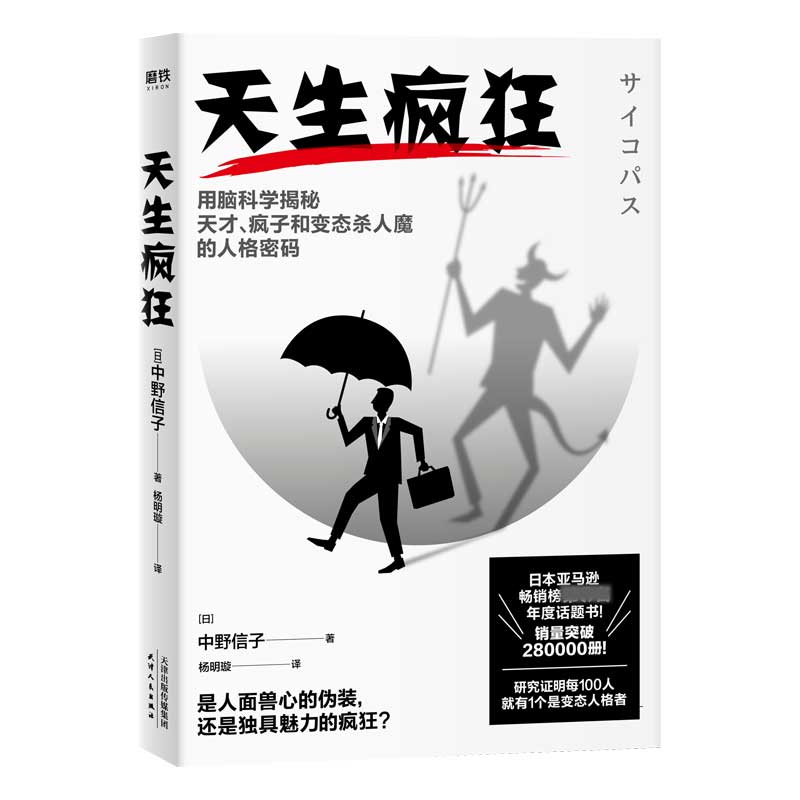
出版社: 天津人民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6.55
折扣购买: 天生疯狂
ISBN: 9787201160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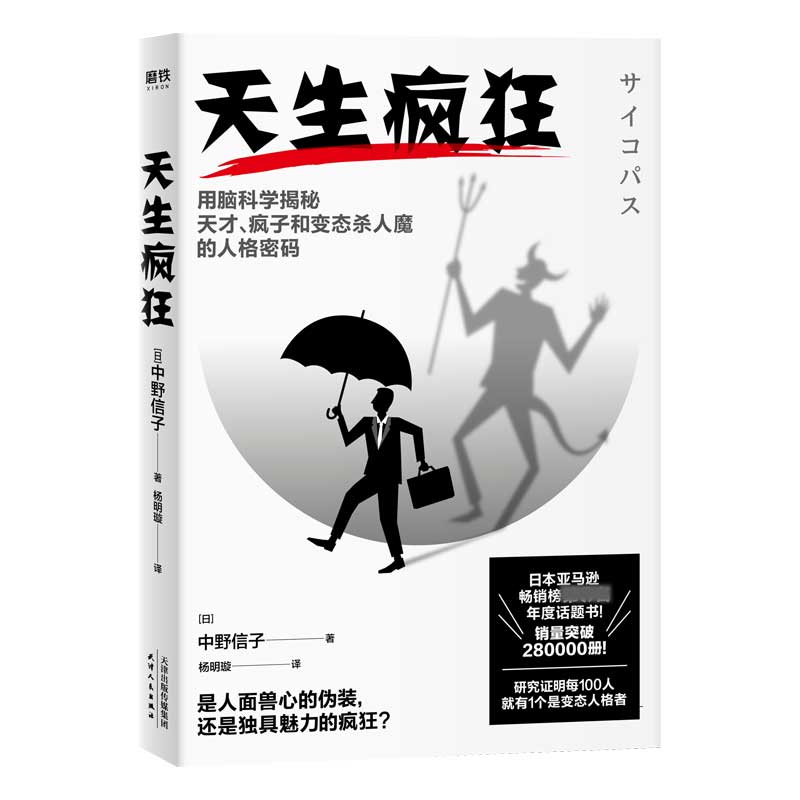
\\\"中野信子,日本脑科学家。东日本国际大学特聘教授。横滨市立大学客座准教授。生于1975年。东京大学工学部毕业,东京大学医学系研究科脑神经医学专业博士毕业,医学博士。自2008年起近10年来,就职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NeuroSpin(超高磁场MRI研究中心)。 曾以评论家的身份活跃于「信息介绍独家报导」等电视节目,并于富士电视台“平成教育委员会2013!! 日本的头脑决战SP”节目中获得优胜,赢得“日本第一金头脑”的封号。 著有《科学验证的改运法》《脑内麻药》《东大毕业的女性脑科学家教你如何换一副有钱人的脑袋》《活跃全球的人会做的事》《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祈祷”》《大脑·战争·自然法则 超越与克服近代人类观》等 \\\"
\\\"国家负担高过抑郁症 从历史角度来看,变态人格总是和犯罪密不可分。 但是,现实情况究竟如何呢?犯人有变态人格的概率到底是多少呢? 根据加拿大著名犯罪心理学专家罗伯特·黑尔的统计报告,在服刑的罪犯中,平均有20%的罪犯有着变态人格,半数以上的重大案件由他们造成。而且,变态人格者“二进宫”的再犯罪率是其他罪犯的2倍,如果只看暴力犯罪的话,这个比例能达到3倍。 关押在美国监狱内的变态人格者大约有50万人。有相关研究者推测,社会上,虽然没有犯罪但依靠巧妙利用周围人得以生存的变态人格者高达25万人。 而且起诉变态人格者并把他们送进监狱的费用,以及对受害者的赔偿金都是巨大的。根据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神经科学专家K.A.基尔的计算,2011年,美国在这方面共花费了4600亿美元,而这庞大的金额自然由国家来承担。与之相对的是,为了减少“抑郁症”打出的一套组合拳,花费了440亿美元。也就是说,针对管控变态人格者的费用比对治疗抑郁症的投入还要高。 那么,典型的变态人格者究竟有着怎样的画像呢? 下面,让我介绍4位具有代表性的罪犯吧。 兰迪·克拉夫特Randy Kraft(1945—)——无视他人感受、“学习”自我满足的手段 兰迪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这个保守地区的一个中等家庭中长大。 他天资聪颖,智商高达129(日本东京大学学生的平均智商是120),在校成绩优异,取得经济学学位后,以IT顾问为职。 然而,背地里的他却是一位连续杀人犯。每到日薄西山之时,他会一边开着车,一边寻找15岁到25岁的男性为目标。他请选中的男性喝下了药的饮料,让对方丧失意识。因为兰迪有着沉迷于同性性行为的癖好,所以有时会拷问、强奸对方,再将之杀害,遗体则被他丢弃到车外。12年间,兰迪这样做过64回。他甚至为此做了一份被害者列表,仔细整理了自己的犯罪记录。 在犯案后的第二天一早,他还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去办公室上班。犯下连续杀人案,还可以不被任何人发觉地保持着日常生活的状态,正是由于这份异常的冷静,他才能在杀人魔和好青年之间“无缝切换”。这就是变态人格的特征之一。 向失败“学习”,化身杀人魔 那么,为什么兰迪可以在调查当局的眼皮底下屡屡逃脱呢? 真相就在于他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其实,在开始实施暴行时,兰迪曾一度被捕。当时,因为他的目标恰巧是一位卧底警官,所以他在犯罪之前就被发现并被警方当场逮捕。 然而兰迪并没有在这次被捕的教训之后金盆洗手,改过自新,而是决定避开成年男性,把目标锁定为十多岁的少年。因为这样的话,对方是卧底警察的可能性就为零了。 保释后,他只寻找十多岁的少年作为自己的目标,继续着自己的罪孽。 但是,又因为事后他将犯罪者活着放走,导致当地开始爆出有人专门对年轻男子施暴的传闻。 他再次从中“学习”,决定杀害那些被害的少年。在兰迪的意识里,没有“坏事好像要暴露了,收手吧!”,只有“杀掉的话就不会暴露了”这样的逻辑。这也是变态人格者独特的学习模式。 这里,我用了“学习”这个词,可能会有人觉得不合适。可是,要想回避危险、满足自身欲望,最合理的做法必然是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 只是,变态人格者不会去思考他人会变得怎样,不会有关怀他人的想法。他们能非常富有逻辑地思考,步步为营,却不能和他者产生共鸣、同情心,也完全没有羞耻意识、犯罪意识。 变态人格者犯罪时的动机常常是“追求刺激”。而且,比起把目标特定为某个人,他们更倾向于将目标的范围扩大。也就是说,变成像兰迪这样不限定袭击目标的惯犯、杀人魔的可能性非常高。 兰迪罪行的暴露也纯属意外。1983年,他因酒后驾驶被停车检查。当时在轿车的副驾驶座位上发现了一具半裸的男尸。直到今日,兰迪仍在监狱内服刑。 简·托潘Jane Toppan(1857—1938)——活泼开朗、爱吹牛的快乐杀人犯 说到“杀人犯”,一般我们脑海中都会浮现男性的面孔吧?现实也的确如此,根据日本的《犯罪白皮书》显示,大约有75%的杀人案件由男性造成。可我们不能否认,也有女性的变态人格者存在。 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有一位叫简·托潘的护士。因为她在工作中乐观活泼的态度,被人们亲切地成为“阳光小简”。 但是,她却有着另一张面孔。1895年到1901年这六年,她在自己工作的剑桥医院给患者打入了剂量足以致死的吗啡。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没人发现的情况下悄悄进行的。打入吗啡的患者意识模糊,瞳孔收缩,陷入昏睡状态。 你觉得到此为止了吗?随后,她又给患者注入阿托品。 阿托品是生物碱的一种,有抑制副交感神经的作用,还能抑制胃肠运动,加速心率,和吗啡的药效完全相反。打入阿托品的患者,瞳孔忽然放大,变缓的心跳骤急。最终,患者会全身痉挛、发汗,在病床上苦苦挣扎直到死亡。用这样的方法,她至少杀害了31个人。 1901年,简被捕了。她在被捕之后,面对“为什么做这些”的疑问,回答道:“我也没想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多残酷的事。” 通过杀人获得快感 她在杀人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种“靡靡之乐(voluptuous delight)”(表示性方面的快感,19世纪的词汇,现在英语中常用ecstasy)。她不会有罪恶感,只有恍惚的感觉。如果目的不是金钱的话,也谈不上有什么怨恨,这只是纯粹的“快乐杀人”。类似的案件日本也有发生,如“通过杀猫获得快感”的神户、连续杀伤儿童事件的犯人、自称“酒鬼蔷薇圣斗”的元少年A等。 另一方面,因为简的性格开朗乐观,所以在逮捕她后,调查局收到了很多“她应该不是那样的恶人”等反馈。顺便说一句题外话,哪怕是专业的心理学家,在出访监狱和正在里面服刑的变态人格者们谈话后,时常也会有类似的感叹,如“从这个人的谈吐举止来看,他值得信赖啊,一定是因为误会被关进监狱的吧”。 令人诧异的是,简在被捕的第二年被判为无罪。按照当时的医学,她被诊断为“精神错乱”,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 因为她有“极端冷静把人杀死”的自觉,所以,据说她自己在听到这个诊断结果时,也备感困惑。 所谓变态人格,和重度精神分裂不同,没有妄想、幻觉等症状,也不是那种无法自主做出决定的心智丧失、衰弱的状态。他们的意识是清晰的——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其他的精神病患者也会烦恼,也在痛苦。但变态人格者不一样,他们自身几乎没有任何不愉快的感觉。 变态人格,到底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对于这样的问题,专业人士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将在第3章详细讨论这些观点。现在,先让我们看看简是在怎样的家庭中成长的吧。 上文提到的兰迪·克拉夫特在中等家庭长大,受教育程度高。与他不同的是,简·托潘出生在爱尔兰裔的移民家庭中。在当时的美国,爱尔兰裔备受歧视。因此,据说她经常撒谎自称“意大利的孤儿”。 她1岁丧母,父亲因为精神疾病没有抚养她,祖母则贫困潦倒。所以直到5岁,她都在公立的救助机构中苟且偷生。5岁后,她被人收养。但是,与其说她是成为寄人篱下的养女,倒不如说是被当作用人任意驱使、虐待。 简不光伪造了自己的出身,还是个撒谎大王。 “我的姐姐可是英国的贵族哦”“我呀,从俄国皇帝那边收到要我过去做看护的邀请哦,但是为了在这儿工作,拒绝了”这类假话,她在日常生活中对谁都说过。不只想让他人高看自己,有时也会偷别人的东西。这样看来,简不光有变态人格,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可能性也非常高。所谓“自恋型人格障碍”,不是单纯地爱着这样的自己,而是认为自己优秀美好,是特别伟大的存在的人格障碍。 有着这样苦恼的癖好,她却完全没有反省,而是继续在众人面前扮演着人见人爱的角色。 “怦然心动”地剁碎 关于简·托潘行凶的具体数据,最初她自曝“做了31次吧”,但之后又供述“至少杀了100个人吧”。这究竟是隐藏了真相,还是为了炫耀而夸张了事实?又或者,她只是杀了太多人,单纯地记不清具体次数了? 不管怎样,对待杀人这件事,她丝毫感受不到什么深刻的痛苦,她也没有什么情感上的暴力冲动。可以说,她几乎是在用工作的态度机械地进行犯罪。 我为什么认为她有着变态人格呢?因为她表面上表现得十分富有魅力,另一方面,却习惯性地说谎,迫使大家关注自己,却完全无视他人的痛苦,只为了满足自己的快乐。罗伯特·黑尔的这个形容就十分吻合简·托潘的情形:“(变态人格者)像是在感恩节的晚宴上切碎火鸡一样,怦然心动地拷问、剁碎受害者。” 有着变态人格的杀人犯和没有变态人格的杀人犯,在犯罪时也有着天壤之别,就是他们是否会有计划地犯罪。 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有过这样一项研究。针对变态人格者犯罪的计划性,心理学家迈克尔·伍德沃斯和史蒂芬·波特对2002年加拿大联邦监狱收监的125名男性杀人犯做了统计。他们把杀人案件分为“冲动、无计划的激情杀人”和“为了享乐或金钱等目的,之前做好计划、有手段的预谋杀人”两种类型。其中,有48.4%的非变态人格者犯下了“预谋杀人”的罪行,而变态人格者“预谋杀人”的比例竟高达93.3%。 而且,变态人格者在犯罪的时候,除了杀戮之外,还有对受害者施加暴力的倾向。例如,不仅仅是勒死对方,他们还会把遗体弄得破破烂烂。他们钟情于拷问、殴打、分尸等虐待狂的行为。同时,迈克尔·伍德沃斯和史蒂芬·波特也研究了变态人格和奸杀的关系。他们调查了2003年因奸杀定罪的38位罪犯,其中有52.6%的非变态人格者和82.4%的变态人格者对死者做出了超出致死范围的暴力罪行。 非变态人格的罪犯们,往往都是为了不让死者被发现(就是说隐藏证据)而杀人。而变态人格者们则不仅是这样,他们还有着通过观察他人痛苦的样子而感到愉悦的倾向。 有计划地、理智地犯罪和超出杀人灭口范围的过剩暴力——这就是变态人格的特征。 克里斯托夫·罗康库 Christophe Rocquencourt(1967—)——骗局暴露仍面不改色的天生诈骗专家 不是所有的变态人格者都是杀人犯。克里斯托夫·罗康库就是一名游走在法国和美国之间的诈骗专家。 1967年,他出生于法国的翁弗勒尔。喝得烂醉的父亲和一名娼妇生下了他,之后他就被送入了公立救助机构。 他在18岁的时候成为了俄国贵族,看到女友父亲的房产时,就当成自己的房产一样,伪造了相关文件,私自把那栋房子卖掉。通过这起诈骗案件,他骗取了100万法郎。 他又通过撒谎犯下了数起案件。然而他的谎言被识破的原因,看起来有些愚蠢。 克里斯托夫·罗康库还自称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员”,从资本家手中骗到了以百万美元为单位的投资。然而,他的坐骑暴露了这场骗局:因为他乘坐的轿车不是美国三大巨头(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高级轿车,而是日本的马自达。 在被逮捕后的采访中,他直言道:“我觉得自己不是罪犯,因为我只是运用头脑盗窃。”与兰迪·克拉夫特一样,我们完全看不到一丝反省的神色。 甚至他被释放后,竟然把这段经历做成了一门生意,包括开展作为诈骗专家的人生演讲等,也因为形象好,出演了电影中诈骗专家的角色。 “要把剩下的纸箱也打开吗?”——日本江东区公寓碎尸案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起案件的罪犯极其猖狂,就是在2008年日本东京江东区发生的一起女性失踪被害案件。 一名23岁的女性在回到江东区的自家公寓时,忽然失踪了,只在她家的玄关处发现了少量的血迹。公寓出入口处的监视摄像没有拍到她再出门的身影,因此推断她确实是在公寓楼中失踪的。于是,警察开始搜索公寓楼内部,也采集了每一位居住者的指纹。 然而,尽管警方对公寓楼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但经过了一个月,仍然不知道犯人究竟是谁。各种解不开的谜团和不安的情绪充斥着这栋公寓。 在这之中,有一位年轻的男性居住者过于频繁地出现在各个媒体上。他接受了电视采访,说了很多诸如“(对被害者)有印象”“太可怕了”的评论。案件发生后,传闻他又给公寓的物业打电话,要求“必须有更严格的管理”“增加摄像头的数量”等。 然后一切真相大白之后,才知道这位男性就是犯人。因为他想要把那位女性“变为性奴”,从而袭击、杀人,又将遗体藏在自己家中。之后,观察警察的动向,把遗体切成小块,一部分通过下水道冲走,另一部分遗弃在便利店的垃圾箱中。 为什么他能够在警察的眼皮底下“逍遥”一段时间呢? 当然,警方的搜查员也进入了他的房间搜查。 他的房间中堆着数个纸箱,毋庸置疑的是搜查员也注意到了它们。他一脸无所谓地协助调查,并且自己率先打开了几个纸箱给搜查员看,并问道:“剩下的也要看吗?” 实际上,最后几个箱子中还有受害人的部分遗体。如果当时搜查员检查了所有的纸箱的话,就可以当场将他绳之以法。可是,他自信满满的态度,让搜查员掉以轻心。最终,还是因为留在现场的零星几个指纹,以及只有他在犯罪时间段和被害者在同一楼层这两点将他逮捕。 即便证据确凿,他在被警察传唤调查、搜索房间时,依旧摆出一副什么坏事都没有做的样子,一脸平和地编织着谎言。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位犯人很可能有着变态人格。 在这起凄惨的杀人案件被侦破后,向犯人的邻居和他周围的人了解情况时,得到了很多诸如“为什么是他啊”“完全看不出他能做出这种事”的回答。 他得到周围人这样的评价并非个例。正因为他有着变态人格,才有能力伪装成普通人,或者比普通人更加认真的“好人”。 变态人格者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非常好的。他们仪表堂堂、满腹才华,甚至天真烂漫,其特征就是能够轻易获得他人的信赖。 \\\" \\\"·为什么有些人睁眼说瞎话、踩踏别人、毫无同理心?? 为什么他们表面上精神健全,却有着假面下的扭曲心性?? ·透过脑科学精准解析,揭开面具下令人意想不到的人格阴暗面!? ·研究证明每100人就有1个是变态人格者! ·日本亚马逊畅销榜第1名年度话题书! 销量突破280000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