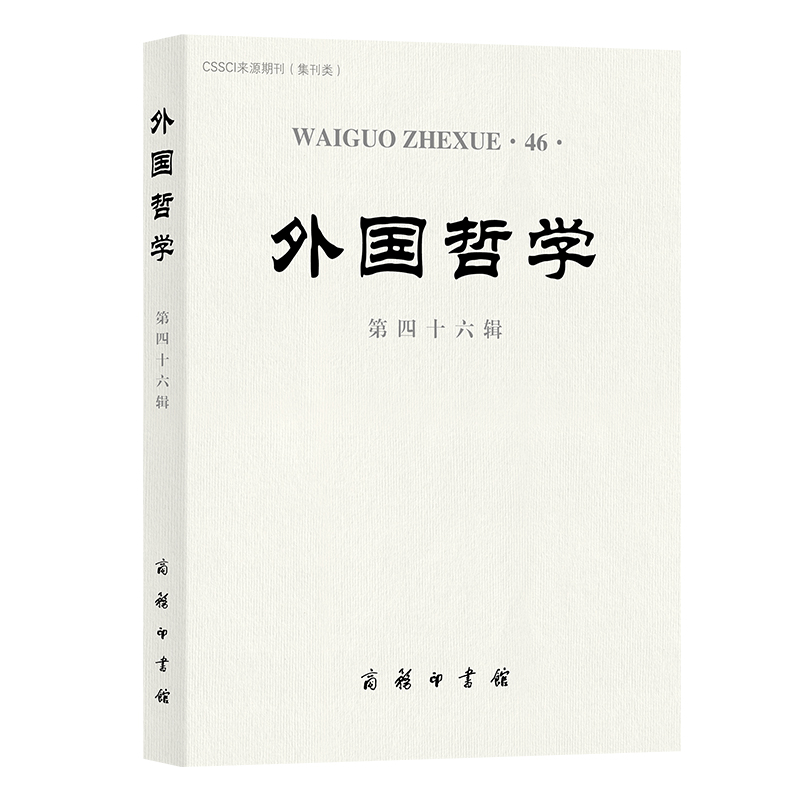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128.00
折扣价: 88.40
折扣购买: 外国哲学(第46辑)
ISBN: 978710023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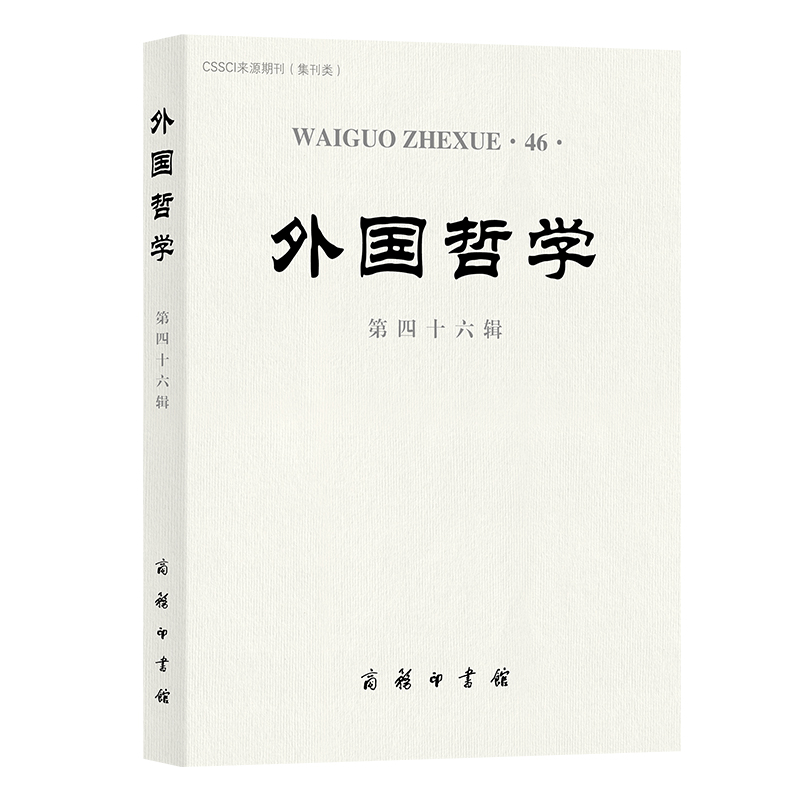
韩水法,1958年生,浙江余杭人。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德国图宾根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通讯研究员、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研究领域:康德哲学暨德国唯心主义、政治哲学、韦伯与社会理论、当代中国思想、大学问题、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汉语哲学。出版研究著作六部,译著三部,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
先让我们对苏格拉底举的这个例子中的东西做一个简单的分类。“手指”属于“本体”(substance)范畴,而其他的包括“中间与两端”“黑和白”“粗和细”等都是“属性”或“偶性”(attributes/accidents)。如果对这些“属性”的划分再具体一点,那么“中间与两端”表示某种“位置”,“黑和白”“粗和细”都是“性质”,只不过“黑和白”是“相反者”(contraries),“粗和细”是“相对者”(relatives)。“相反者”和“相对者”是不同的。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每一个“相对者”都只存在于与对方的相对关系中,而“相反者”则指同一类事物中差异最大的。“相对者”中的每一个都不能单独地通过其自身而被把握或存在,而“相反者”中的每一个则必须能够单独地存在。亚里士多德虽然说在一些“相对者”中也有“相反者”,比如德性与恶相反,知识与无知相反,但是它们不是作为“相对者”而彼此相反的。 另外,就像James Adam注意到的那样,苏格拉底说在上述提到的所有这些事情中,是“多数人”而非“所有人”没有被强迫追问“手指是什么”。或许柏拉图在这里巧妙地暗示,还有一些灵魂非常敏锐的天才,他们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高贵的好奇心,即使在这样的感知中,他们也可以激发其理智。这也说明,以下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渡或者飞跃,可能对某些天才而言显得有些笨拙,但是它却可以更广泛地适用于更一般的人。 另外,视觉“从没有”(ο?δαμο?)提示“灵魂”,手指同时也是手指的对立面,这里的“ο?δαμο?”,Paul Shorey直接把它理解和翻译成“never”;它翻译成“at no stage”。他们主张柏拉图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心理学的过程(in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在这里,当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心理学“过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小心地把柏拉图哲学和现代的某种心理学或者现象学区分开来。哪怕柏拉图认为“灵魂”是能够“自我运动”的(而这遭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把“时间性”看作是我们意识或心理活动的一个特征。而亚里士多德哲学根本就不支持关于我们心理或意识活动的任何“过程”解释。因为,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灵魂”自身是不“运动”的。这样,虽然从某种意义上灵魂可以处于某种“潜能”状态,但是它的“实现”就绝不是一种“运动过程”,而是刹那完成的。就像Themistius解释的那样,“对于灵魂,所有的变化都不在时间中,它是独立的,而且它不是从潜能到实现逐步地发展,而是一切都立刻实现,就像视觉从白的事物转到黑的事物”。从“时间性”出发来理解我们的“意识”或者“存在”,这是一种非常反希腊哲学的现代“意见”。 读者对象:外国哲学专业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