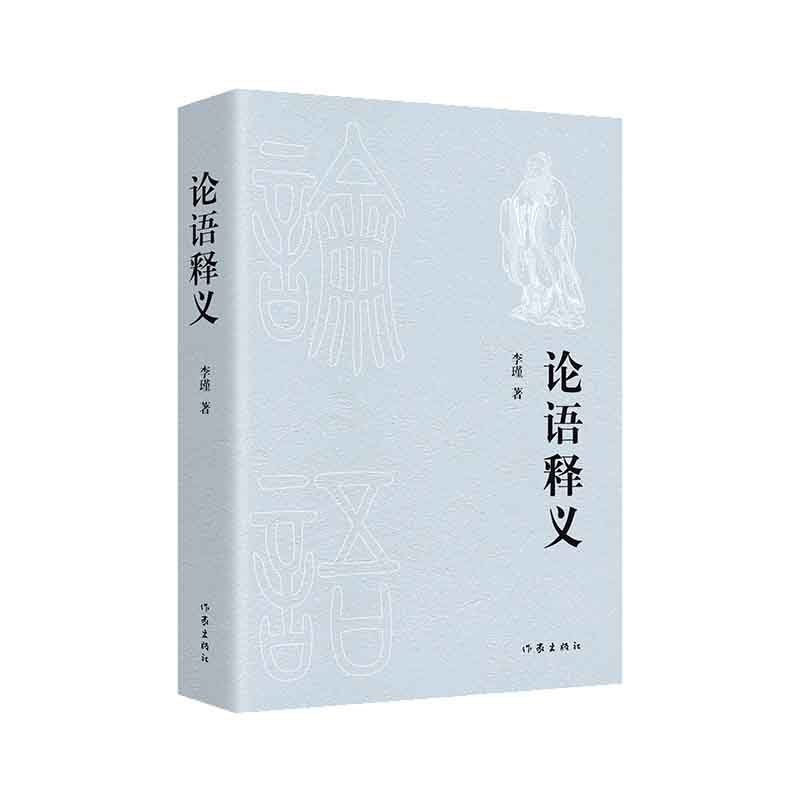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3.60
折扣购买: 论语释义
ISBN: 97875212197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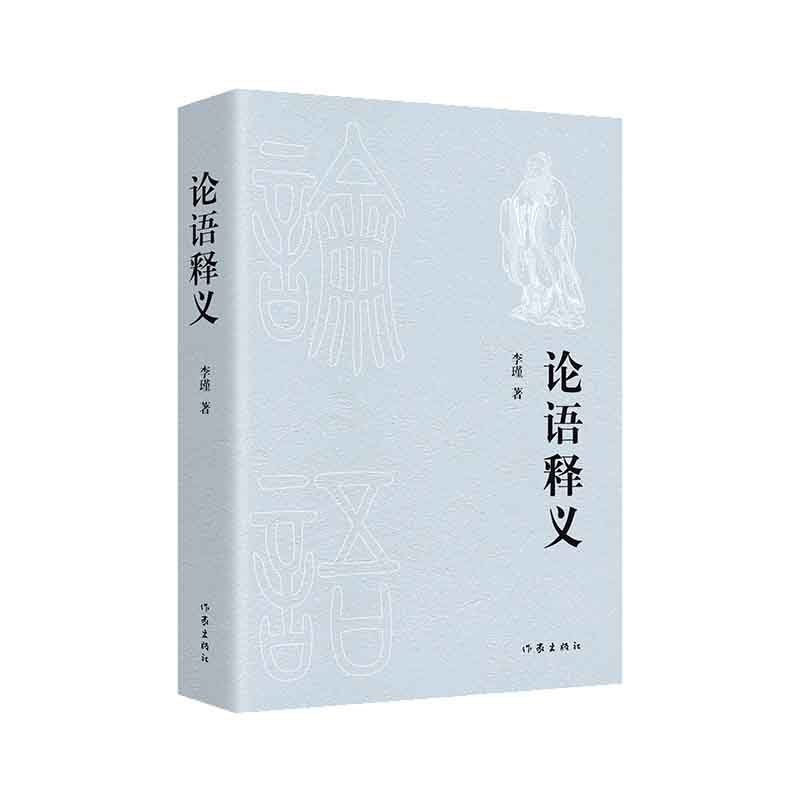
李瑾,男,山东沂南人,历史学博士。有作品在《人民文学》《诗刊》等报刊发表,出版“三释”“二录”“一裁”(《论语释义》《孟子释义》《山海经释考》《谭诗录——实然非实然之间》《观影录——我们如何逃离自己的身体》《纸别裁》),诗集《君子作歌》《倾听巴赫和他内心的雪崩》《落雪,第一日》《黄昏,闭上了眼》《人间帖》《孤岛》,故事集《地衣——李村寻人启事》,儿童文学作品《没有胳肢窝可怎么生活啊》等。
我一直觉得,《论语》可能暗含了某种“命运”关系,首章《学而篇》开宗明义谈“学”,末章《尧曰篇》以“君子”概括总结,是不是意味着“学”是《论语》之始之根,目的是为“君子”?首章首则以“人不知而不愠”,对应末章末则“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是不是意味着君子首先从“己”出发,然后及“人”的?上述感觉在写作《论语释义》过程中十分强烈,以至于认为这种对应里包藏了孔子的失败。 孔子之世,天下无道,民不聊生。当此关节,夫子把败乱的根源归结于人,特别是上位者,认为天下无道的主因在于上位者为政不以德、为国不以礼,且由于名不正,言不顺,导致“民无所措手足”。他的逻辑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一旦邦国有道,远人莫不归附。孔子要做的,就是将上位者培养成文质彬彬的君子,在他看来,“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上位者只要“无为”“恭己”,做个君子,就可以德化民,此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不过,君子并非只是针对上位者,而是包括整个社会中的所有个体,当然,孔子似乎也注意到这种要求过于空泛,故而将君子限定为精英群体,常常拿君子和小人对比说事。 如何做君子,或者说怎么培养君子,孔子的方案只有一个字,这就是“学”,亦即通过“学”确立人之为人和人之为政:人之为人的最高境界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人之为政的最高境界乃“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需要指出的是,儒学是一种秩序/关系学,孔子孜孜以求的是如何处理人与国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秩序/关系问题。其中,人与自己的关系处于整个问题的核心。这一点至关重要。面对失道失礼失乐之天下,孔子救时救世救人的出发点是反求诸己,通过回答“何为己”这样的终极性问题,解决何为人、何为政/国这样的社会性问题,亦即通过“为己”实现“为人”,通过“克己”实现“一匡天下”。 孔子之道,不外修身,这点确切无疑,但“修身”二字恐流于迂阔。若自他的思想体系中拈出一个统摄性词语,非“学”字不可。《论语》中出现“学”的有四十二则,计六十六次,出现次数比在《易经》《尚书》 《诗经》中合计起来多三倍。邢昺说:“学者,觉也”。毛奇龄说:“学者,道术之总名。”李光地说:“学字,先儒兼知行言。”上述讨论恐怕并没有抓住孔子思想的精髓或落脚点。在孔子这里,“学”并非没有目的,其价值指向是为“君子”,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孔子所谓学,只是教人养成人格。什么是人格呢?孔子用一个抽象的名来表示他,叫作‘仁’;用一个具体的名来表示他,叫作‘君子’。”《论语》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是开始,也是目的;人是器用,也是价值。孔子将“礼乐崩坏”根源于人,他的治理之道也在于成人,即通过内向求己之“学”,成人、为君子,达到入世的目的。不得不说,“学”为“君子”是《论语》的主体指向,邢昺讨论《学而篇》时即曰:“此章劝人学为君子也。”在中国文化脉络谱系上,孔子第一个将“学”和人统一起来,没有孔子,孟子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尸子的“学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荀子的“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恐怕都难以获得“立人”的价值指向。在孔子心中,学即人,人即学,“学”是区别于他者的核心之德,也是自我完善的必然途径。故而陈来指出:“‘好学’是孔子思想的一个具有核心意义、基础性的概念。”一句话,“学”是《论语》阐释的核心概念和中心思想,孔子将它推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正由于孔子,“学”成为千百年来志士仁人的一种超越性价值追求,可以不仕不贾,但“学”却不可须臾离之。 按照个人统计,《论语》中出现“君子”一词的有八十六则,计一百零八次,和“仁”出现的次数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在《易经》《诗 经》中分别出现了一百二十七次、一百八十六次。不过,《论语》中的“君子”和前经典的用法并不一样,出现了明显的语义迁移。孔子之前,划分君子的依据是人所处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政治地位,到了夫子这里,则是道德标准,故而“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上述迁移首先来自对“天”以“德”授命的认知,亦即政治观念的变更促进了“君子”含义的革新。周代商后,“德”成为“天命”归之的依据,在有识之士看来,只有“终日乾乾”,“君子”才能不失位。当“德”成为新的人才评价标准,君子不再是血统或地位的象征,而是一个拥有崭新德行精神的阶层和群体,进而提炼为一种规范性、理想化的人格要求。不得不指出,赋予“君子”新义是孔子顺应时代变化而进行的伟大创造,而《论语》则是第一部将君子平民化、精神化的经典作品。《论语》之后,《孟子》(七十七次)、《荀子》(二百八十五次)、《韩非子》(三十四次)中的“君子”已成为一种对成人的普遍规定。钱穆说,“孔子之教重在学。孔子之教人以学,重在学为人之道”。经过孔子发明,“学”就是“君子”,“君子”就是“学”,“学”乃中国文化繁衍不息、士人君子日用不辍的“道”。 《论语》中,君子是人格完美的典范,当“学”的目的在于让自己为“君子”,即成为个体的真正主人时,“学”不再只是认知性行为和求欲性活动,而是一种价值性行为和道德性活动。需要补充的是,“君子”一词蕴含着修己和治世两个层面,一方面修己为了心性,这是质;一方面修己为了治世,这是文。就“为心性”而言,孔子眼里的君子是安贫乐道的自得之士,他曾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种自得之乐被周敦颐称为“孔颜乐处”,突显的是君子的道德修养功夫。此一层面修己,根本的内涵是“仁者不忧”的破小我、成大我的生命境界,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超越日常生活的内心和谐追求。就“为治世”而言,孔子眼里的君子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有志之士。《荀子?王制》中的一句话可作为总纲,其云:“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在孔子眼里,管仲虽小德有亏,但其能匡天下,便可以“如其仁”,也就是说,利天下者方为君子。这种家国情怀、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是君子人格建构的重要内容。“为心性”和“为治世”是可以和谐地统一在君子身上的,这就是所谓的“达退之道”。 有一句话值得特别留意,即“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孔子这里,“我”始终是人生最大的问题和难题,为君子的关键是树我又去我,即通过修己以成人,树立起大我,将“我”与人区别开来,又要去掉小我、私我。邢昺对此有精当的理解,认为这句话“论孔子绝去四事,与常人异也。毋,不也。我,身也。常人师心徇惑,自任己意。孔子以道为度,故不任意”。孔子的去我并非无我,而是将“我”放在一个德性的场域中,而且这个“我”是需要不断学而习的,体现在“温故而知新”之日日新的过程中。正基于此,孔子始终把自己当作“学”的化身。孔子在世时,便“遭遇”了对自己的神化问题。太牢以为孔子是圣人,子贡则直接认为是天生的。孔子没有顺水推舟地自认,或沾沾自喜地默认,而是实事求是地认为,自己不过一个学习者,通过坚持不懈地学习,获得了各种技能。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不回避自己的低贱出身,也不以大师或圣人自居,这既是“学”的正确态度,也是“学”的结果。孔子为何强调“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无非是想提醒世人,通过自己的不断学习,可以成人、成君子,也正因为这一点,他获得了培养、辅佐上位者并教导他们“立己”为君子的“师者”资格。 青年作家李瑾解读《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