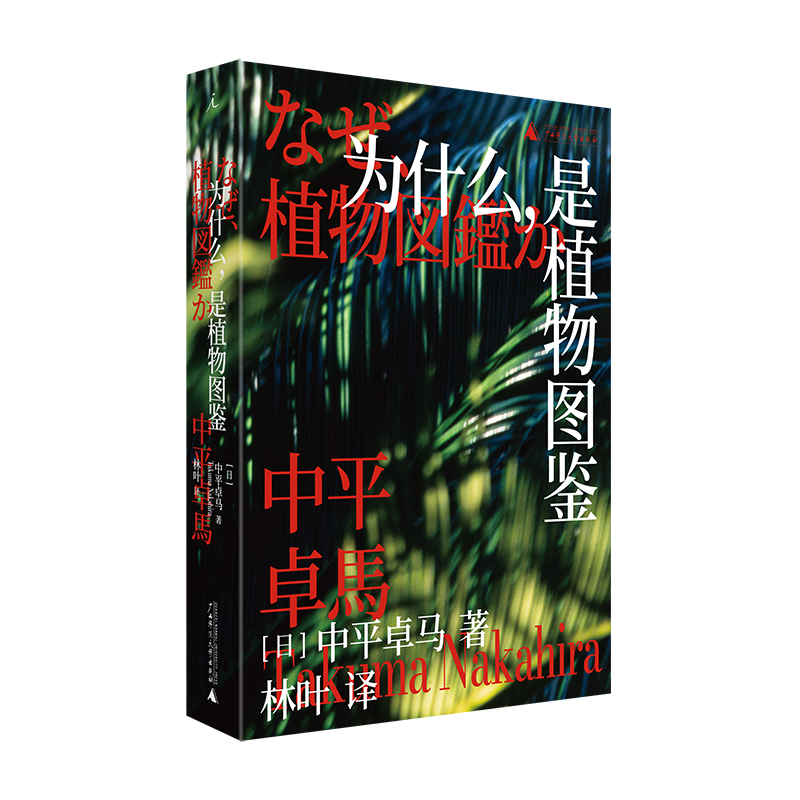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39.90
折扣价: 25.20
折扣购买: 为什么,是植物图鉴
ISBN: 97875598378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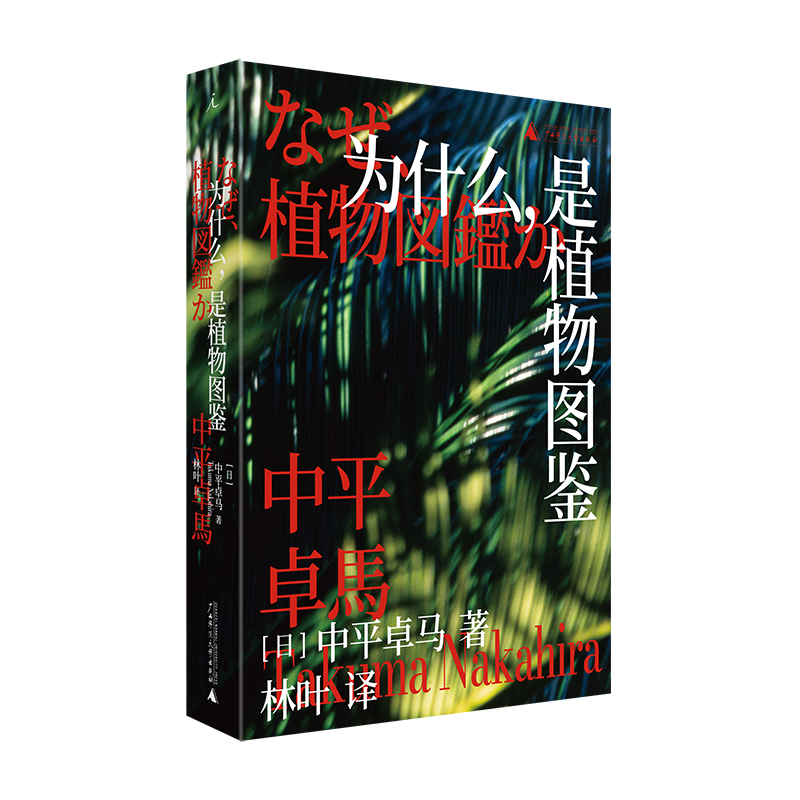
中平卓马,摄影家,摄影评论家。1938年生于东京, 1958年进入东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就读。毕业进入《现代之眼》担任编辑,1968年与高梨丰、多木浩二共同创办摄影同人志《挑衅》,对日本战后摄影产生重大影响。1970年出版摄影集《为了该有的语言》,翌年参加巴黎青年双年展。 1973年发表评论集《为什么,是植物图鉴》,宣布与摄影决裂,这本本也宣告他与《挑衅》时代的自己彻底诀别。在这本书出版之后,中平卓马将自己此前所有的摄影作品烧光。 1976年与筱山纪信于《朝日相机》共同连载 《决斗写真论》。1977年,因酒精中毒紧急送医,造成逆行性记忆丧失。此后,摄影遂成中平卓马作息般的生理行为,每天外出拍照,被称“变成相机的男人”。 2015年,因肺炎在横滨市某医院去世,享年77岁。
为什么,是植物图鉴(节选) 相机是什么?依据照相机而建立起来的逻辑又是什么?照相机是我们的观看欲望的具体表现,是历史性积累产生的一种技术,其本身应该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照相机将所有的一切对象化,通过隔离现实与自我的距离,让世界变为客体。将现实切割在四角形的边框之中,集中在一点之上,通过这样的方式,哪怕它只是现实中的一部分,也能够占有它。按照这个意思,照相机已经不可避免地承担起了以主体—客体这种二元论为基础的现代逻辑。然而,观看行为,在割断与身体的关系这一点上,是不成立的。撇开人是背负着身体活在这个世界这一事实,或者撇开观看这种行为,都是不成立的。于是,穿过世界、拓展这个身体,或者被身体化了的空间,这一切都构成了世界,而这个“记忆”,以及这所有的一切,全都是观看行为的实际情况。世界并非简单地靠自我就能逐渐被对象化的客体。这种说法,与我此前一直在谈的对事物和自我之间的那种绝对不和解性的确认这个命题是相矛盾的吗?也许并非如此。因为自我的视线、面对自我的视线而被抛投回来的事物的视线,这两者互相争斗的磁场才是这个世界本身。观看行为,这也是将自己暴露于他者的视线之下的行为。不过,在这样图示化地加以展示之前,我首先要确认那些绝不是我的东西的事物,确认那些因为是确实的事物所以才是事物的东西,我必须以此作为起点。也就是世界存在而我也存在的这一事实。 但是,照相机这个杰出的现代产物,打算以一点透视法为基础来统御世界。照相机片面地将观看行为局限于自我的眼中。因此,这体现的是一种管理世界的思想。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照相机从它诞生开始,不就是一种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方法吗?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质疑。确实,只要拿起一张照片来看,它呈现的都只不过是从自我这一点出发、单方面窥视到的一个空间而已。然而,并不是限定在一张照片里的空间,当考虑到以时间与场所为媒介的无数照片时,一张一张的照片所具有的透视法的意义便逐渐地被弱化。也就是说,因为这样的行为,那个以时间为媒介、无止境地超越并且被超越的东西,的确就有可能让世界的构造—包含世界与自我、那些二元对立的场域—逐渐变得明朗。其中,已经静止的自我与世界这种图式就消失了,并且逐渐被无止境地不断运动的无数视点结构化了。这个情况如果成功了的话,那么事态肯定会稍微发生变化。我仍然痴迷于摄影,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是如果从它的可能性来看,恐怕有一部分就是这样的形式。“日期、场所、行为”,是前年(1971年)我在某美术展览上所做的一次这样的表现行为。这个作品是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我不仅观看我所接触到的大量现实,而且是将其以照片的形式定格在底片上,有的时候连正在做这个事情的我自己也都拍摄成照片,并且每天都将这些照片展示出来。当然,由于当时想法上的不成熟以及物理条件的恶劣,这种思考方式本身并没有被明确地表现出来,但是,现在再来回顾的话,可以肯定的是,激发我的这一行为的可能就是前面我所阐述的那种情况。因为其数量的巨大而且超越一张一张照片中所具有的视角,所以即便无法超越,也努力让那些照片各自所具有的视角失去效用。简单讲,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吧。 可是,仔细想想,也可以说这种透视法的失效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维度上,正更广更深地渗透着。传媒惯常地向我们输送大量的影像,这些影像单独地来说,都是必须基于一个视角的东西,但是,如果是同一时间发出多种影像,而且从我们这一方—在我们所有的感受层面上来接受这些影像—来说的话,将这所有全都放在一个点上来接受的这种个人视角本身就不可能成立。譬如,电视上所放映的所有断片式的现实(毋庸置疑,由于它是断片式的,所以它不得不变成一种拟似现实),完全让我们混乱,把我们编排入一个有方向性的现实之中,再加以重组,换言之,从根本上夺走那个不断被意义化的过程。从新闻到家庭剧、做菜的时间、运动,并且见缝插针地插播简短的商业广告。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或者基于什么样的视角来逐一赋予它们秩序,对它们进行组织才好呢?内村刚介非常恰当地将今天活在这种现实中的我们称为“历史的消费者(顾客)”。 …… 为什么,是植物图鉴呢?到这里为止,我一直是通过回应针对我的批评信件的方式,迂回曲折、左右摇摆地说明了我自己为什么无法再以以往那种形式来拍摄照片,或者我为什么对那样的照片感到腻烦,以及虽然结果上是无意识的但是“诗意”却从我的照片中丧失等这些情况。尽管我采用了对来信者的回应这种体裁,但这当然是对我自身的确认。总之,抛弃意象,面对真实的世界,正当地确定事物作为事物、自我作为自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这才是我们以及这个时代所必须要表现的事情。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排除通过自我对世界的拟人化、情绪化这种行为。而且,一般的、抽象的言说已经没有必要了。倘若如此,那自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此外,这种行为通过摄影这种方法是否可能呢?接下来我们必须要探讨这种更加具体的问题。 …… 最重要的是图鉴。就是鱼类图鉴、矿山植物图鉴、锦鲤图鉴这种常见于儿童读物中的图鉴。图鉴的最大功能就是清楚地指出这个对象。图鉴拒绝形成任何阴影,拒绝任何情绪潜入其中。“悲伤的”猫的图鉴是不存在的。只要图鉴稍微有一点暧昧的成分存在,那么图鉴的功能就无法实现。所有物品的罗列、并置是图鉴的另一种性质。图鉴绝不是对某个事物加以特权化,并以它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整体。也就是说,存在于那里的部分不是渗透到整体的部444444444分4,部分始终只限于部分,它的对面则什么都没有。图鉴的方法就是彻底的并置(juxtaposition)。而这种并置的方法,则必须是我的方法。此外,图鉴描摹的只是发光事物的表面,至于进入到事物内部,探寻其内部的某种意义,这种粗俗的好奇心或者我的骄傲自满,图鉴是彻底拒绝的,它是因为让“事物就是事物本身”这一事实变得明确才成立的。这也必须是我的方法。 图鉴在本质上必然不接受诗意或者“模糊”“薄暮”。所以,图鉴或许和商品图录比较相似。商品图录也排除所有的暧昧性,只是直接指出商品。如果商品没有被一丝不苟地拍摄下来,那么商品图录的功能就无法实现。模棱两可的商品图录,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是一种逻辑矛盾。 那么为什么是植物呢?为什么不是动物图鉴、不是矿物图鉴,而是植物图鉴呢?动物的话,腥气太重了;而矿物质则与生俱来地拥有“彼岸的坚固性”的优势。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就是植物了。叶脉、树液等这些东西保留着与我们的肉体相似的元素。归根到底,这就是有机体。处于二者之间,以意想不到的弹力,窜入我内心的就是植物。植物之中尚还保留着某种暧昧性。捕捉植物所具有的暧昧性,最大限度地明确区分出植物与自我之间的界线,这就是我私下构想的植物图鉴。前面提到的《诉讼笔录》的主人公亚当·波洛,在某一个夏日和女性朋友一起去海边游泳。亚当的后背长时间曝晒在太阳下,但却一声不吭。他的女性朋友突然和他说话。漫长的沉默被打破了之后,亚当突然发出了怒吼:现在,只差一点点我就能进入矿物的阶段,明明已经非常确定地进入植物阶段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让自己变成一个世界上的石头。这样就和某个小石块、叶子、波浪以及其他种种事物并排在一起,将自己变成一个事物。这终究是不可能的。因为自己被意识这种病魔所侵袭。但尽管如此,意识行为已经不是人们始终相信的那种世界之王。因为意识行为,就是我把自己当成是他者发出意识活动的行为。或者说,把自己当成他者发出意识活动的行为,就是自己意识到他者、意识到事物的反映。 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通过植物图鉴来重新开启我的工作。我用彩色照片来捕捉阳光下的事物,收入到植物图鉴之中。无论如何这都必须是彩色照片。因为,我已经将我前面所说的黑白照片的暗房操作中所具有的“手的痕迹”抛弃得一干二净。而这只手才是一直让艺术得以成立的东西。手,这就是自己身上的他者。不过,虽然如此,手还是自己的。用手来操作、被操作的东西,这些毕竟都是手的延伸。世界是用手来把握的。在干脆明确地将它截断这一点上我的植物图鉴就成立了。在这个意义上,彩色照片已经是彼岸之物了。 按下快门,一切因此结束。 1、“变成相机的男人”:《Provoke 挑衅》创刊人、森山大道“最爱的宿敌”,摄影的思想者与实干家如何用人生回应摄影的意义。 2、“阅后即焚”:是什么,让中平卓马宣布与摄影决裂,将自己的所有摄影作品烧光?为什么,是植物图鉴?推翻自己的激进宣言,风格秀异的摄影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