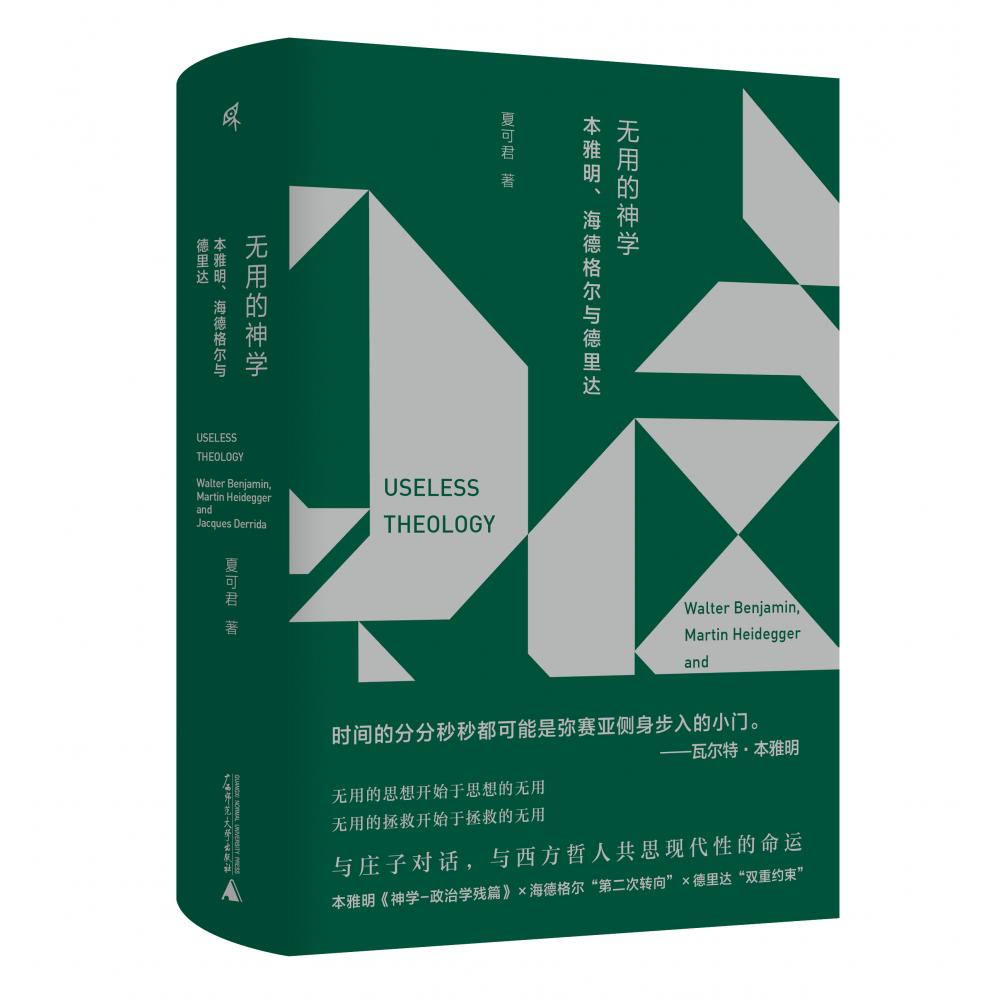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2.00
折扣购买: 无用的神学:本雅明、海德格尔与德里达
ISBN: 9787559850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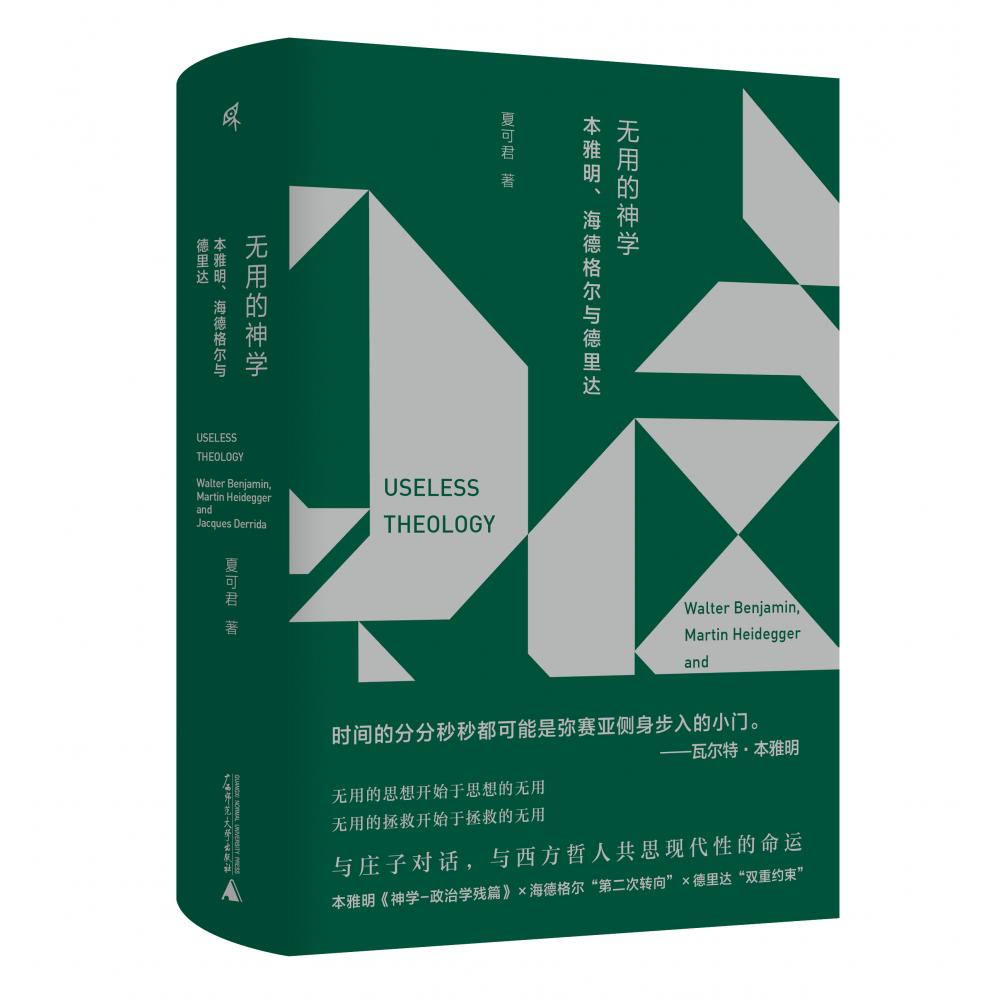
夏可君,哲学家,评论家与策展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曾留学于德国弗莱堡大学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述十余部,从“无用”出发,撰有《虚薄:杜尚与庄子》《庖丁解牛》《一个等待与无用的民族:庄子与海德格尔的第二次转向》《无用的文学:卡夫卡与中国》,以及英文著作Chinese?Philosophy?and?Contemporary?Aesthetics,?Unthought of?Empty。 夏可君尝试让“无用”“虚化”以及“余让”等中国范畴,生成为当代世界哲学的核心概念。
本雅明的无用教义 在《论历史的概念》的第二条中,本雅明写到了幸福与救赎的关系: 我们关于快乐的观念和想象完全是由我们生命过程本身所指定的时间来决定其特性和色彩的。那种能唤起嫉妒的快乐只存在于我们呼吸过的空气中,存在于能和我们交谈的人,或本可以委身于我们的女人身上,换句话说,我们关于幸福的观念牢不可破地同赎救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这也适用于我们对过去的看法,而这正切关历史。过去随身带着一份时间的清单,它通过这份时间的清单而被托付给赎救。过去的人与活着的人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我们的到来在尘世的期待之中。同前辈一样,我们也被赋予了一点微弱的救世主的力量,这种力量的认领权属于过去。但这种认领并非轻而易举便能实现。历史唯物主义者们知道这一点。([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266 页。) 没有比这个第二论题更接近《残篇》主题的了:接续第一条讨论弥赛亚救赎对于历史的任务或者服务,弥赛亚与现实历史发展及目的不相干,因此就是无用的。确实如这里指出的,神学似乎已经彻底看似没有什么可认识性,而且很丑陋不入法眼了。但是,本雅明还是相信,神学可以帮助历史唯物主义,如陶伯斯敏感指出的,因此,弥赛亚王国与世俗世界的不相干,需要幸福作为中介来转化,需要唤醒或者触及自然的沉默。难怪阿多诺会认为整个文本写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而且这里提到“委身于”女性的身体,还提到“呼吸”——这不就是更自然化的躯体?甚至就如同《拱廊街》提到的母性,女性的弥赛亚(female Messiah, la Mère)? 这些微弱的弥赛亚力量,试图在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弥赛亚救赎的断裂之间,找到微弱且碎片化的联系,那些闪烁的余光或火花。这个微弱的联系,就是本雅明思想的当代意义,但已经不再是微弱的,而是无用的弥赛亚性。 弥赛亚的自然化, 犹太思想的道家化, 还体现为本雅明与布莱希特在逃亡过程中的自我转化。布莱希特1938 年在流亡途中写出了题为《关于老子在流亡途中著〈道德经〉的传奇》(Die Legende von der Entstehung des Buches Taoteking auf dem Weg des Laotse)的十三节诗歌,认为这是生命保存的钥匙之诗(Schlüsselgedichte)。而本雅明则专门回应,并强调了道家“友善”的重要性: 一个中国先哲曾说:“大学者、大文豪们曾生活于最为腥风血雨、暗无天日的年代,但他们也是人们曾见过的最友善、最开朗的人。”这个传奇故事中的老子不论走到哪里,不论在何处停留,都始终在传播这种开朗与欢愉的氛围。他骑坐的公牛是欢快的,尽管它驮负着老者,这却并未妨碍它去愉快地享用新鲜草料。他的牧童是快活的,他坚持用干巴巴的言语来解释老子的贫穷:“他是位教书师傅。”身处关卡横木前的税吏是快乐的,正是这种快乐才激励他去高兴地询问老子的研究成果。如此一来,这位智者本人又怎么可能不快乐,若他不快乐,他的智慧又有何用?([德]本雅明:《无法扼杀的愉悦》,239-240 页) 而且本雅明还相信,此道家“友善”的姿态,一点也不亚于犹太教的弥赛亚精神:“你懂的,被战胜的乃是坚硬之物。”(即“以柔克刚”)这也来自老子“水之运动”,这是道家的智慧。本雅明甚至认为:“老子如此的教谕诗,如同预言一样振聋发聩,一点也不比弥赛亚的言说差!这句话,对于当今的读者而言,却不仅包含了一个预言,还包含了一种训诫。” 改写后的老子式教谕诗,也是本雅明自己梦想的教义式精神,在这里,道家的教义其实已经与弥赛亚性关联起来,弥赛亚已经更彻底地道家化,革命的方式也柔和化了。在被迫流亡途中,本雅明与布莱希特不约而同把自己的生命逃避方式想象为老子式的自由逃逸, 以此逆转不可承受的历史灾难。或者,这也是一种消失于图像的方式,老子出关——离开这个世界——以便消失在自己留下的箴言之中(处于革命艰难困苦时期的鲁迅在上海也创作了《出关》), 因此也才让布莱希特与本雅明如此着迷。 1.这是一本既残酷又温柔的哲学奇书,书中处处都弥漫着现代性状况下的绝望气息与危机氛围,却又处处昭示着绝处逢生的可能性。你在本书中将体会到的可能不是哲学家们仿佛领受天命般的“大师气象”,而只有一个个挣扎着寻求救赎的灵魂,以及他们进入思想深渊的勇气,或许这才是思想的动人之处。 2.在中西之间和现代各种哲学思潮之间的比较与对话,使得本书充满思想激荡的活力。本书的核心议题从本雅明1920年代的哲学手稿开始,而我们的时代与整个1920年代的生命哲学思潮相关,从叔本华到尼采,从西美尔到舍勒,从狄尔泰到卢卡奇,从巴霍芬到克拉格斯,从弗洛伊德到荣格,甚至,对于庄子与海德格尔,本雅明都有着内在对话。从本雅明《神学-政治学残篇》出发,本书展开了极为丰富的现代哲学思想路线图。 3.夏可君师从邓晓芒和让-吕克·南希,接续中国现代哲学和法国解构主义哲学的思考,把“无用”“虚薄”“余让”等中国范畴带到世界哲学论坛上,切入对现代性的批判,回应现代性的危机和困局,其思考具有启发性。 4.无论是陷入内卷还是选择躺平,现代人都需要心灵的安顿。本书的思考无疑是为了寻求当代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并不提供心灵鸡汤式的安慰,而是按照哲学的严格要求,不断追问现代性的根基,提示现代性的陷阱,甚至突入精神的绝境之地,经过各种思想实验,打开通道,来培育生命灵根的种子。阅读本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精神的复苏和情感的舒展。 5.本书对现代德国、法国哲学精华文本的翻译与注释,对于相关研究领域的学生有较好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