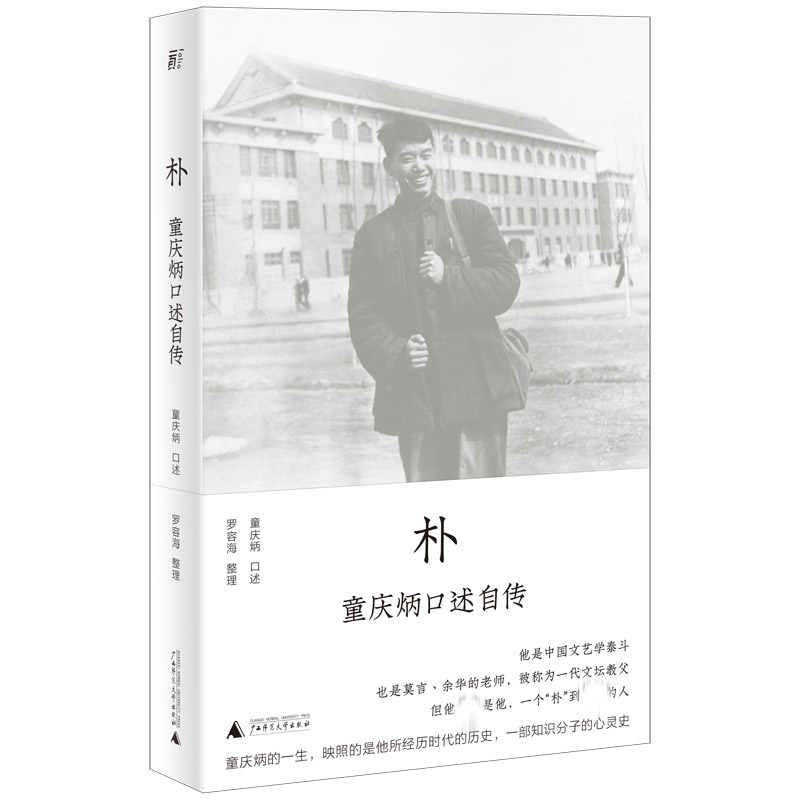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3.50
折扣购买: 朴:童庆炳口述自传
ISBN: 9787559844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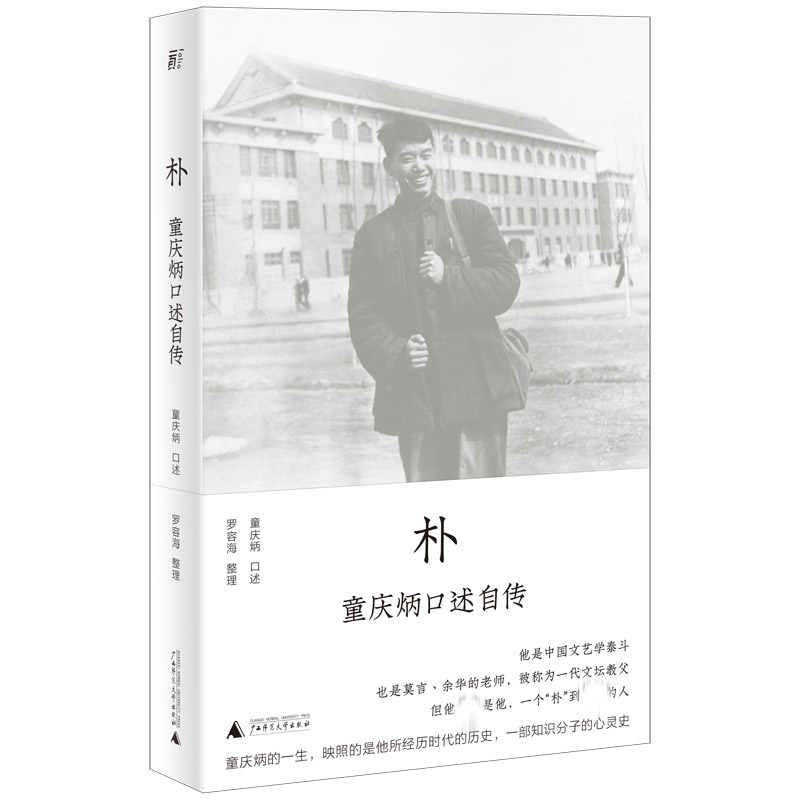
口述|童庆炳(1936—2015) 中国文艺学泰斗,被称为中国文坛“教父”。 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毕淑敏等都曾经是他的学生。 整理|罗容海 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但是,在这么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贫穷伴随着我,而且时刻剥夺我学习的权利。现在想想,我能够到北京来读书,留在北师大,成为教授,现在还给我评了个资深教授,愉快地跟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一起谈论学问,纯粹是偶然。因为从小我的理想就是每天能让家里人有五斤米下锅。我们家老少三代,七口人,每年到了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这时候父母就要吵架,因为第二天没有东西下锅,连南瓜和番薯(白薯)也吃光了。 我大概三四岁时,有一次得了大病,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肺炎。当时发高烧,老是不退,咳嗽不止,眼看就不行了。祖母在我的床边一直求,求祖宗、上天、各种菩萨,“求求你,我老了,你们让我去,千万不要让我孙子去!”呼天抢地,这是我幼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所以,从小我就知道,祖母对我的那种爱和亲,我是永生难忘的。后来我每次回家,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给祖母扫墓。 在上海停留了一天,有一个人留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我们另外三个又买了慢车票上北京。这慢车从上海出发,要三天三夜才能到北京。这车是所有的小站都要停,农民种地挑着肥上来,下一站下车去施肥。 经过十五天的跋涉,我终于从福建西部小小的连城县来到了北京城。到北师大之后,我母亲担心的那些问题都解决了。我报名之后,学校总务处说,只要写个申请,要什么就给发,比如棉衣、绒衣——当时普遍还没有毛衣,就穿绒衣,红的绿的,各种颜色都有——一身的棉袄、棉裤、棉帽子。当时我正年轻,有这些就很满足了。 关于1957 年的“反右”斗争,大背景不讲了,说说我们班和我是怎么参与的。我们先听到的传达文件,是给党提意见, 和风细雨,要鸣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当时我在班里担任团支部书记,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因为党是要通过每个班的团支部来引导学生。在鸣放阶段,我自己可以说六神无主,不知道怎么做,是响应党的号召,召开鸣放会,让同学们对党提意见, 还是不开会,不让同学们胡说,我隐隐感觉夸大其词会犯错误。 为什么我当时会有这样的觉悟?因为我们班有一个党员,是个老大姐,1937年的老共产党员,党龄和我的年龄就差一岁,是当时我们班的调干生。她当时是我们年级党小组的组长,我事事征求她的意见。就鸣放会的事,我问她开还是不开,她说不开。我说别的班都开了,就我们班不开,同学们都有意见,说我们对党的整风消极怠工,我怎么应对这些质疑呢?她说你别理他们,第一,绝对不主动开鸣放会;第二,要是班里哪个同学贴了什么大字报,你就去把它给撕了。我当时很年轻,才二十几岁,根本没有经验,当时只是觉得这个老大姐很正派,后来才知道1955年评军衔的时候就给她丈夫评了中将军衔。她说不要开,我们就没有开。凡是看到我们班同学写的大字报,我就都给撕掉。 往事如烟,还是往事并不如烟,现在不同的人说法不同。我是同意往事并不如烟的。我的这种看法,不是随便附和别人的意见,它源于时不时地会涌上心头的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往事。 那时候大字报贴在哪儿呢?在西饭厅那。当时北饭厅西饭厅东饭厅连在一起,现在都成邱季端体育馆的一部分了。从东饭厅出来到北饭厅有一处拐角,那里正好可以挡住风,大字报就都贴那里。那时候贴大字报,中文系是最积极的,特别是大三、大四那些高年级的,他们还有组织,叫“底层之声”“苦药社”等,甚至写章回小说,揭露党委书记如何跟女学生有暧昧关系,就这一类事情,搞得很热闹,我们每天都等着他们新的大字报。 当时我们天天围在西饭厅那,那里又称为枣树林,现在仅剩四棵枣树——我看这四棵也不一定能保住。枣树林是我们辩论的地方,看完大字报进宿舍之前,就在那里辩论。有的人为了突出自己,搬个椅子,站在上面发表演说。我们都是听众。我们班里有几个同学贴了大字报,甚至在《人民日报》6 月8 号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对这社论不理解,还贴大字报, 但这些大字报我一一都给撕了。 就这样,我们班在1957 年没有一个人成为“右派”,因为我们的鸣放会是在《这是为什么?》发表之后开的。《这是为什么?》发表后老大姐对我说,鸣放会可以开了。我们开了三次, 大家不敢说一句话,提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一个年级四个班,唯独我们一班没有一个“右派”。 后来在总支档案里,我看到我们全班都被划归一个等级, 叫中中。当时分为五等,即左派、中左、中中、中右、右派,到了右派就是敌我矛盾了,中右还不是。我们全班都在中中,这就是说我们的政治面貌不清,因为我们之前没开鸣放会,没有说话,没有贴大字报。而别的班,像三班,出的右派是最多的, 抓了五个还是六个。后来大家回过神来才有体会,说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当得真是太英明了,没有开鸣放会,最后全明朗了才开。我说:“不是我英明,都是老大姐的主意呀。” 再往后就让我们班去参加别的班批评右派的会议,每个右派都要被批判得死去活来。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昨天是同学, 今天就成为敌人了呢?很难讲得通,怎么能这么做呢?于是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当时上面已经给我们每个班派来辅导员了, 我们班的辅导员说:“你们要积极一点,这是政治斗争。”我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昨天还是同学,今天怎么就成为敌人了呢?我们说不出来批判的话,不知道怎么开口。” 那位辅导员也是个年轻的老师,他告诉我,“如果这个右派说党不民主,你只要反问他一下,‘难道我们党是不民主的吗’,这个你会不会说?”我连忙说这个会。我们就用这个套路,到二班、三班等各个班去,于是我们的批判就变成了各种重复加提问:“难道事情是这样的吗”“难道事情是那样的吗”,一路反问下来,只有这一招,从来没有给别人扣过帽子。这也是那个老大姐教导我们的,不要那么激烈。 但是事情还没了。当时划右派是有指标的。我们班也分到了指标,指标怎么下达的,我作为基层党员还了解不到,甚至连党委的某些委员也了解不到,只有党委书记、副书记和总支书记这几个人了解。所以我们班最后也不能都是中中,要根据反右派斗争的表现,分个五等。结果还是没有划出“右派”,大部分人是中中,个别的人被划成中左,有三个人被划成中右。这三个同学都是有人揭发,按照当时的政策,中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要承认错误,做个检讨,就过关了,依然可以毕业分配工作。 他是中国文艺学泰斗 也是莫言、余华的老师,被称为一代文坛教父 但他首先是他,一个“朴”到极致的人 童庆炳的一生, 映照的是他所经历时代的历史,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他出身于贫寒,但有一位伟大的祖母 童先生是苦孩子出身,家里穷到他从小的理想是每天能让七口之家有五斤米下锅。而为了支持自己的孙子近乎奢侈的读书梦,祖母不惜拿出积攒了一辈子的棺材钱来给他交学费。更重要的是,她向他的生命注入的善良,让他对意识形态的狂热免疫,在政治正确卷席一切的时候能守住人性的尺度。 ■当历史走起弯路,他拒绝着历史的道 底层者特有的强烈上进心,让童先生得以从山区来到北京,但他并不盲目地追求进步。于是近乎奇迹的是,他不仅从未在运动和斗争中整过人,保持了人格的清白,还绕过时代去到国外,为自己赢得暗地里读书的时光。这里面有运气的成分,但更主要是因为他在关键时刻作出的两次关键抉择。 ■他首先是大师们的学生,其次才是泰斗 在打倒孔家店的氛围中,童先生依然维持着对老师的古老的尊崇和感恩,不仅尽可能地保护他们,更从他们的身上汲取营养,获得做学问和做人的启示。正是靠着这种擅长当学生的能力,他才能为自己打下深厚的基础,不断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几乎靠一己之力为中国的文艺学理论奠基。 ■他还有一支小说家的笔,这让他得以成为大师们的老师 童先生会让人不禁联想起大批评家乔治·斯坦纳,虽然他的小说无法如学术那般给他带来公众声誉,但它们可以表明童先生绝非所谓理论的生产者,而很少有学者像他这样保持理性和感性的平衡。正是凭借这样的全面,他才不仅有一批理论家弟子,还有一些已经进入大师级的作家弟子,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