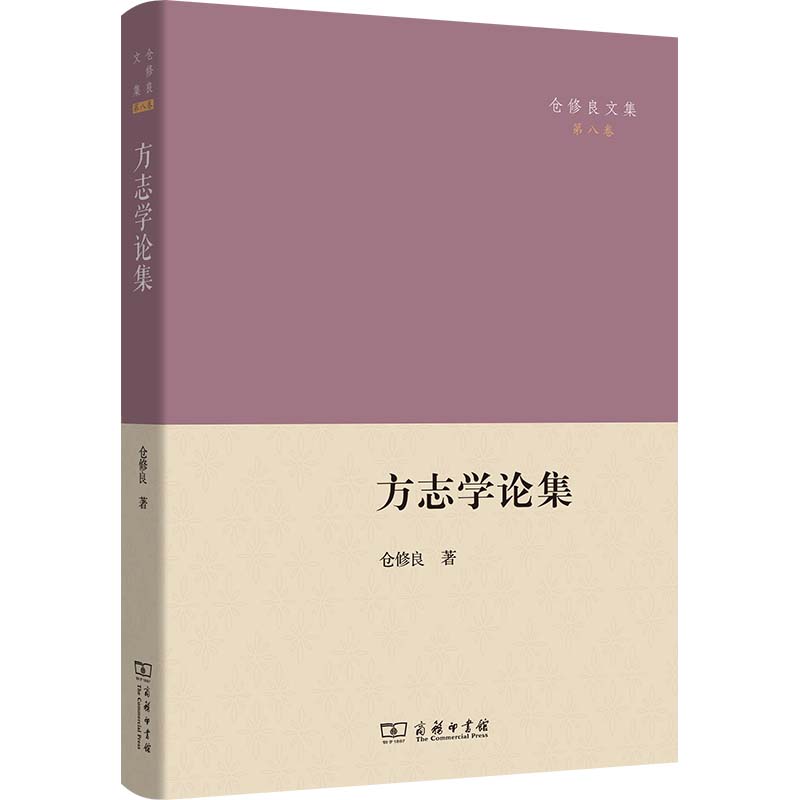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160.00
折扣价: 126.10
折扣购买: 方志学论集/仓修良文集
ISBN: 97871002439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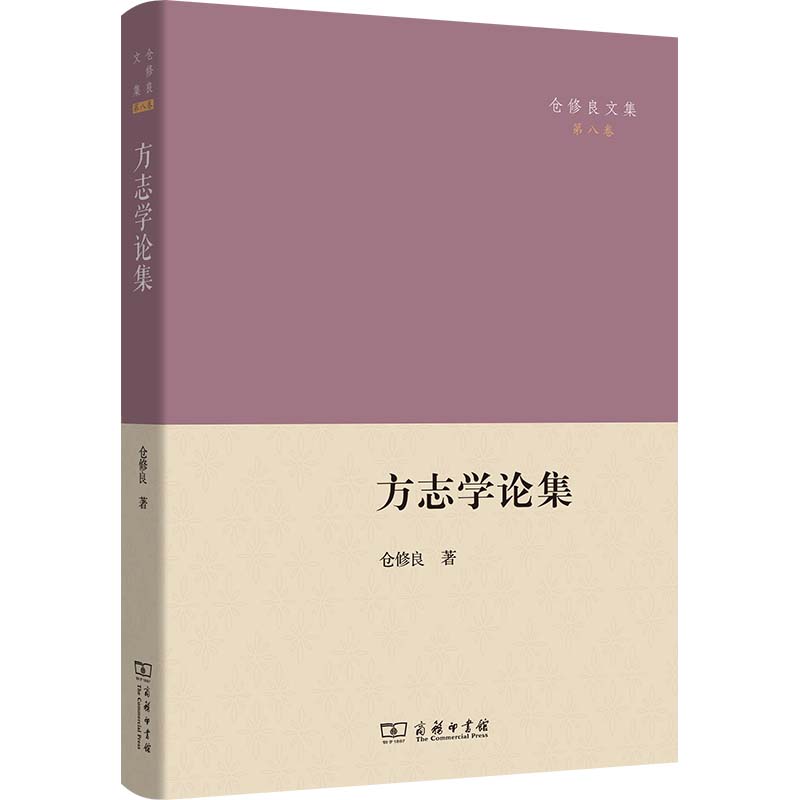
仓修良(1933-2021),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浙江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宁波大学、温州大学兼职教授等。毕生致力于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方志学、谱牒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节选) 编修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自从两汉产生方志以来,由于历代统治者对这种地方著作的重视,故每个朝代都曾明确规定,各个地方政府都必须按时编修,及时进呈。特别是自隋唐以来,直到民国时期,从未中断。对于这些规定,史书都有记载,可谓有案可查。有些规定就连编写内容要求都明确提出,这就有力地保证了我们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特有的文化发展现象能够得以代代相传而不衰。尽管其内容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充实,体例也不断地完善与更新,但是作为方志所固有的特点却始终保持着不变。对此经久不衰的著作形式,国外学者研究时无不感到惊叹。当然我们也必须说明,这种著作形式与其他文体一样,绝不是成于一朝一夕,也不是成于某一人之手,而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开始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善。它和谱学一样,都是史学发展中所产生的旁支,并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形成,乃至最后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方志学。而在方志发展的过程中,曾经经历过地记、图经、定型方志三个阶段,在这不同的三个阶段中,不仅名称不同,而且服务对象也不同,并且都还有着不同的特点,特别是都不同程度带有各自产生的时代烙印。正像我们今天所编修的新方志,它必然要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这不仅体现在观点上,而且还会反映在体例、内容、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唯其如此,要想探索出方志的产生和发展规律,总结出不同阶段的特点,势必要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比较研究和分析,才有可能收到比较理想的效果,而绝对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对此,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有过论述,一定的学术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作用并影响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因此不同时代,总是要出现为这一时代服务的学术文化思想体系、学术流派以及相应的各种学术著作。这就是说,文化这种精神生产,都一定建立在特定的物质生产上,并与当时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无论研究哪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或哪种著作形式的产生,都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都必须同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过程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这样既注意到它与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又不能忽视学术文化本身的渊源和发展过程,这就是马列主义文化反映论。对于史学界的朋友来说,长期以来大家都是遵循着这一理论进行各自内容的研究,大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然而,方志学界有些人在研究方志起源的时候,却持背道而驰的观点,他们脱离社会发展条件,抛开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重要社会因素,孤立地抱着某部书来谈方志起源,因而有所谓方志渊源于《禹贡》说,方志渊源于《周官》说,方志渊源于《山海经》说等等。至于为什么渊源于这些著作,实际上连主张此说的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就以说法最多的《周官》而言,这部书实际上是战国时期人所作的一部古代官制的汇编,完全是凭想象而作,有许多官名,古代根本就没有实际出现过。试问作为方志著作怎么会起源于一部官制汇编?问题是《周官》中曾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这样的条文,他们就抓住这点,硬说方志起源于《周官》,这实际上是天大的误解。著名学者黄云眉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发表了《略论〈周礼〉五史与〈礼记〉左右史》一文,否定了《周官》所载“五史”之说,其结论是:“准是以言,《周礼》五史,可信者惟大史、内史;《礼记》二史,可信者惟左史,天子有大史、内史、左史等,诸侯皆有大史而不皆有内史、左史。其职掌亦不必与《周礼》、《礼记》同。若其因大史而有小史,因内史而有外史,因左史而有右史,因《周礼》之无左右史,而以《礼记》之左右史,强与《周礼》之大史内史冶为一炉,皆由前人以理想构成制度,而后人以文字认为事实,故纷纷藉藉而终莫能通其说也。然则所谓粲然大备之周代史职,夷考其实,盖亦廑矣。”可见外史、小史实际都是子虚乌有。而该书中所云之“四方之志”、“邦国之志”的“志”,乃是指史而言,指四方诸侯国的历史,这都是历史常识,我在《方志学通论》一书中已有详细论述。既然如此,方志渊源于《周官》之说的依据自然也都成了泡影。我们讲了,学术著作、学术思想既是各个时代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总要为特定时代服务,方志编修自然也不例外,这就是方志发展过程中所以会出现明显的阶段性,产生不同的特点和名称的原因所在。对此,方志学界以往却很少有人研究,似乎产生的各个阶段、不同名称乃至各种特点,都是理所当然,并无研究之必要。其实研究这些,既要有深厚的学术基础,又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代价。 方志,顾名思义,是以记载一方之事为内容的地方性综合性著作。其名称,较早时候史学家称之为“郡书”、“郡国之书”、“郡国地志”,这就是说是记载以地方行政区划郡县为范围的著作。后来的发展,也正是沿着这样的道路。所以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因而就有府志、州志这一类名称。众所周知,我国的郡县制度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在全国推行的。既然如此,那么在郡县制度尚未确立之前,自然就不可能产生反映这种制度的著作。正像在共产主义尚未到来之前,谁也无法写出一部反映共产主义社会的著作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尚且要摸着石头过河,自然就可想而知。所以,我认为在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代要产生这种性质的著作都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没有产生这种著作的温床。同时还应当看到,秦是个短命王朝,建立仅十多年便被农民起义推翻,在其存在的短短十多年中,也一直处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连一部史书也无人修过,哪里还会去编修郡县志呢?汉承秦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代,社会经济得到空前的繁荣,这就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了西汉后期,特别是东汉,地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豪强地主势力不断壮大,这就为产生地方性著作创造了温床。从这个时候开始,各地先后产生了许多地方性的人物传记和地方性的地理著作,经过两者汇合,从而形成了地方志雏形之地记。因此,我们说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特别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这种著作非常盛行,这同当时的门第制度的流行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门第制度需要标举郡望,以显示自己门第的高贵,因此,单纯夸耀本地人物出众显然还不能满足要求,还需要宣传产生这种杰出人物的地理条件的优越性。于是那些单写人物的传记已经不能满足这个要求,这么一来地方性人物传记与地方性地理著作两者遂走上结合的道路,从而产生了第三种著作形式——地记。 我们说方志起源于两汉,除了从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当时的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和研究外,还有确切的史书记载为依据。《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小序曰:“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这段文字共讲了三层意思:第一,东汉光武帝刘秀,为了表彰乡里之盛,诏撰了《南阳风俗传》,其内容皆为这里的人物、风俗、山川、物产、名胜等,这么一来,各地都争相仿效。第二,“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意思是编写郡县方面的著作,从这个时候便开始了,在这里国字是指县,“郡国之书”就是郡县之书。第三,这种著作开始时亦多由史官而作,故称“史官之末事”,所以这种著作亦是史学的一个支流。文字虽然不多,作用却是很大,它确切地记载了方志的起源。本来方志的起源问题早就不成问题,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和史念海先生,也都早就提出方志起源于两汉地记。令人不解的是,方志学界有些人宁可不相信正史之记载,却偏偏将《周官》奉为经典,这当然已经不是什么研究方法的问题了。如此研究何以取信于人!嘉靖《山阴县志》的《述志》曾这样讲:“夫自禹裔绝封,秦皇肇制列县称名,张官置理,分合代更,群职联叙,志为邑而作也。”这就是说,由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度,派官吏治理,郡县之划分也常有变更,于是为一邑而修的志书也就产生了。看来这位《述志》的作者确实很有点见解,他能够说出邑志是产生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以后,很显然比我们今天有些方志理论工作者还来得高明。 当然,我们应当知道,地记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为世家大族服务的,所以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就曾明确指出:“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这就说明,那些世家大族们为了显耀各自门第的高贵、郡望的优越,以维护其门第制度下的特权社会地位和权益,都纷纷撰写各自地方的地记,所以我早在《方志学通论》中就已经指出:谱学和地记,是为了维护世家大族利益,巩固门第制度而形成的两种史学方式。它们产生的社会条件和肩负的任务都是一致的,都是世家大族所建立的庄园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可以说是一根藤上结出两个不同形状的瓜。可见到了魏晋南北朝,史学所以会衍生出两个旁支—谱学、方志,绝不是出于偶然。当时的社会现实既向人们提出了要求,同时又提供了产生的土壤和温床,这就进一步说明,地记乃是时代的产物,它负有时代的使命,因此,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它的产生,绝不是凭空而降,而是有本有源。那种脱离时代背景,孤立地用某部著作来说明方志的起源,不仅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而且是徒劳无益的。总之,郡望观念是在门第制度下产生的,标举郡望,则在于显示门第的高下,而门第的高下,与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宣传郡望的优越,以巩固门第制度,这就是地记产生后所肩负的社会使命。这里我们也告诉大家,“人杰地灵”的思想观念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到了唐初王勃在《滕王阁序》将其概括提出以后,影响非常深远,后来方志定型以后,许多方志作者仍相沿袭而不改,尤其是如今许多新编修的地方志中,为了表述本地人才出众,照旧在说在于“人杰地灵”。可见当年为世家大族服务以夸耀本乡本土为著述宗旨的地记,其思想影响居然会如此深远。我们认为某地是否会产生杰出人物,绝不单纯取决于地理环境是否优越,穷山恶水之乡,照样会产生许多英雄人物,这是无数历史事实都足以说明的。因此,对于传统著作中许多观点和术语,必须本着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精神,千万不要照搬照抄。可惜的是,尽管汉魏六朝时期编写的地记数量是相当多的,至今我们能够知其名者尚有一百三十余种,但完整流传下来的竟一部也没有。 进入隋唐五代,方志发展迎来第二个阶段—图经大为发展阶段。隋唐时代,在大一统的形势之下,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许多制度都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原来的九品中正用人制度,人事大权操纵在地方世家大族手中。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就得把用人大权收归中央,故隋唐采用了科举选士制度,这种制度以才取士,不受门第高低的限制。自隋文帝开始,又把国史的编修大权垄断在中央政府手中,私人评论人物的著作也一律禁止,这显然就是针对旧的世家大族势力。这些世家大族以前总是标榜自己门第的高贵、郡望的优越,并借编写地记来达到这一目的,通过地记或相互吹捧,或自我吹嘘。这种风气若让其继续流行,势必影响中央集权的统治,故被下令禁止。另外,东晋偏安以后,北方世家大族纷纷南逃,为了保住自己的社会特权,到南方后先后设置了大量的侨置州郡,据史书记载,仅今天江苏常州一带,便设置十五六个郡级和六十多个县级流寓郡县,搞得杂乱无章,名实相违。所以还在南朝齐时,沈约写《宋书》的《州郡志》时,已经感到头绪纷繁,“邦名邑号,难或详书”。故隋王朝建立不久,有的大臣已经指出“天下州郡过多”的弊端,并建议应当“存要去闲,并小为大”。隋文帝根据这个建议,便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还合并了一些州县。既要整顿州县行政区划,就必然要整顿版籍,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国家赋税的收入。只有知道各州县的户口数,方可得知各地所收赋税数字是否准确。于是,整顿地方行政区划,加强户口控制,了解各地物产,确保赋税收入,便成为隋朝大修图经的重要因素。这就告诉人们,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各种相关制度也在发生变化,而作为地方著作的功能也必然要随之变化,于是地记编修大为减少,而图经则得到普遍发展并取代了地记的社会使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图经取代地记而行使其历史使命,可视为封建中央集权战胜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的具体表现。这种变化,显然又是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受各种社会因素制约的。 (后略) 方志学专家仓修良在该领域的论文合集。 仓修良先生在方志学领域造诣颇深,本书收录了的论文中,既有仓先生在方志学理论上的探讨,也有他对几本方志的经眼点评,这些论文曾推动了我国的方志学发展,体现了仓先生的卓越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