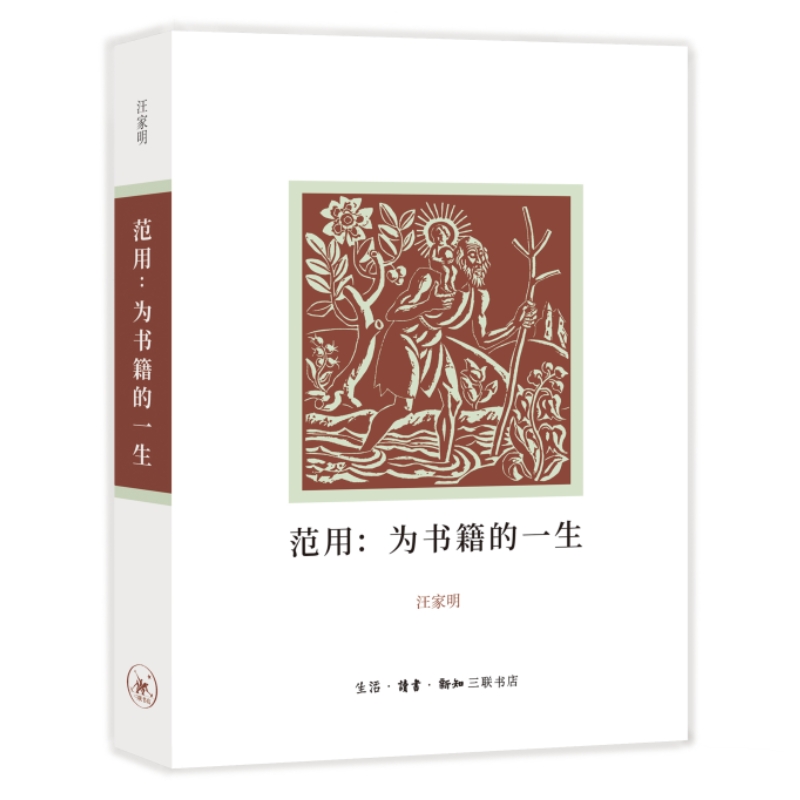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9.60
折扣购买: 范用:为书籍的一生
ISBN: 9787108064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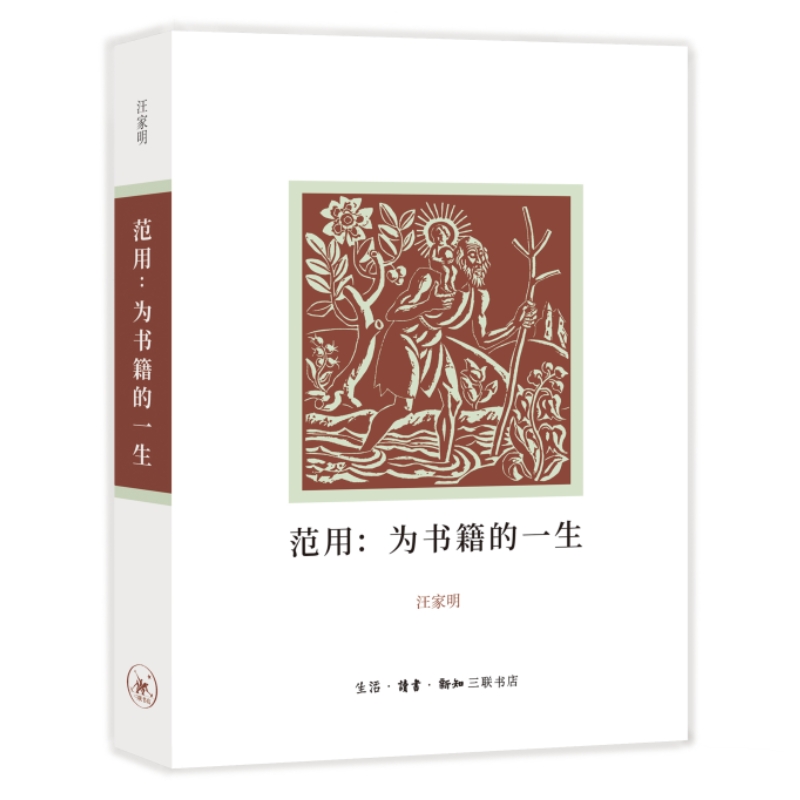
汪家明,1953年出生于青岛。1984年进入出版行业,曾任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副总经理,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著有《难忘的书与人》《难忘的书与插图》《爱看书的插画》《立尽梧桐影——丰子恺传》《美术给予我的》,编辑《范用存牍》《三心集》。
1940 年在重庆,范用用了半个月的工资买到“复社”出版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宁谟·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中文译本。 …… 《西行漫记》中译本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本书对日本铁蹄下的中国读者,尤其对当时苦闷的青年人影响巨大,许多人的命运是因为读了这本书而改变的。范用虽然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对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许多红军领导人的情况,都是通过《西行漫记》才了解到的。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十四岁在镇江澡堂里一口气读完的《毛泽东自传》,原来就是《西行漫记》当中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 几十年来,这两本复社精装的大书,始终是范用最珍贵的收藏,保存完好。其间,中国军事博物馆曾为了展览借用过,许多朋友也借阅过。作为出版人,他一直很期望能够按1938 年初版本原样重印《西行漫记》。尽管斯诺1960 年来中国时,这本书作为内部读物重印过一次,横排精装,定价2.20 元,但印数很少,定价高,一般人看不到,甚至完全不知道。由于书中牵扯许多敏感人物和事件,牵扯到中共党史、军史内容,一直难以重印出版。 1972 年初范用从干校回京后不久,得知斯诺去世的消息。他想有所纪念,恰巧香港朝阳出版社出版了斯诺的一本小册子《我在旧中国十三年》。这本小册子是香港《文汇报》摘译自其回忆录《旅行于方生之地》,摘译者夏翠微。范用建议以香港《文汇报》的摘译为底本,在内地出版这本书。他在亲自起草的选题报告中说:“此书……记叙其(斯诺)在30 年代来到中国以后,接触了中国社会,结识了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思想认识逐渐变化,自此起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斯诺的为人,也可以看到中国革命的一个侧面。经与翰伯同志研究,可用此译文翻印一些(先印一万册,由本社内部发行)。以后如有必要,再考虑是否加印交书店内部发行。”最终,这本书被列为“灰皮书”之一于1973年3 月出版了。出版名义是三联书店。书前的“出版说明”也是范用写的。 斯诺去世后,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写了一本回忆录《尊严的死——当中国人到来的时候》,由美国兰登书屋于1975 年出版。书中记述了斯诺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在中国医疗小组到达后(斯诺的家在瑞士),他们家里发生的动人的故事。这本书的中文译者是董乐山。董乐山在社科院工作,是三联书店的老朋友了,曾参与翻译“灰皮书”之一《第三帝国的兴亡》。范用看到译稿后,十分感动,决定出版。他在审稿记录中写道: 斯诺夫人的A Death With Dignity 一书,原来打算摘译附录于《斯诺在中国》。在研究了全书内容后,觉得可以单独出版,公开发行。 这本书写得很有感情,她写了斯诺生命的最后的日子,写了毛主席、周总理对斯诺的关怀,写了中国派去的医疗组的尽心的治疗和护理,写了斯诺和他一家对中国的诚挚的感情。 现在公开出版的翻译书不多,出版这样一位老朋友的著作不无意义。全稿我通读了一遍,译文甚好,不必做任何删节。可以发排。 与对外友协联系,打电报给斯诺夫人打个招呼——此事可待排出清样时再办,免得与出书相隔太久…… 范用 1978.4.17 范用根据译者董乐山的意见,拟了六个书名,请大家考虑。他建议用《“我热爱中国”——在斯诺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此前的3 月20 日,范用亲笔起草了给马海德和路易·艾黎的信,约请他们为这本书写序,希望他们4 月中交稿。信的落款都是以个人名义:“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两位外国友人、斯诺的朋友如期完成了写作。马海德正在病中,在与马海德夫人的通信中,范用建议在中国度过大半生的马海德写一部回忆录。 《“我热爱中国”》的封面是范用自己设计的,由美术组组长马少展制作完成。一个蓝色的框,像画框一样框在封面封底四周,框内是白地儿。他让美术组的宁成春根据斯诺照片画了一幅线描肖像,放在白地儿的右上角,左侧是竖排的书名。这是不同一般的,因为一般都是把书名放在右侧。封底并无装饰,而是将内容简介和作者简介用六号字排成一栏,用与肖像相同的深棕色印,看上去文字也有了装饰效果。整个封面封底,只有蓝、棕、黑三色,而且除了三联书店的圆形标志,连出版单位名称都没有。他在发给美术组的“内部通知单”里特别注明:“本书可列为今年评选装帧候选书之一”,可见是很满意的。好友姜德明得到样书后致信范用说:“斯诺夫人一书无论从开本、编排到封面设计都别具一格,看后爱不释手。这样搞下去,三联一定会重享盛誉。”以后这类书都用这种风格,比如韩素音的三本自传《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 《“我热爱中国”》选用了一幅毛泽东、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斯诺夫妇的照片,特向外交部美大司申请批准;另外通过对外友协致信驻瑞士大使馆,请他们转告斯诺夫人,准备于1978 年9 月出版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对外友协的具体联系人是资中筠。时任中国驻瑞士的大使亲自去见了斯诺夫人。斯诺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激动,一口答应,说“我们全家都很高兴”,“中国朋友完全可以处理”。 《“我热爱中国”》比原计划晚了半年,于1979 年3 月出版(版权页上仍是1978 年10 月),人民出版社写信给驻瑞士大使馆,请他们转致斯诺夫人,并寄去样书八册,四册交给作者,四册大使馆自存。在这封信的最后特别注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应中国广大读者的要求,正在翻译出版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特此告知。斯诺夫人有何反应,请告。” 《西行漫记》的出版终于提上了议事议程。 其实,1976 年1 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就重印了《西行漫记》;1977 年1 月,香港南粤出版社也出版了《西行漫记》,译者陈云翩。1978 年12 月21 日,人民出版社曾给中国对外友协发去一封公函: 埃德加· 斯诺(EDGAR SNOW)的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将在国内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译本,公开发行,系采用原著1972 年版全译,只对其中个别涉及林彪的地方稍作删节。附录未用。拟请你处转托我驻瑞士使馆用适当方式告诉斯诺夫人,并将结果通知我们。 显然是这封公函发出后没有回音,所以在寄送《“我热爱中国”》样书时,又一次提请驻瑞士大使馆转告斯诺夫人。 《西行漫记》的内容分为十二章、五十三小节,内容极为丰富、生动、具体,都是第一手资料。比如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对谈,对红军将领贺龙、徐海东等的描写,苏维埃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游击战术的奥妙等等,尤其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故事,从红军领袖们嘴里讲出来,是那样奇特。 另外,作为一位外国优秀记者,斯诺观察的角度、叙述的方式都与一般记者不同,读来很新鲜,很真实。可是,从采访写作到1978 年,时间已过了四十二年,这样一部关乎历史的书稿,以当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眼光,里面的问题很多很多。编辑部提出: 这些问题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改,不加注,保持历史原貌,读者都是可以理解的,出版社自己可以讨论决定的,如书名,主席离婚、结婚,林彪……等;一种是需要改,或加注说明,出版社自己很难定,需向有关方面请示或征求意见的,如外蒙、(中国)台湾、印支、缅甸等,这些问题涉及当前国际斗争和我对外路线,确实需要慎重。 其实,对上述问题的加注、删改,恐怕都不是妥善的办法,是否不加注、不删掉的地方就永远没问题了呢?读者就可以据此书所载作为正确的依据呢?所以,倒不如统一写一个出版说明,作一交代更为灵活,留有余地。这等将来再研究吧。 社里主事的张惠卿、范用也有些拿不定主意,还是上报时任国家出版局正副局长的陈翰伯、王子野、许力以。陈翰伯最后拍板,只删除个别内容,其他不再加注。 根据范用的要求,胡愈之在百忙中校订了一遍新译书的全稿,写了三部分、十二条参考意见,分别是“关于内容方面”“关于编排格式”“关于文字和标点问题”,认真而全面;他建议为了保留历史原貌,还是以《西行漫记》为题出版,另外,他写了一篇分量很重的《〈西行漫记〉中文重译本序》,介绍了斯诺和《西行漫记》出版的全过程: 当时,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了一个“星二座谈会”,每星期二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餐厅集会,讨论研究抗日宣传问题。我在这个会上提出了出这本书的问题,大家都同意,就由参加座谈的同志分别承译。我们当时都意识到,翻译这本书很重要……翻译问题解决了,怎么出版呢?决心发动群众自己来搞,大体算了一下,出版后定价一元,就征求预订,先交订款一元。一下子就征得了一千本订金……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从1937 年12 月开始翻译,1938 年1 月出书,前后也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遇到难处理的地方,常常去问斯诺,得到他的帮助。他还给中译本写了序,提供了照片,有些是英文本原来所没有的…… 这本书是通过群众直接出版的,但对外总也得要一个出版名义,我临时想了一个“复社”的名义。在书上没印“复社”的地址,实际上它就在我家里……这本书初版后很快销掉,接着再版、三版……受到意外的欢迎,但它们都没在书店里出售,而是群众自己组织印发的…… 斯诺的原书名直译过来是《中国天空上的红星》,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不能照译。我们就改用一个隐讳些的书名。为什么要叫《西行漫记》?因为在工农红军长征后,关于我们党在西北情况的比较真实客观的报道,只有一本书:范长江同志写的《中国的西北角》……从此,“西”或“西北”就成了我们党所在地的代称。 胡愈之在《序》里,特别引了斯诺为中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写的序文里的一段话: 从字面上讲起来, 这一本书是我写的, 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 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这本书描写的对象……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 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 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 那种热情—凡是这些, 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胡愈之最后总结说:“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是少数领袖们——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这是《西行漫记》这一本书的总结。” 经过一年多的编辑、审核、校订,三联书店版《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终于出版了。1979 年12 月第1 版,正文四百零六页,照片六十八张,三十二开,横排平装,首印二十万册,每册定价一元三角。这次重译出版,除改正个别十分明显的史实错误及人名、地名和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外,一律照译原文未作改动。四封是宁成春设计的:封面是一位仰头吹号的战士,封底有斯诺的照片,而且很出格地印上了路易·艾黎写的诗《埃德加·斯诺》。 像《“我热爱中国”》一样,这种在封底印长篇文字的设计方式,既有广告作用,文字版块也可作为设计元素,是范用所喜欢的。 三联版《西行漫记》出版后不到两个月,本店和各地加印的,总计已经超过七十万册。此时距中文版初版,已过去了四十一年。 今人大概很难想象,在性命之虞、身心困顿中还要坚持做出版,是怎样一种情境。这本范用先生的传记,就写了许多或惊心动魄、或感人至深的出版故事。范用的一生,是为书籍的一生;本书也就围绕着“书”而展开,写他七十余年间的读书、编书、出书、写书、设计书、推广书。世间爱书人有不少,但称得上“书痴”的可不多,范用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书痴”,因着这种“痴”,他催生了那么多经典书籍,泽被后世;在他与一众名家作者的交往故事中,我们也懂得了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编辑、一个合格的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