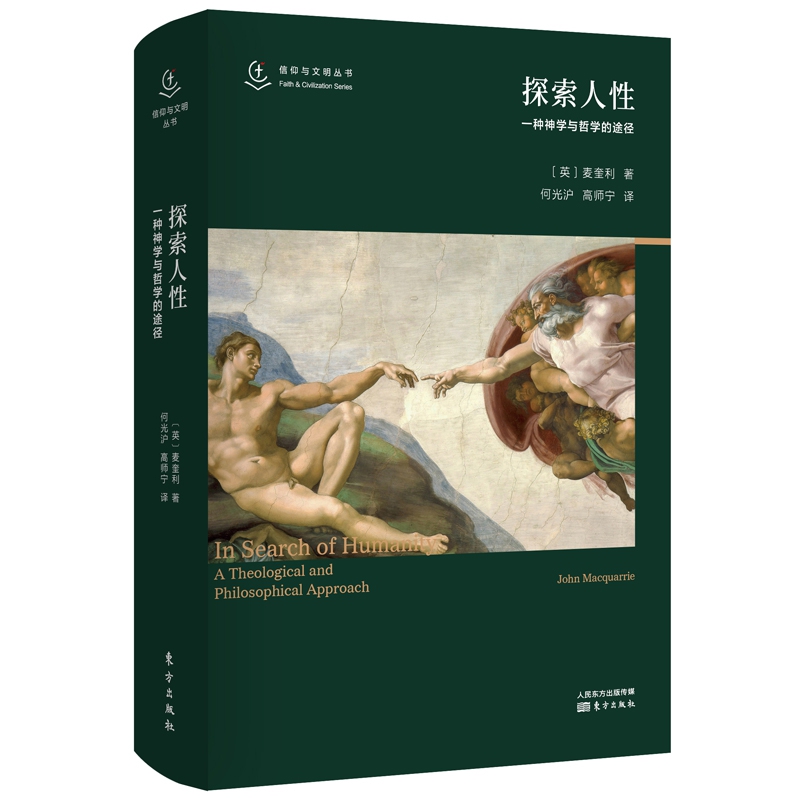
出版社: 东方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4.20
折扣购买: 探索人性
ISBN: 97875207117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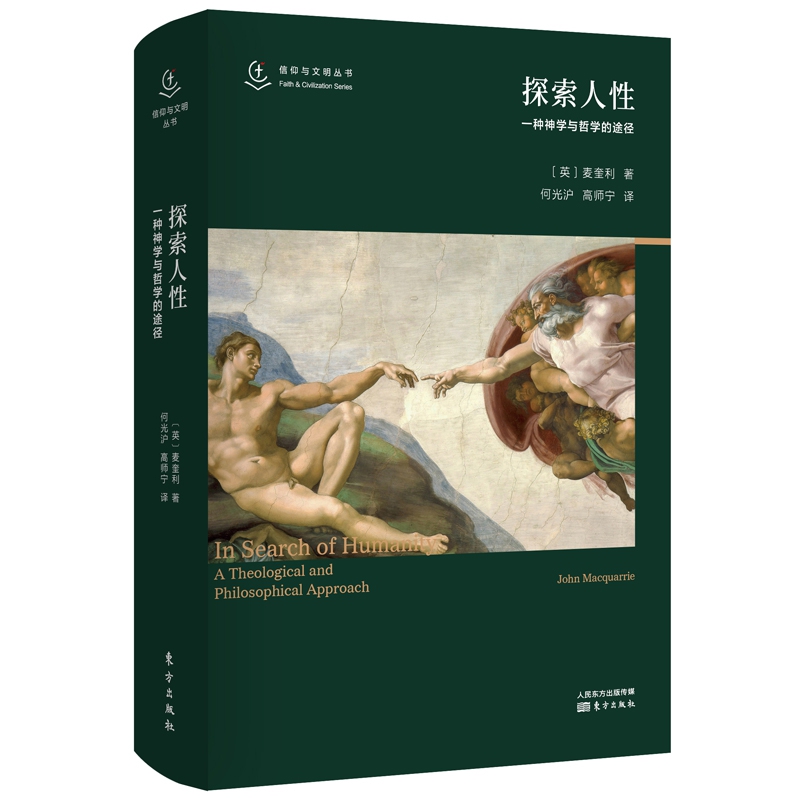
麦奎利(John Macquarrie,1919—2007),英国哲学家、神学家,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神学讲座教授,牛津大学荣誉教授,英国研究院会员。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纪宗教思想》(1963)、《基督教存在主义研究》(1965)、《谈论上帝》(1967)、《基督教神学原理》(1977)、《基督教的盼望》(1978)、《探索人性》(1982)、《探索神性》(1984)、《现代思想中的耶稣基督》(1990)、《海德格尔与基督教》(1992)等,并与人合作将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译成英文。
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这些都属于最难以回答的问题,然而又都属于最为重要的问题。蒲柏曾写道:“要研究人类,最适当的对象就是人。” 但是,我们可以说,在研究非人性的环境而不是在研究我们自己方面,我们事实上从来都努力得多,而且也成功得多。对自己的认识一直被恰当地认为是一切认识中最为困难的认识。在本书的开头,我们必须来看看这样一些特定的难题,任何想要解决做人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努力,都逃不掉这些难题。 首先,“人”这个词本身就具有一种歧义。我以前的同事、著名伦理学家莱曼(Paul Lehmann)在他的某些作品中几乎像迭句似地运用的一句话很好地表达了这个歧义。这句话是这样的:“要使人的生活成为人的生活,要保持人的生活始终成为人的生活。” 这句话不是要成为纯粹的同语反复,尽管它在形式上是一种修辞手法。它并不像“要使猫的生活成为猫的生活,要保持猫的生活始终成为猫的生活”这句话那样,似乎是一种空洞的措辞。但是,只有认真地弄清楚莱曼使用“人”这个词时在两个方面的意思,这句话才能脱离纯粹的修辞手法而获得意义,因为这个词在此显然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在前一处使用这个词时,“人的”这个词是描述性的:“人的生活”是指所有在生物学上可归类于人,即属于“智人”(Homo sapiens)这一物种的所有人的生活。但是在后一处使用时,“人的”这个词已经带上了一种评价性的含义;现在它所意味着的是“真正是人的”,或“本真地具有人性的”,或“完全属于人的”之类。 进一步说,使用“使……成为”和“保持……始终成为”这两个动词,看来是要表明,“人的生活”(在描述的意义上)是一件会变化的或者也许是未完成的事情,它可以成为“人的”,也可以不成为“人的”(在真正是“人的”意义上),因此不得不使它成为人的,或者,如果它已经成为了“真正是人的”,那么它也依然处于成为别的东西的危险之中,因此也不得不“保持它始终成为人的生活”。当然,这也就意味着,这样说的人心中必定有某种标准去判断“真正是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刚才所引用的莱曼是有意识地利用了“人的”一词的歧义,但是,在我们不假思索的日常用语中,也有同样的歧义。当我们谈到某个残暴的独裁者或杀人犯的时候,我们会说他是一个“非人的(即没有人性的)恶棍”。我们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他不是人类的一员,而是说他的行为没有达到我们认为是真正的人的标准。说起来似非而是的是,恰恰因为他事实上是人而且应该像人那样行事,我们才说他是“非人”。艾伯林(Gerhard Ebeling)说得十分清楚:“只有人才能成为非人。而且即使是那个成了非人的人,也有权利要求被作为人来对待。” 上述第二句话表明,无论一个人可能堕落到人的标准以下有多远,我们也绝对不能完全否定他的人性。神学家们谈到洗礼和圣秩时,都称之为“不可消除的”,在一种更加基本的意义上说,人性本身更是不可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