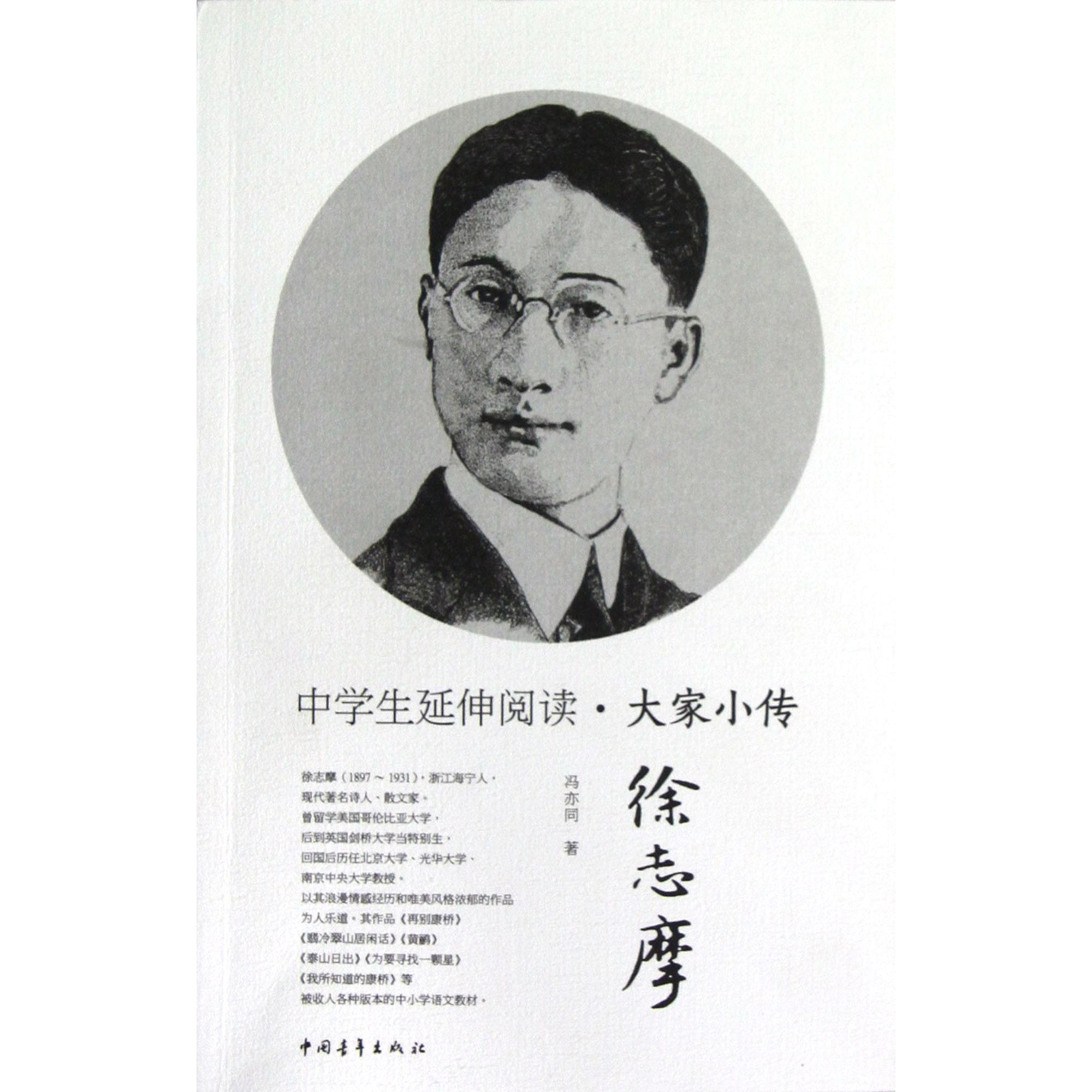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青年
原售价: 19.00
折扣价: 12.20
折扣购买: 徐志摩/中学生延伸阅读大家小传
ISBN: 97875153106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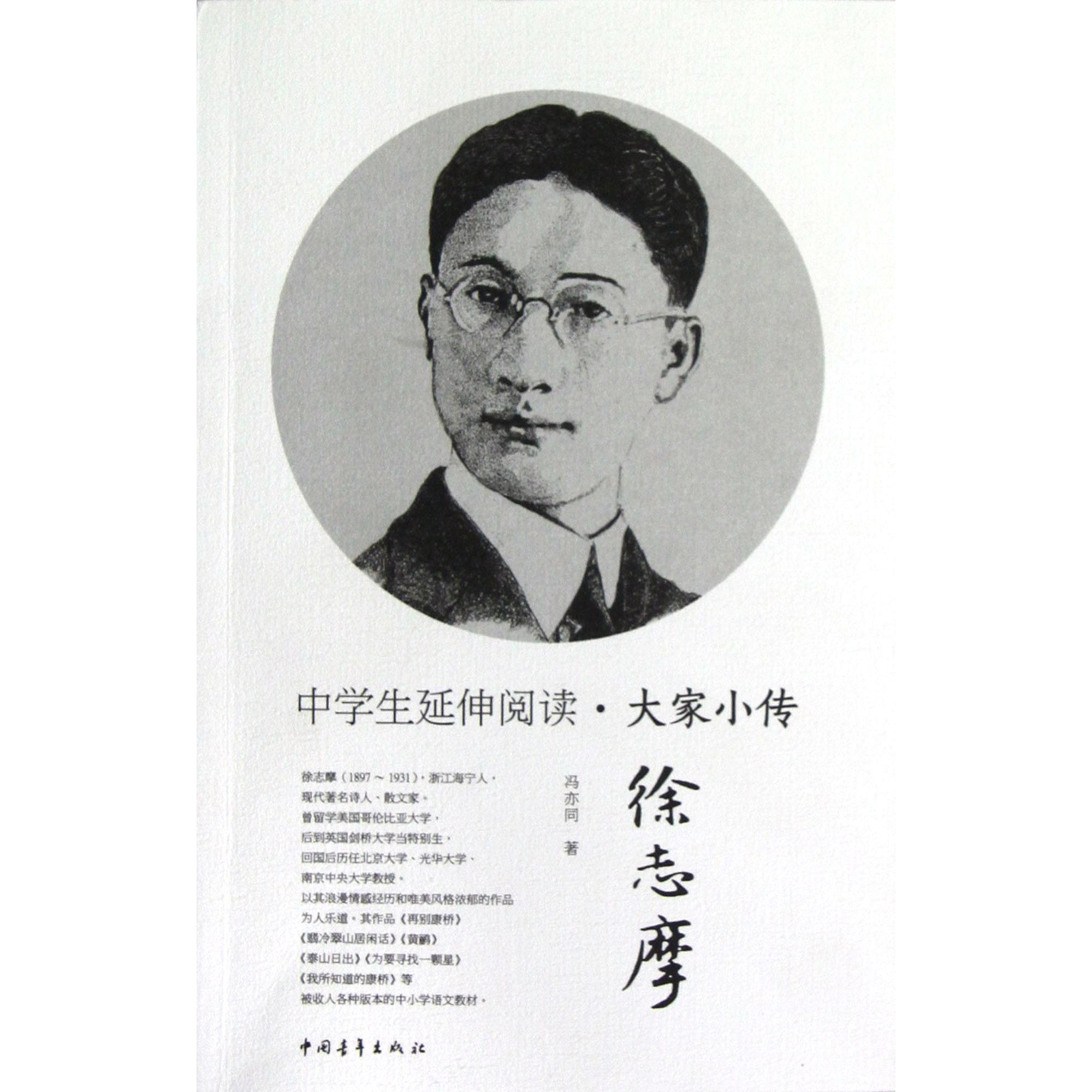
冯亦同,1941年生于江苏宝应。1963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南京市作家协会顾问、江苏省诗词学会顾问、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理事。著有诗集、评论、散文和传记文学多种,曾获南京文艺奖、紫金山文学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国际炎黄文化奖等奖项。
云游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喜爱和熟悉中国现代诗的读者,都不会忘记诗人徐志摩的名字。以上几 行空灵、洒脱的诗句,便引自他写于1928年的抒情诗《再别康桥》。这是一 首脍炙人口的传世名篇。此作问世三年后,才三十四岁的徐志摩竟不幸死于 空难。这幕突如其来的悲剧,发生在1931年11月19日中午时分,济南城南十 五公里处党家庄的开山,当地人叫“白马山”的山头上。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晴日,徐志摩所乘坐的“济南号”邮政班机早晨从 南京起飞。机上只有三人:正驾驶王贯一、副驾驶梁璧堂和他这唯一的乘客 。自这年2月徐志摩应聘为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并兼任北京女子大学教授以 来,因家眷仍留在上海,大半年里他经常只身往返于南北两地。喜好乘飞机 旅行的诗人,曾存一篇题为《想飞》的散文中说: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 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的这 么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大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 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 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 就在三个月前,他还写了一首后来被改题为《云游》的十四行诗,同样 醉心地吟唱那“翩翩在空际”的“自在”与“轻盈”,而当时家庭经济的拮 据,已迫使“逍遥”的诗人不得不考虑节省开支,经一位在航空公司工作的 朋友帮助,他得到了一张“免费飞车券”,可以不花钱乘上该公司的航班。 就在11月13日从北京飞返南方,惊喜交集的妻子陆小曼还责怪他不该坐这“ 要命不要钱”的飞机。几天后,乘火车去南京,小曼也叮嘱他今后不可再“ 冒险”。然而在南京办事、访友,整日奔波,第二天一早,行色匆匆的徐志 摩还是登上了这令他的家人和朋友们都为之牵挂的北返航程。 望着机窗外阳光灿烂、纤尘不染的蓝天,诗人的心境也开朗起来。比他 更有兴致的,恐怕还是正驾驶座上的王贯一技师。这位爱好文学的飞行员得 知身后乘客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和大学教授,竟跟自己的副手调换位置,坐到 徐志摩身边来向他讨教诗文问题。攀谈中不觉已飞抵徐州上空,徐志摩突然 感到一阵难忍的头痛。恰好飞机要在徐州着陆,在机场休息的一刻钟里,向 来笔勤的徐志摩还抓紧时间给家中妻子写了封信,告诉小曼自己感觉不适, 不想北飞了。然而当王技师走来关切地询问:“徐先生头痛好些了吗?”徐 志摩已恢复过来,自我感觉不错,连声答应着又上了飞机,时间已快到中午 了。 印着邮徽的“铁鸟”在鲁西平原上空穿行,星罗棋布的城镇、乡村、河 流、丘岗,纷纷退向身后,莽莽苍苍的泰岳也为它打开了壮丽的画屏。迷恋 云游的诗人此时在机舱内想些什么、说过什么,都已经无法查考了。后人可 以断定的是,促使他急着赶路的直接动因里,有一串他情感世界中烙印最深 、也最难破译的心之履痕:他同他热爱和追求过的、被人们誉为“东方第一 才女”的诗人、学者林徽因之间非比寻常的“友谊”——因为林徽因定于19 日当晚要在北平城里的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节作关于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 徐志摩曾答应她届时将前来听讲。天性随和、热情,又最讲信义、喜好交游 的诗人怎么会“失约”呢?他在南京出发前就给林徽因拍了电报,请她下午 派车来机场接他。可以想见飞机越往北飞,他对古老都城的眷念和故人相聚 的心情也愈加热切。一个多月前,他还在给陆小曼的信中说:“北京真是太 美了,你何必沾恋上海呢?” 然而,一场不祥的、铺天盖地的黑色厄运突然袭来,永远隔断了这位飞 行客与北京友人之间的约定。从济南方向四面包抄而至的浓密雨雾,就像是 死亡之神张开的无情大网,在波谲云诡的天海上翻滚、兜腾起来,要打杀一 切与它相遇的生灵。正如徐志摩在他那篇散文《想飞》中描绘过的那样: ……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 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硼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 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 诗人的艺术想像真的成了对自己命运的“谶语”,它不幸而言中。在这 一时刻——那被雨帘雾障裹住的“鸟形机器”已晕头转向,正冲着济南城郊 外的一座青山撞去,伴随着“硼的一声炸响”,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疾风 似的消失了飞机的影子,“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 收到电报的林徽因是下午二时后派车去南苑机场接徐志摩的。说好三点 钟到,等到四点半也不见人影,但有消息传来,说济南那边有大雾,肯定飞 不回了。林徽因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挨过了一夜,20日清早才得到飞机失事 、包括徐志摩在内的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的确信。这惊人噩耗的打击,使身体 本来就弱、不久前还住西山疗养肺病的林徽因眼前一阵昏黑,胸口如针刺般 地疼痛。她的丈夫、同是志摩友人的梁思成教授也惊愕得无言以对,当天他 就同张奚若、金岳霖、沈从文等先生连夜兼程,赶赴出事地点为死者料理后 事。细心的梁思成尊重和理解妻子的感情,特地从志摩遇难处捡回一块烧焦 的木头,那是“济南号”邮机的一星残骸。既然它未烧成灰烬随风飘散,上 面也该丝丝缕缕地羁留着诗人最后的时光吧?林徽因睹物思人,将它作为永 久的纪念,用线绳穿起来,挂上自己卧室的墙壁…… 新诗坛上这颗耀眼明星的殒落,给深秋的古都也带来了几分寂寥与寒意 。《晨报》副刊上,大学校园里,人们惋叹这位早期新诗人的离去。从平津 、济南、青岛,到南京、上海、杭州,文化学术界为之震惊、哀恸,许多地 方举行了公祭。第二年春天,诗人的灵柩运至故乡——浙江海宁的硖石镇上 ,父老乡亲们在西山梅坛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据说各界人士所送的花 圈、挽联之多,把一座葱茏的青山都映白了头。同年秋天,灵柩安葬于东山 万石窝,墓为一方庄重肃穆的矩形石棺,墓前有书法家张宗祥所书石碑:“ 诗人徐志摩之墓”。 诗人生前友好、亲属、同事与学生,纷纷写下不少追思和悼念的文字, 《新月》杂志和《诗刊》都出了“纪念志摩”专号。撰联和撰文者中,有蔡 元培、史量才、胡适、黄炎培、郁达夫、沈从文、梁实秋、林语堂、蒋百里 、梅兰芳、杨振声、叶公超、周作人、何家槐、赵景深等许多名流。悼文中 ,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一篇,是当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同诗人交谊 极厚的胡适先生写的。这位声望很高的学界巨子,满怀深挚的情感评说徐志 摩的个性魅力和他出人意料的死: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都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得 这样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 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 摩会一个“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 ,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 死法,也挑不出更合式、更悲壮的了。 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云彩。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中 ,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 爱。他常说: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个方向吹—— 我们也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可是在狂风过去之后,我们的天空变 惨淡了,变寂寞了,我们才感觉我们的天上的一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卷走 了,永远不回来了!① 时隔六十多年,重读胡博士不无伤感又惶惑的话语,仿佛是从岁月回音 壁上传来的遥远声波,既反映了这位“五四”新文学大家和著名学者对他亡 友的推重与赞许,也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多少表现出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像胡 适和徐志摩那样的上层知识分子,在世事纷扰和时局动荡中的思想游移与心 灵苦闷:“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个方向吹”这句出于徐志摩笔下的缥缈诗句 ,为什么会引起这特定时空下的“我们”的强烈共鸣?徐志摩又是怎样成为 了“我们的天上的一片最可爱的云彩”?他在“我们”中间是怎样焕发和保 持了那“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的诗人本色? 历史的旅程、生活的波澜,究竟怎样投映他真实的形影? 且让我们溯回这位“云游者”的来路,沿着他留在人间三十四个春秋的 生平踪迹,去寻找答案吧。P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