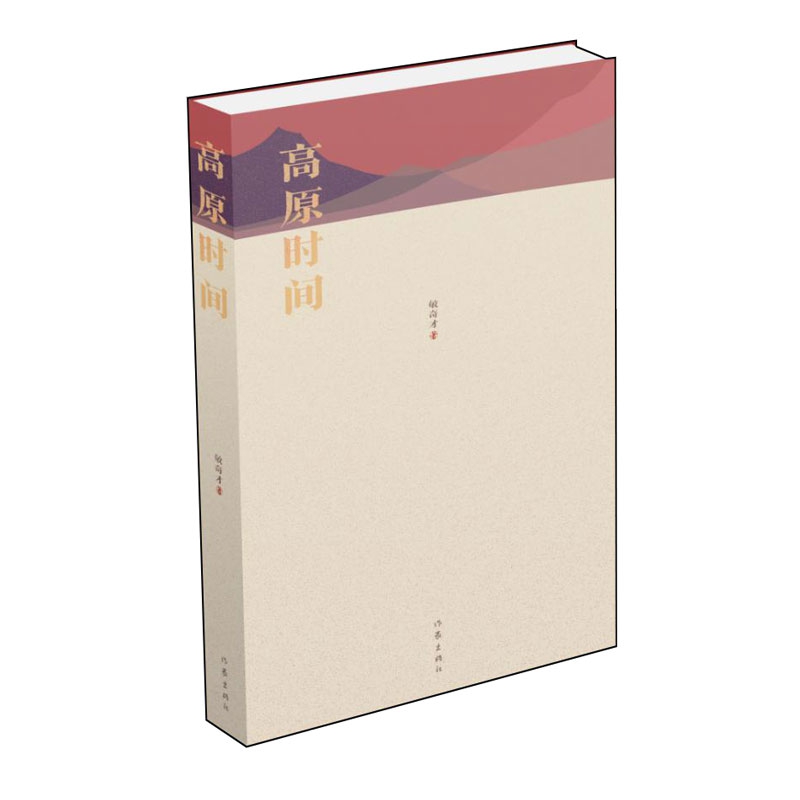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8.40
折扣购买: 高原时间
ISBN: 97875212077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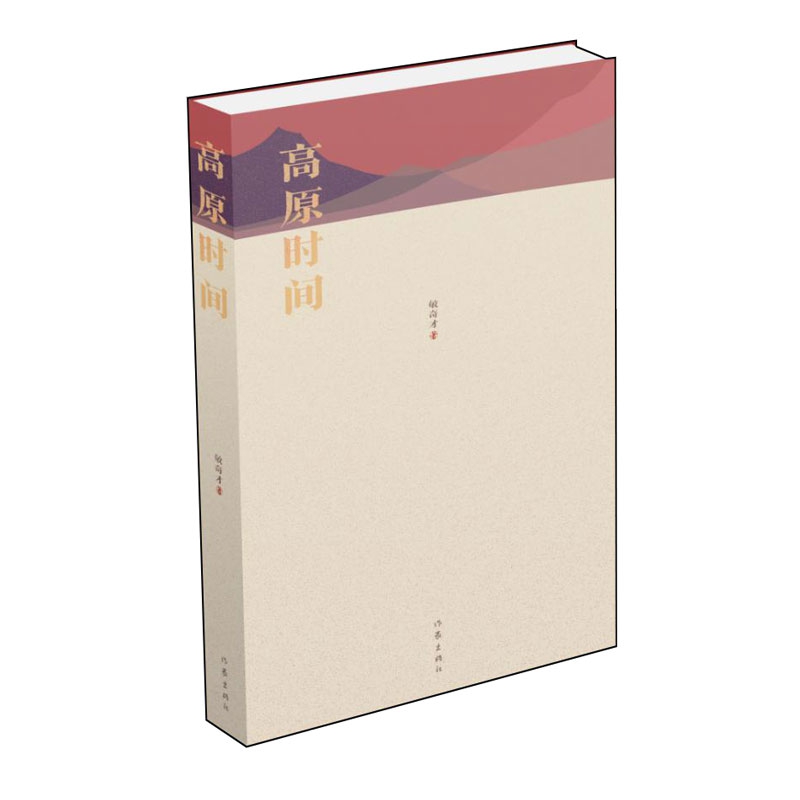
敏奇才(1973年11月——),回族, 生于临潭县长川乡敏家咀村一社。1995年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汉语系,现任临潭县文联**。系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学员。小说、散文、剧本散见《民族文学》《中国作家》《光明日报》《文艺报》等一百三十多家报刊,入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2008年中国散文精选》等。主编散文诗歌集《洮州记忆》,主编《洮州温度》等。出版散文集《从农村的冬天走到冬天》等。名录列入《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当代卷)》。
我的母亲 那天,母亲从乡下家里带了点杂七杂八的东西,背了一大包,在 楼下喊曼茹叶。母亲是来看她亲手拉扯大的孙女的。妻子下楼去接母 亲。在她们说说笑笑地上楼梯时,我发现母亲掩在黑盖头下面的脸庞 有些许苍白,但仍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她的步子迈得很缓慢也很吃 力,似乎是在攀登一座大山。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母亲的腿是有病 的,是走不快的,也走不稳。我的心里就隐隐作痛起来。这十几年 里,我凭着手中的笔,写家乡,写乡亲,曾一度写得手酸,但就是没 有系统地写过母亲。这几天,我思谋了许多,决定系列性地写写母亲 的一生。 1.一把弯镰 家里檐柱的镰夹上牢牢地挂着一把明晃晃的镰刀,像清真寺脊顶 上闪耀的那弯新月。那是母亲用了好几年的一把镰刀。以前母亲用过 好多把镰刀:有铁匠铺里打的,也有街市上买的,还有自己掏钱用钢 板打磨的。母亲手里用过的镰刀多,也对镰刀有很深的见解。 她说,铁匠铺打的镰刀,割庄稼能揽田,茬口低;塄坎上割草不 撒,能收得拢草,但有一样就是刀口老得快,费时费力。街市上买的 现成镰刀,只能随便用用,凑凑紧可以,初学割田的人用着顺手,轻 巧,不拉力,但就是上不了大场合大排场。而自己用薄钢板打磨的镰 刀既能用着顺手,也能揽田,而且割田茬口低,刀刃也老得慢,省力 省时也省心。母亲挂在镰夹上的那把弯钩似的镰刀就是父亲亲手给母 亲打磨的。那年,有人曾想用四把铁匠铺里打的镰刀换那把镰刀。父 亲笑着说,就是五把也不换,那把镰刀用着既省老伴的劲儿,也省我 的力。来人笑着摇摇头走了。他也许是笑父亲怕母亲吧。但不管怎么 说,那把镰刀用了好几年,母亲就是不肯撒手,就是家里人用一下, 她也不允许,说怕把她镰刀的刀刃打豁了。 那把镰刀就是母亲的宝贝。就是用成了一把弯月也不让别人用一 下。父亲有时候开玩笑说,等把这把镰刀用坏用烂了,再给你打磨一 把*好的镰刀。母亲狠狠地说,这把镰刀谁也不能用,它不能用了就 让它挂在镰夹上放着,就是不能往坏里用往烂里用。 家里谁都知道母亲珍爱这把镰刀,于是常常拿这把镰刀跟母亲开 玩笑。有时候和母亲一起说笑的时候,父亲就猛地转过头,朝院子里 大声喊道:“曼茹叶,把你阿婆的镰刀放下,甭到石头上砍,砍坏 了!”母亲就急匆匆地奔出屋子,朝檐柱上望去。看到镰刀好好地挂 着,就嘿嘿地一笑,笑得甜甜的。于是我们就从她那甜甜的笑容中看 出了母亲对生活的一种惬意。 母亲再也未用过新镰刀,她挥不动新镰刀了。她只用她那把用勚 的镰刀,闲的时候给牲口割点青草。她虽然多不用镰刀了,但她还是 要把那把镰刀磨得锋利无比。她常说,镰刃就像人的牙口,要常磨着 才硬棒。人有时候,也要像这把镰刀一样磨一磨,磨利锈钝的心智。 母亲很哲理地说一些话,这些话我们是说不上的,只有母亲才能说得 上这农民式的哲理。 母亲常拿那把镰刀磨一磨,其实,她磨镰刀的时候,也在不断磨 新自己的记忆,回味过去的岁月。磨好了镰,然后沉浸在一种美好的 回忆中。 2.一根老担子 家里没有了猫,老鼠就在灶房里肆无忌惮地窜来窜去,犹入无人 之境。你在下面做你的饭,我在椽条缝里闻我的香,有时候,还故意 丢下几粒黑乎乎的东西来,不是掉在碗里就是落在锅里,真是一只老 鼠祸害了一锅汤。老鼠如此肆意地祸害,使人简直受不了,让人吃着 生了病。于是三弟就不时地守在灶房里一心想把那几只祸害人的老鼠 给捣下来。有一日,又有老鼠在椽条缝里窜来窜去,三弟悄悄地下地 拿上一根竹竿狠狠向老鼠戳去。但这一戳却没有戳到老鼠,而把母亲 担放在椽条缝里的担子捣了下来。担子翻了一个跟头,平平地落下来 啪地摔成了两截,差点把母亲的心摔碎。 母亲心疼地把这根担子念道了好几天。这根担子在奶奶的肩上磨 了好多年,直到把奶奶从一个年轻媳妇磨成了老奶奶。后来,母亲进 了门,这根担子就磨在了母亲的肩上,每天鸡还没有叫的时候,母亲 就挑着担子沿着羊肠小路到山湾里的泉上去给奶奶挑洗小净的泉水。 这一挑就是好多年,风雨无阻。现在担子摔断了,让母亲很是痛心, 这根担子是奶奶留给母亲的念想。过了一段时日,父亲偷偷地把两截 断开的担子当烧火柴扔在了柴房里。母亲找着又用绳子缠好后放在了 厢房里,不让人碰它。 这根担子摔断了,不但母亲的心里难受,大家的心里也很难受。 这根担子毕竟在母亲的肩膀上颤悠了几十年,颤悠着磨走了母亲的青 春,磨大了几个儿女。直至磨得明光光的,没有了棱角。其实,一根 担子磨成了这个模样的时候,也磨走了人的棱角和性子。母亲就这几 样顺手的东西:一把用弯的镰刀,一根磨光的担子,一个残边的背 篼。现在担子摔断了,母亲说,担子的筋骨用酥了,像人一样,几十 年下来,说老就老了,再也挑不起生活的担子了。母亲说这话的时 候,眼里有了一丝泪光。这个时候,大家只有默默地看着母亲的眼 睛,不敢再说什么,怕是说到母亲的伤痛处。 母亲靠一双肩膀挑起这根担子,把我们兄弟几个养育成人。我们 小的时候,村里没有自来水,家里吃的水全靠人用一双肩膀到很远的 泉上去挑。泉离家很远,流量也很小。天不亮的时候,勤谨人家的媳 妇和姑娘就已经从泉上挑回了满**的一担水,那些懒惰人家的媳妇 和姑娘只有等到大天亮再去挑水,天亮时分,泉里已让人挑干了。母 亲常常是半晚上就去挑水,等别人家的媳妇和姑娘开门挑水的时候, 母亲已经是第二次出门去挑水了。所以那时候,我家碗里的水常常是 清澈明亮的,没有别人家碗里的那些黄汤和泥沙。因此,至今我们的 牙齿白生生的,没有那像镶了金牙的黄牙。让人看着挺奇怪的。 后来,村里拉了自来水,但由于水库小,水的储量不大,家家给 牲口饮水还得用人到泉里去挑。母亲还是像以往一样,等天不亮就挑 回了泉里的水,然后放在檐台上,等待太阳的到来,等太阳晒热了泉 水,母亲再端给那些牛啊羊啊鸡啊的。尤其是冬天,母亲挑了水来, 便要放在灶房里暖一暖,不让牲口喝冰水。她说,牲口喝冷水或是凉 水可以,但千万不能喝冰水,冰水拔牲口的胃气呢。别人家的牲口不 上膘,就是冬天喝了冰水的缘故。不知母亲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反正 我家的牲口就是上膘快。有人认为我家给牲口喂了什么大料呢。但看 了我家的牲口料之后,就想不通了。 前几年,村里扩建了蓄水池,自来水不但够人用,也够牲口用的 了。母亲的担子**地歇了下来。母亲就把它用布缠了放在了灶房里 的椽条缝里。 担子断了,母亲的心里像丢了一段记忆,空落落的。 母亲老了,记忆像摔断的担子,接续得吃力而又困难。 3.一只残边的背篼 南面柴房里的横梁上挂着一只背篼,沿边儿的竹骨乱奓着,周身 的竹骨变得黑黄斑斓,只有靠背的一面被人的衣物磨得光滑而油亮, 像打了蜡似的。其实那是母亲背上的汗水浸洗摩擦的原因。母亲常背 着这个背篼拿上镰刀到山湾里的田埂上去割青草。母亲出去的时候是 顶着烈日背了一背希望,而回来的时候则是背回来了一背青青的生 命。母亲就用这个背篼喂养着十几只羊儿和两头牛。羊儿是一切家务 花销的来源,牛儿是全家那二十几亩地的劳动力。没有羊儿,几个孩 子就穿不上新衣服,盐罐子里就没有盐可盛,油缸里就没有油可放。 没有牛儿,家中那二十几亩田就耕不了,一家大小就会吃不饱肚子, 所以母亲就格外爱护疼肠那些羊儿和那两头牛。很多时候,母亲是把 羊和牛当成了家中的成员。我记得,有一年,村里来了一个买羊的 人,父亲忍痛割爱地卖掉了一只羊给我们缝衣服,结果母亲哭着心疼 了好几天,像挖掉了她心上的油一样疼肠。 每天都要割回大大一背篼青草,母亲是空着背篼出去,然后背回 满满的一背青草。黄昏的时候,母亲蹒跚在山道上,身后扯下了一条 长长的身影。 后来,人们都用上了拖拉机,耕地不用牛了,村里的牛就开始一 头一头地减少,*后我家的那两头牛也被人买走了,但养惯了牲口, 母亲一下子闲了下来却有点不适应,于是父亲就买来了一头奶牛。母 亲又在青草青青的时候成天忙着给牛割青草。这时候,家家的羊儿 都卖光了,只有我家的羊儿母亲舍不得卖,还是那样养着,但已经 没有谁关心那几只羊儿了。父亲天天喊在嘴上,却也没有把羊儿卖 掉,照着母亲的吩咐喂养着羊儿。有时候还能帮着母亲割回一背篼 嫩翠的青草。 背篼用的时日一久,那柔软的竹骨就变得坚脆起来,不是这儿裂 就是那儿断的,母亲想方设法延长它的寿命。母亲先是用废布料把背 篼的沿子包起来,再用针线缝上,这样背篼就在用的过程中减少了摩 擦和碰撞的机会,自然地延长了寿命。再后来在用的过程中背篼的筋 骨断了,周身的竹骨没有了主心骨,随之也就破烂得不成个样子了。 母亲就再次用布包着裹好,挂在了南面柴房的横梁上,成了母亲用之 教训儿女的有力证物。母亲常指着那只破旧的背篼叹口气说,人老 了,就像那只没用的背篼一样,没有一点作用了,只能丢在柴房里当 一个弃用的东西保存起来。母亲在闲着的时候翻看一下那只破背篼, 心中就会增添几分豪气和莫名的激动。 看来,那只背篼母亲说不定还要挂很长时日呢。 4.一把老镢头 这把老镢头一直立在柴房墙角里,没有谁动它,也没有人愿意用 它,多么像一位让农活苦败的老人啊。让农活苦败的老人,苦不动 了,就整日坐在墙角旮旯晒着太阳,不说一句话,闭眼思谋上一阵自 己年轻时风光的日子,或是洗了小净跪坐在炕上,小声入神地诵念上 一会儿《***》。坐得时日久了,再逗一逗身旁玩耍的孩子们,自 己再哈哈大笑上一阵,笑得孩子们莫名其妙。 老镢头静悄悄地立在柴房的墙角里,从来都是一个样子。它的刃 口虽然钝钝的,但仍发着寒森森的一点光气,木把子的手握处深深地 凹进去了,那是母亲常年手握它劳作的缘故,浅浅地发着木漆的光。 大家知道,这是母亲又在哪天乘人不注意用碎布擦了它。 我小的时候,母亲还很年轻,用那把宽刃长把的镢头开荒,种 田,打胡基,挖地,掏壕,干着各样的农活,但干完农活后,不管有 多忙,母亲总要从田边扯一把杂草拣一块石块把镢头打磨得闪闪亮亮 的,不让它生锈。母亲的这把镢头由于管护得好,所以用起来也就顺 手,于是村里那些年轻媳妇时常来借这把镢头,有时这家刚放下,那 家又借走了。有时候母亲自己要用,却找不到镢头,这让母亲很生 气,但生气归生气,东西还是要借的,在农村从来就没有不借东西的 人。母亲也不例外,但母亲是勤借勤还,再借不难。借来用了的东西 用罢后要仔细地打磨和擦洗干净了才肯还人。但有人借了母亲的镢头 用过后却连泥带水地还来,母亲也不生气,悄悄拿到柴房里打磨干净 后晾着,从来不给家里人说那些清汤寡水的事。 母亲干起农活从不鞧力,她的力量仿佛是一眼汩汩流淌的泉水, 从来就不会干涸。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一年四季她好像从来就没有 闲过。有时候,和母亲坐着扯闲话,问母亲那时候为什么总是那么 忙。母亲笑着说,那时候不忙,几个儿子的鞋都做不过来,一双新鞋 有时候穿不了一个月。现在好了,当娘老子的一看儿子女子的鞋破 了,到街上转上一圈,把什么鞋买不来。那个时候,手头紧,几个钱 都是四个蹄子拼来的,你看到柴房里那把镢头了吗?你们那时候身上 穿的戴的,吃的喝的,没有一样不是那把镢头挖出来的。那把镢头打 地里的胡基,锄草,开荒,砸干灰,也在春天的时候,挖草药换钱。 不说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母亲一笑就摆摆手不说了。 我想起来了,大概是我才上小学的时候。有年开春,村里来了一 群收草药的药贩子。主要收黄芪和柴胡。母亲起早贪黑地背着背篼提 着那把镢头到山野里去挖草药。每天背回一背篼。有时候,在油灯 下,母亲就悠长地叹息着、自言自语着,数着那命似的小钱,算着该 给谁添双鞋子了,该给谁买身衣服了。那时候,语文老师天天给我们 讲《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那些故事一直在我的心头萦绕,我就想 要一本《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书。我把我小小的愿望说给了母亲,母 亲笑着说,给你买一本。我把母亲买书的事始终放在心上,母亲也始 终把答应给我买书的事记在心里。后来,母亲挖草药攒了钱,给小弟 扯了一身新衣服,给我买了双新鞋,又托人到县城里的新华书店给买 了《一千零一夜》。我拿到书后,上课时偷着看,晚上在被窝里看, 硬是把它看了个透。也从那个时候起,我爱上了故事书,也喜欢上读 书,并成了班上的故事大王,天天给同学们讲故事。记得上初中一年 级的时候,我还拿过校园课余讲故事一等奖呢。 这些都是母亲用镢头流血淌汗挖来的。 春天到了,母亲会拿上那把钝刃的镢头到地里打打胡基,挖挖杂 草。有时,我们劝她把那把镢头扔了,换把新的。她笑着说,用惯了 顺手。好在地里的活儿现在不是很多,母亲也没有多少活儿可干,让 她用那把镢头她的心里舒坦。 我常常在心里想,母亲的这把老镢头今后也许会成为我家的一件 老古董而存放着,也许会成为乡村人工劳作的*后见证。 5.一根背绳 母亲是背着青山生活的。山洼里地沟塄坎上瘸连跛摆的人是母 亲;背着一捆青草踽踽独行的人是母亲。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的母 亲患有腿疾,走路不大利索。我的母亲是农民,作为农民,就得养一 些牲畜,养了牲畜就得喂草料。当年,我们弟兄三人都在上学,父亲 做点小生意常不在家,喂养牲畜的任务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母亲的 身上,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一般的事情都有个轻重缓急,可牲畜是 活物,是活物就得吃东西,而牲畜吃的全是草料,喂牲畜这样的事是 没有商量的余地的,只能源源不断地供给。我家人口少,土地*少, 因此草料总是不够牲畜吃的,不够吃就得上山去割。春夏秋冬,满山 遍野的沟沟洼洼都留下了母亲挎着背绳提着镰刀踽踽独行的身影。在 夕阳和晚霞里母亲总是负着一座草的山在移动,遮住了一大段夕阳和 晚霞的光亮。曾经有多少人赞美过也歌颂过夕阳和晚霞,可我一看见 在夕阳或是晚霞中独行的身影时,心似剪刀乱铰一样疼痛,眼前便蓦 地浮现出我的母亲来,也就实在找不出赞美的词句来。她纷乱的发丝 上汗迹斑驳地沾着一些草梗之类的东西,不堪回首啊,我不知道我的 母亲那时的劳动强度有多大,遇到现在我是干不了的。但母亲知道, 三个正长身体的儿子像饿狼一样,每天要吃一锅铁锅巴,乡里常说儿 多的母瘦,的确不错,母亲生养了我们兄弟三人,却也给自己挑起了 一副重担—— 一副永恒的不可推卸的重担。母亲虽然大字不识,但 却十分看重文化,在她的心目中,文化是高于一切的。她常教育我们 要好好念书,不要像她大字不识地窝在乡里,而是要走出去。当然, 这就需要她付出百倍的努力和辛劳。家中的牲畜需要她喂养,田里的 农活需要她干,她情愿把一生的青春搭上供儿子们读书,幸福地生 活。然而,我们念书却念得不怎么样,不是那么成功,她的教育在我 们幼小的心灵上也起不到任何震撼,她彻夜的诉说有时还不及老师的 一句表扬,老师在我们的心里是那么地可畏、可亲,父母的话可以不 听,但老师的话不能不听。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由于那时母亲常年 忙于家务,父亲忙于小生意不回家与我们交流太少的缘故。 真该陪陪母亲,与母亲说说话儿,可我却时常推说工作太忙抽不 了身不回家,就是连看一回小女儿也懒得动身,虽然思女心切。不知 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却生就了一身的惰性。有时却也害怕回家, 害怕直面母亲那双忧怨的眼睛。母亲生养了我,顾盼了我,也拉扯了 我,却又要为了我的女儿重新拿起她的背绳。女儿才八个月,不会说 话,*不会走路,却咿咿啊啊地叫着要母亲背她去玩去浪,一个不会 说话的婴儿,谁还有那么大的耐心哄她玩呢,只有我的母亲才像宝贝 一样地疼爱她。其实,母亲也是希望她能为我们抱抱孩子尽尽奶奶的 责任。然而,我知道,母亲是要把她多年来对儿子的爱表达出来,诉 说给还是婴儿的女儿。每当女儿哭泣时,她就用背绳背起女儿,在这 时候,我的眼前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母亲背负一大捆青草孤寂地行走 在田野上的身影。 **,母亲手边的背绳是用几条长长的布条拧成的,是一条花花 绿绿的五彩绳。这是她用过的背绳中*华丽也*柔软的一条。在前几 年,她拧此绳我们嫌淡它时,她说日后自有用处,显然,她在那时就 想到要替我们拉扯顾盼儿女。母爱无价啊。 母亲到底背断了多少条背绳,谁也说不清楚。可母亲的双肩磨起 的老茧至今馍头似的耸立着,到了节气就疼得呻吟不已,可谁又能 为她轻柔地揉一揉搓一搓减轻她的疼痛呢?我们都不在身边,不能 为她做点什么。有时,我想,母亲能向我们要求点什么有多好,可 她从不向我们张口要求什么。她说她是从贫寒和难辛中**天走过来 的,现在知足得很,还能有什么要求呢。但她还是有点奢望,就是要 我们在工作之余抽空能来看她,哪怕是双肩撑张空嘴,在她看来也 是欣慰的,可我们却往往满足不了她的要求。但我还是要虚情假意 地打着看望她的旗号去看女儿的,去了便给她说一大堆让她高兴的 谎话。不管你说什么,她总是满意的,高兴的。说话间,她熟练地拿 起背绳又背起了哭泣的女儿。她是用孙女把儿子的心牵住,牢牢地拴 在身边的。 母亲的手里握着背绳的一头,女儿扯着背绳的另一头。母亲看着 女儿笑憨了自己。背绳拴住了母亲和女儿,而我呢?究竟要拴在背绳 的哪一头呢?我很想知道。 6.在深巷中等待 昨晚,我又做梦了,梦见母亲在深巷中等我。梦中,母亲离我忽 远忽近,忽模糊忽清晰,总是,我近不了母亲跟前,扯不住母亲的衣 襟。十几年前读书的时候,每当放学回家,母亲总是双手抱在胸前斜 靠在大门墩上等我,满脸笑容灿烂绚丽,往往是等我扯住了她的衣襟 时才拉着我反身回屋。可梦中,母亲始终一脸的忧愁。我的心咚咚地 跳着,从梦中惊醒过来。我知道,母亲又想着她在外工作的儿子了。 我要回趟家,我即刻就决定好了。 母亲一定又在深巷中等我了。 想着回家就忆起了过去:清晨,我肩负着母亲的希望和嘱托从深 巷中一步稳似一步地走出;傍晚,母亲便满载着疲惫和辛劳从田野里 一步快似一步地奔回,日子跟着太阳周而复始,生一日循环不 止。那时候,我家的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似乎永远是一个样,上顿青 稞面疙瘩饭,下顿洋芋搅团,至今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永远只有贫寒 和清苦。**,当对一日三餐挑三拣四或难以下咽时,我知道我已经 在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母亲和自己,这是母亲坚决不 会答应的。年前,带领亲戚家一群孩子回家探亲。母亲又特意做了一 顿洋芋搅团,当时,把一群孩子吃得头顶冒汗,差点撑破了肚皮,还 争相要吃。母亲看着孩子们的馋相,站在锅台边上盛了一碗又一碗, 连脸上的皱纹都乐展了。我想,母亲一定想到了我儿时的馋相。我问 了母亲,她笑着没有否认。从那种清贫的日子里走过来的母亲就那样 给我上了一堂清贫课。 **早上,我给母亲打了电话说我已动身回家。母亲在电话那头 高兴得语无伦次。 班车摇摇晃晃地颠簸着,一车人昏昏欲睡,只有邻座的一位老奶 奶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满脸的思索。看着她的神态,我的心蓦地紧 缩了几下。她多像我的母亲。我终于忍不住试探着和她交流了起来。 得知她是去县城看她工作的小儿子去的。她天天捎话让她的小儿子回 家来看看她,可儿子单位工作太忙回趟家很困难。*后她决定自己去 看看儿子。但到了县城见了儿子,却又想回家。原来,她只是想见见 儿子。作为娘,就剩下这么点愿望了。她问我去哪儿,我说是去看我 娘。我说日子一久,我娘会想我,娘想我时会站在深巷中望我、等 我。她说,娘的心都拴在了儿女的身上,有几个儿女,就是把心掰开 也要拴上。儿女一走就带走了娘的心。娘的心*容易满足,但那不是 什么吃的东西穿的衣物所能代替的,而是在有机会时把娘的心带回去 看看,哪怕是你空着双手,娘的心也是满足的。听了老奶奶的一番感 慨,我的心灵雷击般震撼着,一阵酸楚涌溢而出,再也抑制不住自 己,热泪潸然而下。 在巷口,我的脚步迈得很沉重,我怕母亲又在深巷中等我。渐渐 地,离家门近了,我发现母亲依然像十几年前那样双手抱在胸前倚在 门墩上向巷口张望。 娘,你的儿子看你来了。我飞奔向前。 7.进城 母亲又一次从乡下进城来看她工作的长子。 星期六下午,从朋友处归来,看到门锁上挂着一个包,我知道母 亲又来过了。这已经是母亲第三次来看儿子而未遇着。我看着包里装 着东西,禁不住潸然泪下。一种歉疚和无限的思忆涌上心头。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在一盏孤灯的陪伴下,我的思绪又回到了 童年,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母亲啊,我希望永远亲近你,陪伴你,孝 敬你,我想扶住你瘦弱的身躯,可这些我都没有做到。 母亲,你是我人生旅途上的一盏明灯,你是端正我心灵基石的线 锤,你是给我拓宽真理之路的钢铲。 母亲,你还记得吗?那是我童年春后的某个黄昏,我放下当天念 诵的功课,偷偷地溜出了家门,到野地里去玩。那时斜阳西坠,晚霞 洗空,田野里山花烂漫,馨香盈溢。我趴在草丛中谛听风儿的歌唱, 聆听虫儿窸窸窣窣的碎语,任凭思绪天马行空。在天籁之音里我陶醉 了,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凉意浸透了身心,我从梦乡返回到了繁 星满缀的暗夜里。空旷的山野里隐隐约约地传来你一声声欲哭无泪的 呼儿声。我偷偷地、心神不安地溜回家,趴在被窝里装睡。你从外面 回来后,跟往常一样安排我吃饭、喝水,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我知 道,你肯定找遍了草房、院子里面的每一个角落。我吃完饭之后,你 严厉地让我跪在了炕上。我很惊讶,你究竟要我干什么呢?跪了十来 分钟,你威严地让我背诵当日的功课——一段《***》,当我背不 下去时,你一句一句地教,直至我如行云流水般地背诵时,你脸上才 露出了一丝欢欣的笑容。此后的岁月,我**收敛住了自己放纵的性 格,直至**。 母亲,多少年来,我记忆中抹不掉的就是你陪读的身影。 母亲,**,当我接近污秽、邪恶或步入迷途时,你严厉的目光 总是在告诫我——远离,远离。使我却步,使我醒悟。 母亲,我怎样感激你呢?你把我无邪的幼小心灵放在大地宽厚的 胸膛里,用辛勤的汗水浇灌,而没有放在溺爱的温室里。母亲,我在 你的臂弯里读着风雨成长。 母亲,你蹒跚在那乡间的小道上时,我就是你脚下匍匐的一棵 小草。 母亲,当我仰首读你额头那饱经风霜的“沟壑”时,信仰的光亮 中我看到了一片纯洁和灿烂,使儿感到多么自豪呵…… 8.像阳光一样微笑 母亲的前门牙掉光了,很多时候在人前是不敢笑的,怕别人笑 话。只有与儿子媳妇和孙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她才放松了身心,笑容像 一只熟透的柿子突然长破了身子。 女儿有时候看着奶奶的笑容就说像太阳的笑。奶奶就问太阳的笑 是怎样的一个笑。女儿说,太阳的笑是甜甜的笑,暖暖的笑,艳艳的 笑,可爱的笑。女儿说着就拿来了一张图画,图画上的太阳笑得灿烂 无比。奶奶看着孙女的太阳就笑了,笑得比灿烂的太阳还灿烂。 有了自己的家,也因工作太忙,就很少去乡下母亲家里。过一段 时间,母亲总要打个电话来,问女儿生病了没有,女儿的学习好不 好。这时候,我知道,母亲其实*想问的还是我,虽然她只是在问女 儿的时候捎带着问我几句。然后叹息着说上几句听不懂的话儿,像是 自言自语。 我决定带上女儿回家看趟母亲。到了**,我没有给母亲打电 话,带上女儿买了点东西搭上班车回乡下老家了。 在村外下了车,村街上偶尔有人影晃动,偶尔也有鸡啊羊啊地跑 过。晚风轻轻地拂着,家家烟囱里的炊烟浓浓地冒出了屋顶。家家户 户都在做晚饭。 进了家门,弟媳开力曼在院子里看了一会儿才笑着跑过来接过了 我手中的包,朝屋里大声地说给母亲听,说城里的孙女看您来了。 母亲闭着眼坐在炕上一动不动,显然她不相信城里的孙女会来 看她。 我拉着女儿悄悄地走到炕边,道了色俩目问好,女儿大声地喊 道——阿婆!我来了。母亲才睁开眼回道了色俩目,笑着说,我正 打盹儿呢,听开力曼说,我还没相信呢。母亲迅疾地下炕要给我们倒 茶水端馍馍。 女儿拉住奶奶的手说,我要好好看看阿婆,看看阿婆没牙的笑容。 母亲就笑给女儿看。女儿说阿婆笑得像不像长破的柿子。 女儿说,阿婆的笑像秋天的阳光,灿烂极了,可好看了。 母亲经女儿这么一说,就一直笑个不停,像深秋艳艳的阳光一 样,笑得再也合不拢嘴。 我明白,母亲不是为了女儿的那句话才笑得像深秋的阳光似的, 而是见到了久久没有回家的儿子,心里高兴着呢。 作为娘老子,是*容易满足的了,只要儿女时常来看看他们,和 他们说说话儿,哪怕是生活过得清苦一点,日子过得紧巴一点,他们 也没有过高的要求,只是希望儿女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日子过得红 火一点,她们的心里就没有了过多的牵挂和愁肠。他们的脸上就会时 常挂一副阳光似的微笑。 只要我们娘老子的脸上天天挂着一副阳光似的微笑,我们也就心 满意足了。 9.明亮的月光轻柔的手 母亲推门进来的时候,裤边和鞋面上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飘逸 的黑盖头上沾了一层尘埃,像落了层霜似的,雾尘尘白煞煞的。显 然,母亲是走了几里土路再搭上班车来的。从咱家搭车到县城来是要 走几里土路的。有时候,有进村的面包车或是出村的三轮车,凑巧碰 上了,去县城的人就少走那几里坎坷不平的土路,要是不凑巧,就不 得不磕磕绊绊地走那几里土路。母亲就是不凑巧才白白地走了那条土 路的。 母亲的肩上挎了一个大大的绿帆布包,沉沉的。女儿听到了奶奶 的声音,从她的卧室里跑了出来,扑在了奶奶的身上。女儿是母亲一 手拉扯大的,对奶奶的那种感情往往胜似我和她妈妈。在这个时候, 母亲往往会春风吹拂般地把自己喜成一朵红朗朗的山丹花,笑得艳艳 的。然后随手丢下挎在肩上的帆布包,用她粗粗的大手抚摸女儿的脸 蛋。女儿则像一只温驯的羊羔偎依在奶奶的怀里,显得那么娇憨和可 爱。她幸福地看着我和妻子,挤眉弄眼地笑着,笑容坏兮兮的。 女儿对奶奶的感情叫妻子不得不忌妒,不得不羡慕。女儿对奶奶 的感情是真实的,有时候,当她调皮了,妻子训斥上几句时,她就受 不了,便悲恸欲*地号啕大哭,谁也劝不住谁也哄不好,只有一个劲 地喊着阿婆,哭够了时,才会理你,也才肯听你的劝听你的哄。 女儿说,阿婆就是她的月亮,没有阿婆就是一片黑暗。妻子受不 了女儿这样的形容,就笑着对女儿说,我生了你,是阿婆拉扯了你, 但你对阿婆太偏心眼儿了。女儿回敬说,谁让你生下我不拉扯我,我 又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要不是阿婆拉扯,我怎么能够长大呢。 女儿几句话就把妻子顶撞得无话可说。可女儿还是那一句话,我是月 亮护善下的一棵小草。只要奶奶一来,我的心里就亮敞了。女儿说得 没错。女儿刚生下时,妻子的胃病就犯了,疼得整日整夜地睡不好 觉,无暇顾及女儿,*顾不上拉扯女儿了。母亲看着妻子被胃病折磨 着,心焦得没有任何办法。一面心疼着照顾妻子,一面又心疼着照看 女儿,把母亲累得够呛。可母亲从来就没有叫过苦喊过累。她知道拉 扯女儿的任务已经归她了。母亲既要照顾妻子又要照看女儿,常常累 得坐在床上挣弹不起来。她被女儿的那双幼小无助的眼神常常弄得手 足无措,虽然她一生亲自拉扯大了我们兄弟几个,但她从未费过这样 大的神。照母亲的话说,我们几个是老的拉大的,大的拉小的,她还 没明白过来,我们几个就长大成人了,成了雄壮壮的男子汉。可拉扯 女儿让她费尽了心思。尤其是女儿从生下不到一月就整日整夜地啼 哭,母亲也就整日整夜地抱着女儿在屋子里抖着拍着转来转去,硬是 把那光滑瓷实的砖地用脚磨出了一道深槽。女儿从不到一个月,哭到 了一岁多。现在女儿已经七岁了,但只要她一哭,母亲的身子就不由 自主地抖个不停,这是七年前女儿整日整夜地哭泣让母亲落下的病。 母亲说,她*听不得的就是娃娃的哭,只要一听到娃娃的哭,她的心 就抖得不行,心脏也就不那么好受。 女儿跟着母亲一起生活了四年,当母亲把女儿生拉硬扯地领到县 城里引给我们时,女儿已经跟她分不开了,女儿倒成了她身上的肉, 而我们却不再那么让她牵挂了。每次打电话来,母亲总是说:叫曼茹 叶来接电话。此后时间久了,只要是乡下家里来电话,妻子总是让女 儿去接。女儿接了电话,婆孙两人在电话里东拉西扯地聊开了天,再 也罢休不了。有时候通话时间久了,小弟在电话那头大声地笑着说, 又挣电话费了。母亲就嘿嘿地笑上几声,安慰着鼓励上女儿几句才极 不情愿地挂上电话。后来,母亲每隔一个月,就要带上一些东西风尘 仆仆地前来看她的孙女,时间掌握控制得像十五的月亮,不差时日地 轮回。 女儿也习惯了奶奶的到来,也时常计算着日子等奶奶。有一回母 亲病了,提前打电话给女儿说她暂时来不了。女儿就失神地像霜煞了 的花骨朵,蔫唧唧的提不起一点精神来。奶奶想着女儿,女儿思谋着 奶奶,*终母亲弹挣着来看女儿,女儿哭了整整一下午,连学都不肯 去上了。母亲说,拉大的娃娃养大的羊,人亲门亲。再长大一点,她 就不黏人了。但女儿好像从来就长不大似的,只要母亲一来,她还是 往奶奶身上贴,贴得紧紧的。妻子笑着说,女儿现在就认准了一个阿 婆,不认我们了。但女儿不管我们的内心感受,还是往奶奶身上贴, 只要受到委屈或是受到我和妻子的责备,她准一个劲地喊着阿婆哭个 不停。有时候在睡梦里都喊着阿婆,还笑得格格的。可女儿从梦中醒 来起身一看我和妻子,惊奇地思谋上一会儿,就悻悻地埋在被子里, 谁也不理会了,显然她是知道了是在梦中和阿婆说笑。 我们知道,女儿从小就受了母亲的指教,不在人前调皮,不接任 何人给的钱,从小就知道尊重人,怜悯人。要是走在大街上,见着讨 要的人,她总是嚷着要我们给些小钱。女儿的这些举动曾让我和妻子 汗颜。有一次**,我们上街,见烈日下一位老奶奶盘腿跪坐在街头 伸手讨要,女儿便停住脚步不走,妻子知道女儿想要给钱了,但我和 妻子都没有小钱。妻子小声对女儿说,没有小钱,回来时再给吧!女 儿白了一眼妻子说,刚才出门的时候你手里不是有十元钱吗?妻子心 疼地看了我一眼,极不情愿地从包里像掏命似的掏出钱塞给了女儿。 女儿接过钱,往展里抖了抖,然后像一个大人似的对妻子说,这还差 不多。其实妻子不是一个惜钱如命的人,以前她看见那些讨要的人总 是心软地给些钱,但这两年来,买了房拉了债,妻子在用钱上分分厘 厘划算。女儿的举动让她心疼,但为了女儿那颗未泯的童心和爱心, 她只有苦笑。然后夸着女儿说,好女儿有疼心。女儿却不高兴了,努 着嘴说,明明有钱,就是不掏出来。妻子说,我试你呢,看你是不是 对穷人有疼心。女儿说,那个讨要的人比阿婆还要老,上次阿婆来领 我上街,也给了十元钱。我和妻子明白,这几年我们拉债买房,成了 房奴,没有给过母亲一分钱。但母亲却大手地给女儿做着榜样,让女 儿幼小的心灵从小就感受到怜悯、同情和尊重人。母亲虽然惯着女 儿,但也用自己的行动无声地教育着女儿。我们小时候,来庄子里讨 要的人很多,母亲从不让一个讨要的人空手而归或是失望着离去。有 时候,讨要的人往来复去地来上两三次,但母亲仍微笑着给人送去一 碗温暖。那时候,家里没有钱,讨要的人要是赶上吃饭,不管是男是 女是老是小,母亲都要叫进家来,倒上一杯热茶,再盛上一碗热饭, 让讨要的人热热乎乎地吃上一顿。**,她用她的行为又教给了女儿 疼爱的心肠,这让我们感到欣慰。我们还要教给女儿什么呢,有这些 就够了。这会让女儿的一生受益无穷。 在女儿未来的生活中,母亲的指教像明亮的月光永远普照着,造 就着女儿永远善良和温暖。 ?在思考和书写中,与乡亲们的灵魂说话,与田野说话,与树木说 话,与河流说话,与心爱的庄稼说话,聊天,吐露心曲。写栽种、写 农事,写得细腻、深情、美丽,享受农村的美,享受农活的快乐,体 验丰收的喜悦,从而深深眷念、关心农村、关心生养我的父老乡亲的 生活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