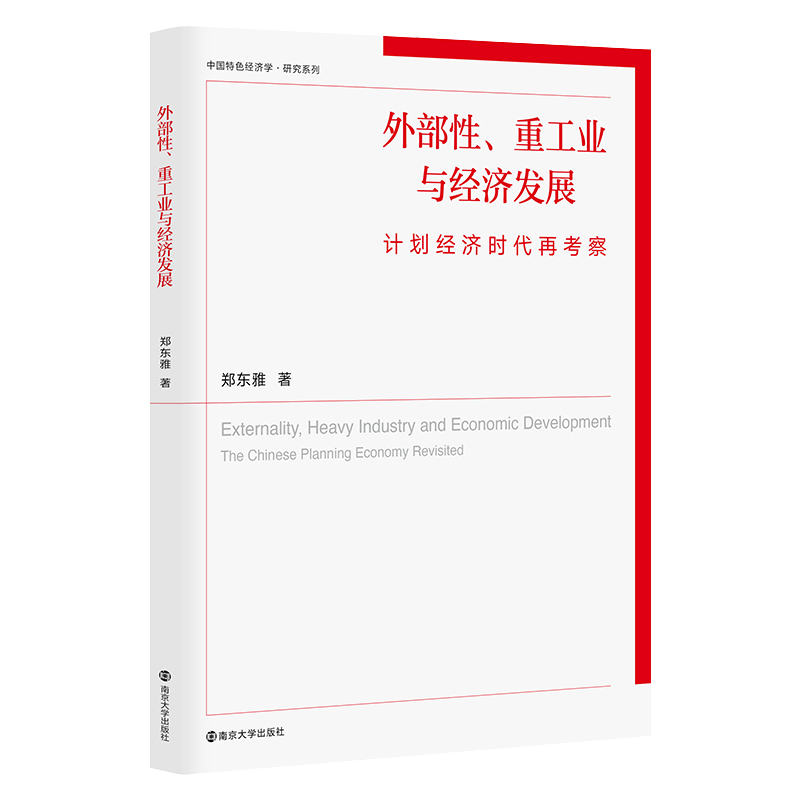
出版社: 南京大学
原售价: 55.00
折扣价: 34.60
折扣购买: (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系列)外部性、重工业与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时代再考察
ISBN: 97873052726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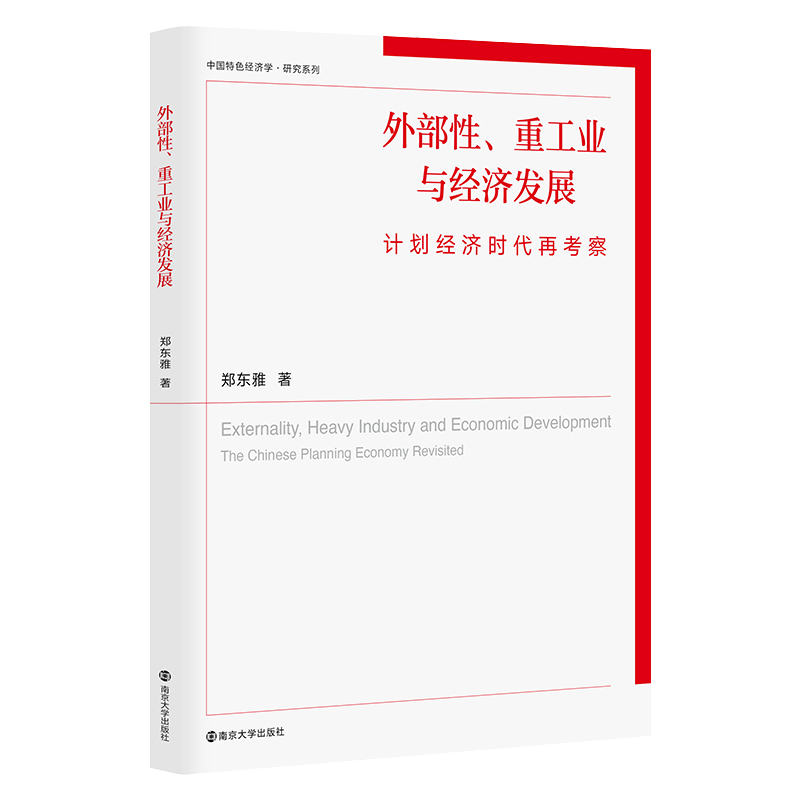
郑东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商学院产业经济系教师。博士论文《外部性、重工业与经济发展》荣获北京大学2010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基础工业和脱离贫困陷阱》荣获2022年度《世界经济文汇》最佳论文。
试读(摘自本书 第六章 总结) 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或者通过赫希曼根据产业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提出的“不平衡增长”,打破纳克斯提出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实现经济的结构转换。他们系统地提出一些发展战略以及政府在规划和计划中的作用。 然而由于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并没有解决大规模的贫困,许多人谴责政策导致的扭曲和由于公共政策而产生的非市场失灵,经济学家日益摆脱对发展规划和计划的迷恋。20世纪80年代第二代发展经济学家支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复苏”,中心在市场、价格和激励,倡导最小限度的国家。 随着人们对“新市场失灵”的认识,新增长理论对知识、外部性和动态收益递增的探索,为因资本积累而产生的收益递增和外部性的协调提供了基础。“因而出现了向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重视因市场规模影响而产生的收益递增……重要性的回归。”人们重新意识到政府在处理新市场失灵(不完全信息、不完全市场、动荡的外部性、规模收益递增、多重均衡和路径依赖性)仍然具有广泛的功能。 墨菲、施莱费尔和维什尼(1989)用数学形式化方法重新对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加以严密表述。墨菲等人认为经济存在外部经济,比如说一个企业工业化提高工人的工资从而提高其他企业产品的需求使得其它企业工业化有利可图,但是该企业无法把这种收益内部化。由于任何一个企业单独工业化无利可图,所以经济可能会出现所有企业都没有工业化的状态,从而陷入贫困陷阱。但是如果通过大推进,所有企业同时工业化,那么所有企业都有利可图,经济则走向高水平均衡。 西科恩和松山(1996)发现由于存在不完美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单个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可以通过现金外部性转化为总量水平上的收益递增。由于中间品的生产需要数额较大的固定投资,如果市场规模过小,报酬递增的技术无法在经济中得到充分利用,所以经济可能会陷于贫困陷阱。 墨菲、施莱费尔和维什尼(1989)虽然考虑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只考虑部门间的水平外部性。西科恩和松山(1996)虽然考虑了垂直外部性,但是没有考虑垂直外部性对工业化进程的关系,而且也没有考虑水平外部性。 我们试图在包括农业部门、轻工业部门和重工业部门的三部门框架下同时考虑互补性和规模经济导致的贫困陷阱,同时考虑水平外部性、垂直外部性和工业化进程。一方面,经济存在外部经济,重工业的发展为轻工业企业提供了更多种类的机器设备,提高了轻工业企业的盈利性,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但是重工业企业无法把这种收益内部化。另一方面,经济存在规模经济,由于重工业的投资需要固定成本,所以重工业企业能否获利就可能取决于采用现代技术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的数量。如果经济比较落后,工业化比例较低,轻工业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较少,从而重工业投资无利可图,轻工业没有重工业的机器设备配备效率更低,从而工业化比例很低,经济陷入贫困陷阱;如果经济比较发达,工业化比例较高,轻工业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较大,从而重工业投资有利可图,轻工业在重工业的机器设备配备下效率提高,工业化比例提高,经济迈向高水平均衡。 近年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界重新审视了早期结构思路的理论文献,发现其中有不少“已经被忘记但却很有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令人吃惊的激发出许多解释”(Krugman,1995)。但是正如奥利韦拉(Olivera,1992)认为,“结构主义的主要弱点,可能在于它所开出的政策药方上”。斯特里顿(1984)则指出,结构主义者犯了过于简单化的毛病,“他们在观察并分析了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后,就匆匆做出结论说,中央政府必须代替市场,……不认为国家应当把市场作为计划化的有力工具,把价格作为政策的有力工具来结合起来”。上述两篇文章都没有讨论政策建议,政府通过什么方式才能使经济从坏的均衡到好的均衡。 我们认为,当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由于轻工业对重工业的需求较少,重工业的市场规模较小,而重工业投资需要固定成本,重工业投资无利可图;但是如果此时,我们对新建的重工业企业投资进行补贴,那么较小的市场规模可以支撑该重工业企业得以投产,轻工业由于有了机器设备配备效率提高,工业化比例提高,对重工业的需求增加,重工业的市场规模扩大,可以支撑新的重工业企业投产,打破恶性循环,经济迈向高水平均衡。我们看到,由于重工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和垂直外部性,苏联和中国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迅速工业化。苏联1928—1940年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6.8%,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学者把它调整为10%~14%。中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期间,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达到79%、8.2%和6.0%,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从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但是苏联自1958年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一直到后来难以为继,直至解体。中国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是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消费品种类单一,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显著提高。为什么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后期会给经济造成种种恶果?正如赫希曼后期进行反思,他认为如果只考虑后向和前向联系,那么就有可能有侧重重工业的倾向,而如果赋予了消费联系应有的作用,这种倾向就会消失。 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考虑了轻工业同样具有外部性。中间品和消费品的生产都需要一个前期投入,因此都具有规模经济。一种产品能否被生产,取决于对它的需求的大小。在这里,中间品和消费品的生产通过需求效应是相互促进的。容易理解,消费品种类和产量的增加,带来对中间品需求的增加。反过来,中间品种类和产量的增加提高收入水平,因此提高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随着经济的增长,消费品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它的需求效应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对重工业的补贴因此应该降低。由于忽略了轻工业的外部性,“以产为纲”,“为生产而生产”,计划经济时代对重工业的补贴率高达37.57%,且持续时间长达25年,因此造成了轻重工业比例的严重失调,消费品种类单一,到1991年为止,居民的效用贴现和仅为不实行这种战略下的761%。但是我们也发现,如果考虑到轻工业的外部性,以所有人的长期福利为目标,实行合适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则对重工业的补贴率应该为31%,而且到1966年就应该取消补贴,则到1991年,所有居民的效用贴现和比不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还高1.85%。所以,目前对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实践中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过头了。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那么它就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的计算是在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模型框架下进行的,它没有考虑重工业优先发展可能使经济逃离贫困陷阱所带来的效用,也没有考虑重工业优先发展对居民福利之外目标的作用,比如说强大的国防力量。 本书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道路的反思尚存在不足之处。我们的模型假设消费者和厂家是分散决策的,而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消费者的消费受配给的影响,厂家的决策受政府计划的限制。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可用的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微观主体决策模型。如果说苏联的消费和生产都是政府计划决定的,那么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离政府计划还差得很远,政府的各个层级以及微观行为主体都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我们承认我们的分散决策模型不是对中国现实的真实描述,但同时也认为,这个模型可以作为对中国现实的一个近似,在最低层次上,它也为我们理解现实提供了一个基准。 重工业由于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性对于经济发展有特殊的意义,下面是本书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第一,利用中国数据检验重工业对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者们一直无法解释增长回归方程中的“索罗残差”项,而只能将之简单归结为“技术进步”,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经济学中分析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技术还没有出现。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要素增长率较高,按照我们的理论,由于重工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性,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大大提高。而这不单单是因为资本的积累,重工业和轻工业在经济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第二,检验中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对于中国改革后的高速增长的贡献。张军(2005)认为,对于一个以工业化过度发展为特征的计划经济而言,“增量改革”或鼓励新兴工业部门横向进入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改善资源在部门间的配置效率。因此,在逻辑上,中国在改革后的高速增长似乎就应该是由资源在部门间的再配置所产生的静态收益增量来解释。他建立了一个很简单的理论框架,并且1979—1994年资本—产出比率的平均增长率为-0.89%,这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TFP)有一个显著的增长,所以这个增长可以用转轨初期的配置效率的改善过程来解释。但是张军(2005)使用资本—产出比率这个指标进行说明,我们希望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 第三,利用世界各国数据验证重工业优先发展是否有利于逃离贫困陷阱。当经济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有可能逃离贫困陷阱;而经济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时,很有可能一直陷于贫困陷阱,经济发展缓慢。 我们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发学者们探讨重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意义以及政策建议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探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发展战略对于当时以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