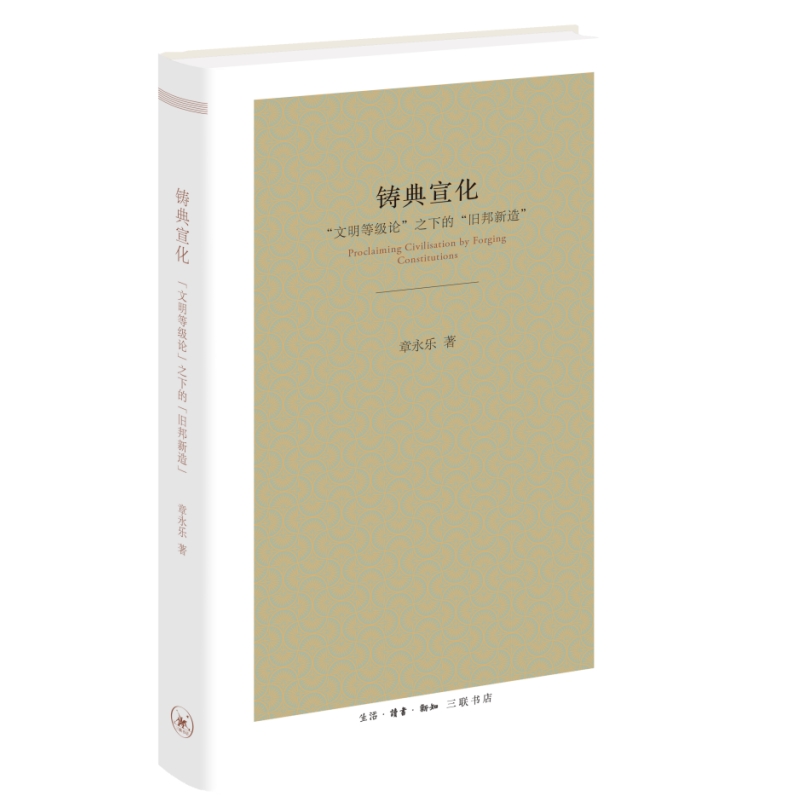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4.90
折扣购买: 铸典宣化(文明等级论之下的旧邦新造)
ISBN: 97871080787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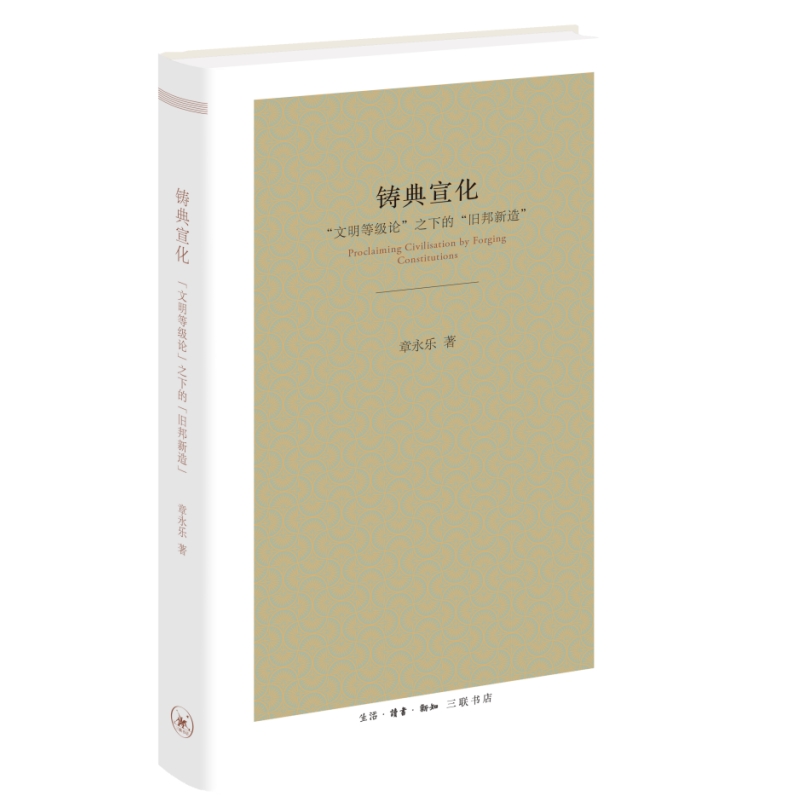
章永乐,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法学学士(2002),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2008)。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兼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长期从事问题导向的法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思考全球秩序的变迁与中国道路探索实践的理论化,尤其关注国家建构与宪制变迁、帝国与国际法、政党与代表制、政治伦理与法律伦理等议题。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西途东归:朝向中国道路的思想突围》等,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
界大战的冲击与“20世纪之宪法”观念的兴起 节选自《铸典宣化》绪论第二节 自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战争的变化,时刻牵动着中国舆论界的目光。自诩“文明”的列强在欧洲战场上进行着猛兽式的搏杀,上千万条人命灰飞烟灭。而德国的战败尤其具有冲击力。战前中国主流舆论界的不少精英从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底色的“文明等级论”出发,认定德国是西方最为先进的力量,德国与英国的争霸,是“新”与“旧”的斗争,“进步”与“落后”的斗争。而德国的战败,导致人们对战前的“文明”话语产生深刻的怀疑。“竞争”“优胜劣败”“军国主义”这些在战前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逐渐被视为导致相互毁灭的思想根源。而欧洲精英在“一战”后更是对自身的文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对战前流行的许多思潮做出了否定。1918年德国学者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出版《西方的没落》,将“文明”(zivilisation)视为“文化”(kultur)发展从高峰走向衰亡的最后阶段,从而将德语世界中“文化”(kultur)与“文明”(zivilisation)的观念对立推到一个新的高峰。梁启超在1919年访欧期间就拜访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与德国哲学家倭铿(Rudolf Christoph Eucken),听取他们对于欧洲文明的反思。而1920—1921年访华的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则在中国公开批评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文明,赞赏中国传统的人生态度。这一切都对中国的舆论界产生了影响。 在“一战”之前,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相并列的用法在中国舆论界较为少见。“一战”的推进带来思想界格局的变化,这种并列的用法与日俱增,而这意味着“文明”观念正在从一种一元的、等级性的范式,转向一种多元的、更为平等的范式。中国秦汉以来形成的大一统、崇尚和平的传统,在“一战”之前的中国舆论界饱受批评,被认为压抑了竞争,从而导致中国在与所谓“文明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一战”中列强的相互厮杀,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东方文明”做出正面评价。“竞争”观念地位的下降导致了“协作”“和平”观念地位的上升,社会主义获得了更为正面的评价,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论证:中国的古代传统中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甚至孔孟都可以被视为早期的社会主义者。 就国际体系的结构而言,“一战”打破了原有的君主国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协调”体系,释放出了被“大国协调”压抑的工人运动与民族独立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协约国取胜,德意志第二帝国覆灭,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解体,一系列民族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新共和国或复国(如波兰),这导致共和政体在欧洲不再处于边缘地位,自下而上的“人民主权”的法理,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在战前“文明等级论”的视野里,工人与农民被视为“文明程度”低下,缺乏行使政治权力的责任能力。然而,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获得普及,“劳动创造文明”成为新的信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与农民就摆脱了在19世纪文明论中的“内部野蛮人”的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的正当性。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更是将工农的政治地位推到了新的高度。布尔什维克支持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殖民主义的“文明等级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我们可以从秉持19世纪“文明等级论”的人士的反应,来观察这种冲击的规模和力度。在1923年初版的《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R?mischer Katholizismus und politische Form)一文中,时年35岁的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这样评论俄国十月革命:“自19世纪以来,欧洲出现了两大反对西欧传统和教育的人群,两大漫溢河岸的川流:进行阶级斗争的大城市无产阶级;与欧洲疏离的俄国群众。从传统西欧文化的观点来看,这两大人群都是野蛮人。当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时,他们就骄傲地自称为野蛮人。”[施米特在此仍然是站在19世纪欧洲主流的文明论立场来看待十月革命,将其视为欧洲边缘民族和无产阶级两股“野蛮人”的合流。在19世纪的文明等级论之下,他们被视为“文明程度”不足、需要被拒绝乃至延迟进入政治场域的力量,是欧洲“教化”的客体。而与之相反的是,1920年3月,不到27岁的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热情洋溢地评论:“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显而易见,毛泽东抛弃了19世纪的主流“文明”尺度,而以战后新的“文明”尺度来看待俄国十月革命以及苏俄。 当然,由于美国战时官方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Public Information Committee)在华的运作,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媒体对其报道和评论的频率,还比不过对威尔逊政府对于战后国际秩序主张的报道。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在中国一度享有极高的威望。许多中国舆论界的精英往往无法分辨威尔逊的主张与列宁的主张有什么实质差别,却对前者寄托了很多的希望。然而,威尔逊为了推动自己的国际联盟计划,在巴黎和会与日本做了交易,同意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导致了中国舆论界对于威尔逊的印象极速转向负面。而列宁则主张废除俄国旧政权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威尔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国共进行了第一次合作,启动国民革命,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广州国民政府的“反帝”主张,推动北洋政府也对列强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直接冲击列强在中国的殖民主义统治秩序。 就内政来看,无论民初的中国政坛多么风云变幻,宪法话语始终在政治正当性话语中具有极强的存在感,大多数具有一定实力的政治势力都试图掌握“法统”,主导国会,控制宪法制定或解释权。这种状况的持续,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中国国内没有任何一派势力具有压倒性的力量,因而还需要通过“法统”话语来凝聚政治盟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以“立宪”获得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承认的思维与行为惯性仍然在持续。而在“一战”之前与“一战”初期,我们在民初的法统政治中,仍然可以看到相当密集的“文明”话语。……这一话语模式也体现在舆论界对于1917年张勋复辟的反应。……在张勋复辟失败之后,陈独秀作《复辟与尊孔》,认为复辟的思想根源在于孔教:“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陈独秀预设君主制是“文明进化”的阻力,而尊孔导致君主制复辟,因而也成了“文明进化”的阻力。 1916年,梁启超为反袁的护国军打造了一套捍卫共和宪法的论述;而到了1917年,当梁启超与段祺瑞站在一起,拒绝恢复《临时约法》时,孙中山却借鉴了梁启超在1916年的宪法论述,打出了“护法”的旗号;甚至到了1922年,当直系军阀试图打掉孙中山“护法”旗帜的正当性,推动南北统一时,使用的还是法统政治的手段:直接宣布恢复《临时约法》法统,实现“法统重光”,试图让南方的“护法运动”无法可护。1923年,孙中山断然放弃了“护法”旗帜,转向国共合作,发动新的革命。而这场革命不再像辛亥革命那样,承认列强在华的特权,致力于通过自身“文明等级”的提升,让列强承认我们为平等的国际法主体;相反,它将矛头对准了列强主导的秩序本身,主张立即废除列强在华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种种特权。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列强“大国协调”的国际秩序,在“一战”期间已经分裂了,在战后也未能获得有效重建,通过“立宪”来获取列强承认为“文明国”的思路,当时已经找不到一个能够全面控局的承认方。而与孙中山建立合作关系的苏联,恰恰是被战后的凡尔赛体系排斥的力量,致力于改造而非融入既有的国际体系。……瞿秋白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在侵略殖民地的时候,往往会扶植当地的封建势力。因而,对于中国而言,只有同时推进“反帝”与“反封建”,才能摆脱原有的被剥削与压迫的状态。因此,需要推进的正是“世界革命”,而非“立宪”。 “一战”之前,“立宪”的形式本身就具有“文明等级论”的意义;在战后,“立宪”形式本身的重要性显著下降了,而宪法文本所规定的实质内容的重要性却在上升。 “一战”之后,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中国都出现了一个制宪热潮。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的重要代表人物张君劢翻译介绍了德国《魏玛宪法》,将其定位为“20世纪之宪法”,并与所谓的“19世纪之宪法”相对比,在当时中国的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之宪法”被视为具有社会主义色彩,关注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而“19世纪之宪法”的自由主义外表下掩盖的是对有产者的保护。正如汪晖指出的那样,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所谓“19世纪”是在“20世纪”的话语出现之后,才获得追溯性命名的,这一点在当时的宪法论述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论者先产生了“20世纪之宪法”的观念,然后才有了对“19世纪之宪法”的追谥。在战后中国的舆论界,一些论者甚至将两个世纪的划分用于对民初《天坛宪法草案》的反思,认为其体现的仍然是“19世纪之宪法”的概念,重在保护有产者而非劳动者。 然而,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制宪热潮,其领导与推动力量要么是北洋集团及其合作者,要么是介于北洋集团与广州政府之间的“联省自治”力量,虽然“20世纪之宪法”提出了如何保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与农民的权利问题,但北洋集团与非北洋的地方实力派真正依靠的力量仍然是军队、地方士绅与列强。……而国共两党在1923年启动的合作,决定性地将宪法问题的重点,从“宪定权”转向了“制宪权”,亦即,必须先解决哪些力量属于“国民”或“人民”这个制宪权主体的问题,才能进一步规定宪法的形式。 于是,“20世纪之宪法”的话语如同“渡河之舟”,国共两党继续前行,形成了自身的宪法话语传统。……而对共产党人而言,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之前的社会形态都是过渡性的,所有宪法都需要根据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与时俱进。20世纪30年代在中央苏区的制宪,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苏联的理论,尚未产生系统的本土宪法理论。…… “20世纪之宪法”的名称貌似从后续的历史进程中消失了。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而言,“一战”结束之后的“觉醒年代”,正是他们思想的形塑期,当时舆论界关于宪法与时代精神的讨论,对于他们思想的成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因而,重新认识“20世纪之宪法”观念的兴起和后续命运,对于理解“一战”之后革命与立宪的历史进程,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书是章永乐继《旧邦新造:1911—1917》《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西途东归:朝向中国道路的思想突围》之后的第五本专著,思路和议论都和他前几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是对“旧邦新造”这个话题的继续深入推进。 这本书偏重探讨近代中国宪制思想与“文明”观念的变迁,阐述中国宪制探索的文明史意义。通过梳理“文明”的话语体系与成文宪法的全球化传播,研究近代中国的“立宪”观念与道路,探讨“文明”的话语在“立宪”传播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帮助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立宪改革背后的历史逻辑与思想渊源,把握国际体系与国内立宪改革间的深刻关系,思考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脉络。
本书是章永乐继《旧邦新造:1911—1917》《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西途东归:朝向中国道路的思想突围》之后的第五本专著,思路和议论都和他前几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是对“旧邦新造”这个话题的继续深入推进。 这本书偏重探讨近代中国宪制思想与“文明”观念的变迁,阐述中国宪制探索的文明史意义。通过梳理“文明”的话语体系与成文宪法的全球化传播,研究近代中国的“立宪”观念与道路,探讨“文明”的话语在“立宪”传播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帮助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立宪改革背后的历史逻辑与思想渊源,把握国际体系与国内立宪改革间的深刻关系,思考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脉络。
书籍目录
绪论 作为“文明”事业的立宪
一 立宪、国家组织力与文明
二 世界大战的冲击与“20世纪之宪法”观念的兴起
三 “文明”的话语与“中国式现代化”
第一章 大国协调、文明等级论与立宪
一 维也纳体系及其全球扩展
二 殖民秩序与“文明等级论”的引入
三 立宪与“文明”
四 余论
第二章 激辩《明治宪法》
一 为何以日为师:梁启超的理由
二 出洋考察大臣奏折中的“立宪”与“文明”
三 立宪、革命与文明:革命派的论述
四 余论
第三章 世界大战与“文明”观念在中国的渐变
一 德国作为典范:“一战”前的论述
二 战争初期的德国形象
三 战争局势与舆论之渐变
四 战后世界的“文明”观念
五 余论
第四章 渡河之舟
一 “20世纪之宪法”观念的生成
二 “20世纪之宪法”观念的时代影响
三 新宪法与新文明
四 余论
后 记
试读内容
世界大战的冲击与“20世纪之宪法”观念的兴起
节选自《铸典宣化》绪论第二节
自1914年“一战”爆发,欧洲战争的变化,时刻牵动着中国舆论界的目光。自诩“文明”的列强在欧洲战场上进行着猛兽式的搏杀,上千万条人命灰飞烟灭。而德国的战败尤其具有冲击力。战前中国主流舆论界的不少精英从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底色的“文明等级论”出发,认定德国是西方最为先进的力量,德国与英国的争霸,是“新”与“旧”的斗争,“进步”与“落后”的斗争。而德国的战败,导致人们对战前的“文明”话语产生深刻的怀疑。“竞争”“优胜劣败”“军国主义”这些在战前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逐渐被视为导致相互毁灭的思想根源。而欧洲精英在“一战”后更是对自身的文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对战前流行的许多思潮做出了否定。1918年德国学者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出版《西方的没落》,将“文明”(zivilisation)视为“文化”(kultur)发展从高峰走向衰亡的最后阶段,从而将德语世界中“文化”(kultur)与“文明”(zivilisation)的观念对立推到一个新的高峰。梁启超在1919年访欧期间就拜访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与德国哲学家倭铿(Rudolf Christoph Eucken),听取他们对于欧洲文明的反思。而1920—1921年访华的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则在中国公开批评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文明,赞赏中国传统的人生态度。这一切都对中国的舆论界产生了影响。
在“一战”之前,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相并列的用法在中国舆论界较为少见。“一战”的推进带来思想界格局的变化,这种并列的用法与日俱增,而这意味着“文明”观念正在从一种一元的、等级性的范式,转向一种多元的、更为平等的范式。中国秦汉以来形成的大一统、崇尚和平的传统,在“一战”之前的中国舆论界饱受批评,被认为压抑了竞争,从而导致中国在与所谓“文明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一战”中列强的相互厮杀,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东方文明”做出正面评价。“竞争”观念地位的下降导致了“协作”“和平”观念地位的上升,社会主义获得了更为正面的评价,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论证:中国的古代传统中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甚至孔孟都可以被视为早期的社会主义者。
就国际体系的结构而言,“一战”打破了原有的君主国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协调”体系,释放出了被“大国协调”压抑的工人运动与民族独立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协约国取胜,德意志第二帝国覆灭,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解体,一系列民族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新共和国或复国(如波兰),这导致共和政体在欧洲不再处于边缘地位,自下而上的“人民主权”的法理,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在战前“文明等级论”的视野里,工人与农民被视为“文明程度”低下,缺乏行使政治权力的责任能力。然而,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获得普及,“劳动创造文明”成为新的信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与农民就摆脱了在19世纪文明论中的“内部野蛮人”的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的正当性。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更是将工农的政治地位推到了新的高度。布尔什维克支持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殖民主义的“文明等级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我们可以从秉持19世纪“文明等级论”的人士的反应,来观察这种冲击的规模和力度。在1923年初版的《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Römischer Katholizismus und politische Form)一文中,时年35岁的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这样评论俄国十月革命:“自19世纪以来,欧洲出现了两大反对西欧传统和教育的人群,两大漫溢河岸的川流:进行阶级斗争的大城市无产阶级;与欧洲疏离的俄国群众。从传统西欧文化的观点来看,这两大人群都是野蛮人。当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时,他们就骄傲地自称为野蛮人。”[施米特在此仍然是站在19世纪欧洲主流的文明论立场来看待十月革命,将其视为欧洲边缘民族和无产阶级两股“野蛮人”的合流。在19世纪的文明等级论之下,他们被视为“文明程度”不足、需要被拒绝乃至延迟进入政治场域的力量,是欧洲“教化”的客体。而与之相反的是,1920年3月,不到27岁的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热情洋溢地评论:“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显而易见,毛泽东抛弃了19世纪的主流“文明”尺度,而以战后新的“文明”尺度来看待俄国十月革命以及苏俄。
当然,由于美国战时官方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Public Information Committee)在华的运作,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媒体对其报道和评论的频率,还比不过对威尔逊政府对于战后国际秩序主张的报道。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在中国一度享有极高的威望。许多中国舆论界的精英往往无法分辨威尔逊的主张与列宁的主张有什么实质差别,却对前者寄托了很多的希望。然而,威尔逊为了推动自己的国际联盟计划,在巴黎和会与日本做了交易,同意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导致了中国舆论界对于威尔逊的印象极速转向负面。而列宁则主张废除俄国旧政权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威尔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国共进行了第一次合作,启动国民革命,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广州国民政府的“反帝”主张,推动北洋政府也对列强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直接冲击列强在中国的殖民主义统治秩序。
就内政来看,无论民初的中国政坛多么风云变幻,宪法话语始终在政治正当性话语中具有极强的存在感,大多数具有一定实力的政治势力都试图掌握“法统”,主导国会,控制宪法制定或解释权。这种状况的持续,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中国国内没有任何一派势力具有压倒性的力量,因而还需要通过“法统”话语来凝聚政治盟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以“立宪”获得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承认的思维与行为惯性仍然在持续。而在“一战”之前与“一战”初期,我们在民初的法统政治中,仍然可以看到相当密集的“文明”话语。……这一话语模式也体现在舆论界对于1917年张勋复辟的反应。……在张勋复辟失败之后,陈独秀作《复辟与尊孔》,认为复辟的思想根源在于孔教:“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陈独秀预设君主制是“文明进化”的阻力,而尊孔导致君主制复辟,因而也成了“文明进化”的阻力。
1916年,梁启超为反袁的护国军打造了一套捍卫共和宪法的论述;而到了1917年,当梁启超与段祺瑞站在一起,拒绝恢复《临时约法》时,孙中山却借鉴了梁启超在1916年的宪法论述,打出了“护法”的旗号;甚至到了1922年,当直系军阀试图打掉孙中山“护法”旗帜的正当性,推动南北统一时,使用的还是法统政治的手段:直接宣布恢复《临时约法》法统,实现“法统重光”,试图让南方的“护法运动”无法可护。1923年,孙中山断然放弃了“护法”旗帜,转向国共合作,发动新的革命。而这场革命不再像辛亥革命那样,承认列强在华的特权,致力于通过自身“文明等级”的提升,让列强承认我们为平等的国际法主体;相反,它将矛头对准了列强主导的秩序本身,主张立即废除列强在华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种种特权。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列强“大国协调”的国际秩序,在“一战”期间已经分裂了,在战后也未能获得有效重建,通过“立宪”来获取列强承认为“文明国”的思路,当时已经找不到一个能够全面控局的承认方。而与孙中山建立合作关系的苏联,恰恰是被战后的凡尔赛体系排斥的力量,致力于改造而非融入既有的国际体系。……瞿秋白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在侵略殖民地的时候,往往会扶植当地的封建势力。因而,对于中国而言,只有同时推进“反帝”与“反封建”,才能摆脱原有的被剥削与压迫的状态。因此,需要推进的正是“世界革命”,而非“立宪”。
“一战”之前,“立宪”的形式本身就具有“文明等级论”的意义;在战后,“立宪”形式本身的重要性显著下降了,而宪法文本所规定的实质内容的重要性却在上升。
“一战”之后,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中国都出现了一个制宪热潮。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的重要代表人物张君劢翻译介绍了德国《魏玛宪法》,将其定位为“20世纪之宪法”,并与所谓的“19世纪之宪法”相对比,在当时中国的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之宪法”被视为具有社会主义色彩,关注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而“19世纪之宪法”的自由主义外表下掩盖的是对有产者的保护。正如汪晖指出的那样,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所谓“19世纪”是在“20世纪”的话语出现之后,才获得追溯性命名的,这一点在当时的宪法论述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论者先产生了“20世纪之宪法”的观念,然后才有了对“19世纪之宪法”的追谥。在战后中国的舆论界,一些论者甚至将两个世纪的划分用于对民初《天坛宪法草案》的反思,认为其体现的仍然是“19世纪之宪法”的概念,重在保护有产者而非劳动者。
然而,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制宪热潮,其领导与推动力量要么是北洋集团及其合作者,要么是介于北洋集团与广州政府之间的“联省自治”力量,虽然“20世纪之宪法”提出了如何保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与农民的权利问题,但北洋集团与非北洋的地方实力派真正依靠的力量仍然是军队、地方士绅与列强。……而国共两党在1923年启动的合作,决定性地将宪法问题的重点,从“宪定权”转向了“制宪权”,亦即,必须先解决哪些力量属于“国民”或“人民”这个制宪权主体的问题,才能进一步规定宪法的形式。
于是,“20世纪之宪法”的话语如同“渡河之舟”,国共两党继续前行,形成了自身的宪法话语传统。……而对共产党人而言,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之前的社会形态都是过渡性的,所有宪法都需要根据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与时俱进。20世纪30年代在中央苏区的制宪,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苏联的理论,尚未产生系统的本土宪法理论。……
“20世纪之宪法”的名称貌似从后续的历史进程中消失了。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而言,“一战”结束之后的“觉醒年代”,正是他们思想的形塑期,当时舆论界关于宪法与时代精神的讨论,对于他们思想的成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因而,重新认识“20世纪之宪法”观念的兴起和后续命运,对于理解“一战”之后革命与立宪的历史进程,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