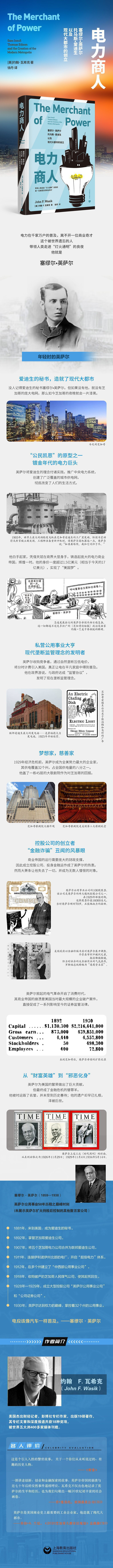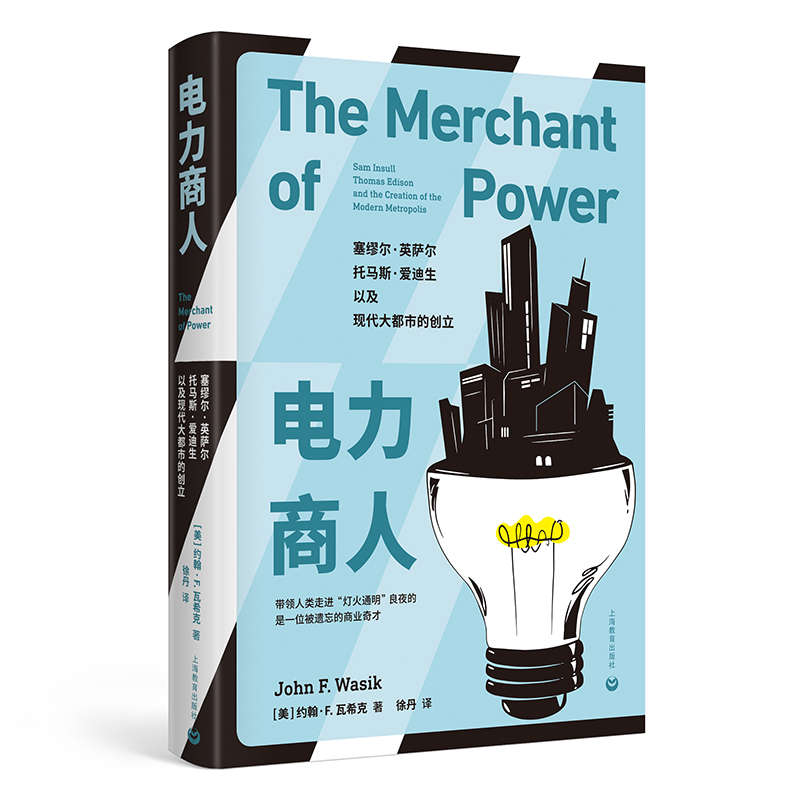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教育
原售价: 65.00
折扣价: 42.90
折扣购买: 电力商人:塞缪尔·英萨尔、托马斯·爱迪生,以及现代大都市的创立
ISBN: 9787572009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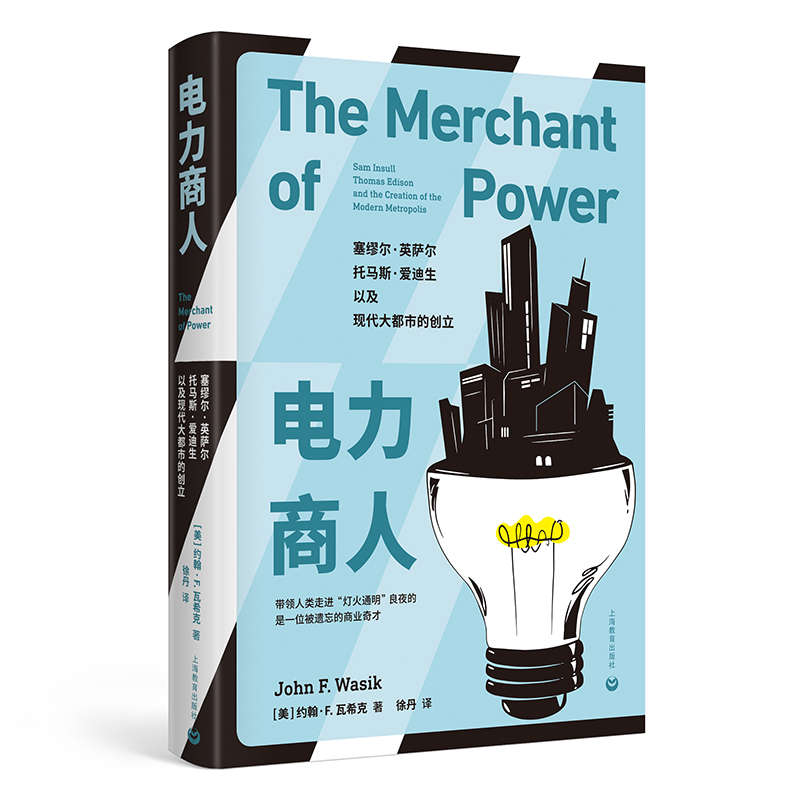
约翰?F. 瓦希克(John F. Wasik),美国杰出财经记者,彭博社专栏作家,出版19部著作,其专栏文章和深度报道共获18种奖项,被世界五大洲400多家媒体刊载。 译者徐丹,上海海事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现为自由译者。
把被告放在证人席上通常会让辩护律师战战兢兢。被告可能会情绪崩溃,忘记细节,变得好辩,消磨掉陪审团的同情心。不过,唯一能够恰当地为塞缪尔?英萨尔辩护的人正是他本人。75岁的英萨尔弯腰驼背,声音沙哑,走路得拄着拐杖。11月1日,法庭挤得水泄不通,他站在证人席上,看上去“身体近乎垮掉”。他身穿一套熨得很好的蓝色哔叽西装和白色亚麻衬衫,开始发表当时最不正统的证词,格拉迪丝皱着眉在法庭后排聚精会神地听着。英萨尔对着检察官的桌子怒目而视,说道:“很抱歉,他们(其他被告)与本案没有什么关系,就像你们一样。”之后,他开始讲述只有他自己才能讲述的故事。 证人席上,英萨尔看上去就像一只被打败的、蜷缩的斗牛犬,在证词开头的战略陈述中,他用自己已经几乎不存在的伦敦口音漫谈起来。英萨尔更像个吟游诗人,完全不像个人民公敌,他将法庭上的人们带回他早年还是伦敦穷小子的那段时光。绝佳的记忆力使他回想起自己卑微的出身,那时他生活在城市的贫困地区,14岁就参加了工作。他愉快地详述了他那一代伟大的美国传奇。他在伦敦每周只挣几个先令,还会在晚上学习优秀文学和速记。他不断跳槽,一步一步走向托马斯?爱迪生代理人的办公室。他骄傲地透过夹鼻眼镜直视着陪审团,直接对他们说:“我恰好有这个荣幸去操作第一台美国境外的电话总机长达一个半小时。” 然后,他被派往美国与伟大的爱迪生会面,处理这位发明家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从回复他的信件到熨烫他的衣服。当提到爱迪生的第一任妻子——那位曾像母亲和朋友一样关心他的女人,他的眼圈就红了,海象胡子也垂了下来。他又瞥了一眼陪审团,用一些爱迪生轶事(后来成为一家芝加哥报纸上的一系列插图)迷住了他们:“有一次爱迪生推荐我加入一个工程学会,但是申请表格上有一栏写着‘申请人在何地接受教育’,爱迪生先生在那一栏填了‘在经验大学’。请原谅我这么说,我来美国是因为爱迪生迷住了我,只要他活着,我就会一直对他着迷。” 现在,陪审团则对英萨尔着了迷。无论控方宣称英萨尔做了什么,都很难将他们亲眼所见的最真实的美国发迹史的光环抹去。英萨尔擦去眼里的泪水,继续讲述他是如何帮助爱迪生筹集资金、创办通用电气并满腔热情地接受他导师的劝告:“让它运转起来,萨米。” 看到英萨尔对陪审团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索尔特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表示反对。“这一切都很有趣,但我们应该了解这与公司证券的欺诈销售有什么关系。” 汤普森笑了笑,让英萨尔继续慢慢讲述他自己在芝加哥爱迪生公司最初的那些日子。英萨尔花了好几分钟描述他如何来到芝加哥领导一家微不足道的、资本不足的公司,年薪只有羞辱性的12000美元。索尔特再次站起来表示反对:“这一切与本案有什么关系吗?”汤普森立马阐述了理由:“也许控方律师并不清楚它的目的,但我所知道的对一个人晚年行为最有说服力的检验标准,就是他在构建自己的生活和经历的那段时期表现出来的性格,如果不让陪审团对他的早年行为有一定的了解,英萨尔先生甚至都无法描述他的晚年行为。” 英萨尔解释了他如何为芝加哥爱迪生公司融资——他从马歇尔?菲尔德那里获得了25万美元的贷款,以及他如何通过出售股票来避免一场早期金融灾难。他开始自命不凡,猛地抬起头来并解释说,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他都对证券估价有着坚定的想法。记者区附近的一名听众俏皮地说:“这位老人正推销自己。我敢打赌他现在就能卖出公司证券的股票。” 证词采集到现在,英萨尔不再是一个破了产的过气人物,他带观众回到了1928 年,那时他还是个公用事业大帝。证词不断深入,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他用右手食指强调要点,并威严地向陪审团发表讲话。他的发音干净利落,解释自己的公司如何将财富扩大到整个密西西比河谷及其他地区时,他的叙述变得越来越详细。他恢复自己的傲慢态度,讲述了自己对小型公用事业公司的多次收购:“他们说我是在合并成堆的垃圾。”他缓和了语气,悲伤地看着陪审团,告诉他们自己如何在拯救公司的过程中失去了一切,以及他本可以在1926年应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的请求,在芝加哥套现并成为英国电力委员会负责人。令人意外的是,他主动承认了自己的一个过失,那就是在1929年的金融危机之前没有向东部的银行示好:“如果我对纽约或费城有一点兴趣,那么我想在1932年的春天,也就是我急需资金的时候,这里的情况可能会大不相同。” 他是“公民凯恩”的原型之一,是镀金年代的电力巨头,是私营公用事业大亨,是现代垄断监管理念的发明者,也是美国第一起“金融欺诈”案的风暴眼。他早年被誉为“梦想家”“慈善家”,晚年被斥为“暴君”“恶棍”。他属于那个时代,又超越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