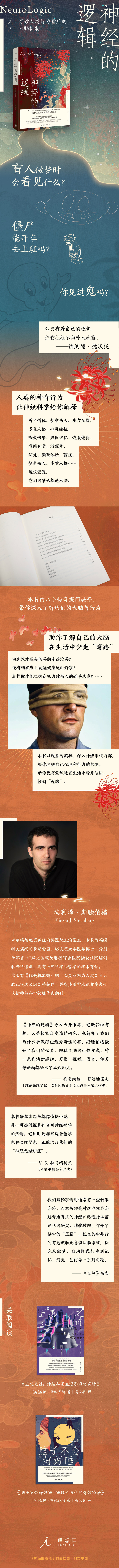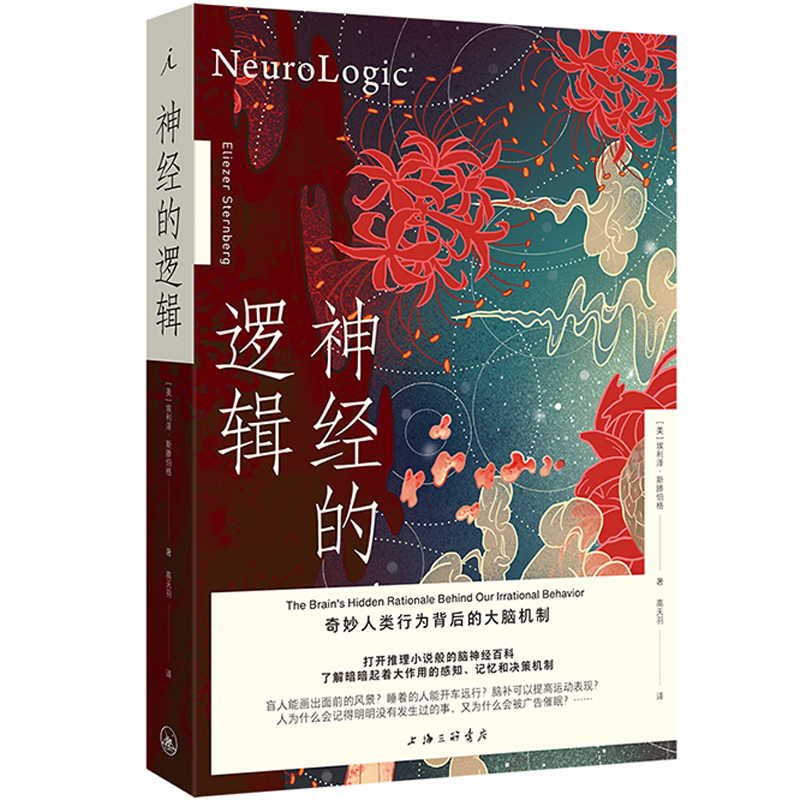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6.00
折扣购买: 神经的逻辑:奇妙人类行为背后的大脑机制
ISBN: 97875426820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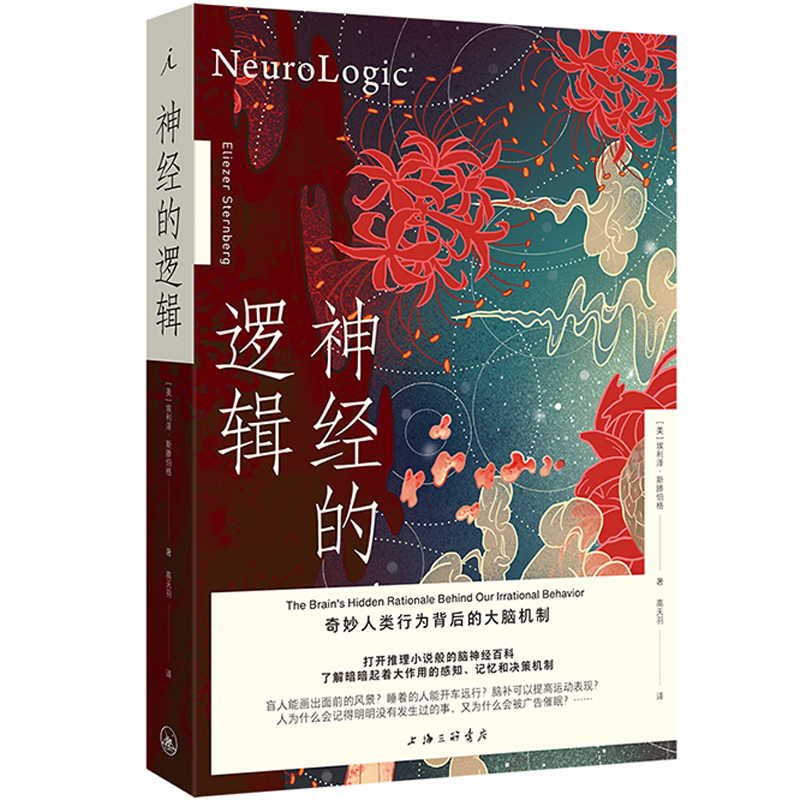
埃利泽·斯滕伯格(Eliezer J. Sternberg),米尔福德地区神经内科医院主治医生,专长为癫痫相关疾病的长期管理。塔夫茨大学医学博士,分别于耶鲁-纽黑文医院及麻省综合医院接受住院培训和专科培训。具有神经科学和哲学的学术背景。出版有《你是机器吗:脑、心灵及何为人类》《大脑让我这么做》等著作,并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于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优秀期刊。
肯尼斯· 帕克斯(Kenneth Parks)23岁,住在加拿大多伦多,从事电子产品生意,工作稳定,结婚已近两年,有一个五个月大的可爱女儿。他和岳父母的关系也十分融洽,甚至觉得比自己的父母更亲近。他的岳母还亲热地叫他“体贴的靠山”。 1987 年春天,帕克斯却为人生中的一个糟糕决定付出了沉重代价。他沉迷赌博,常去赌马,并且花大价钱押冷门,胜率最低但潜在回报最高的赛马。几轮下注失败以后,他开始挪用公司的资金来向妻子隐瞒损失。每天上班他都心惊胆战,因为他还要掩盖自己从公司偷钱的证据。可纸包不住火,他终于行径败露,被公司开除,还遭到起诉。于是他越来越难向妻子坦白自己赌博的事,尤其是当两人不得不把房子挂牌出售的时候。 债务压力常使帕克斯彻夜难眠,就算好容易睡着也往往在半夜惊醒,胸中填满焦虑。在参加完一次“匿名戒赌会”后,帕克斯决定向家人包括岳父母坦白自己的财务困境。在召开家庭会议的前夕,他一刻都没有睡着 ;翌日早晨,筋疲力尽的他告诉妻子会议推迟一天。那是5月23日星期六,凌晨1点30分,帕克斯终于在长沙发上沉沉睡去。 帕克斯接下来的记忆,是看着满面惊恐的岳母在自己面前倒下。他接着象自己的车跑去,当他伸手去够方向盘时,才发现手上握着一把刀,刀上正在滴血。他把刀扔到轿车地板上,然后径直开到了警察局,告诉警察:“我好像杀人了。” 在多轮独立讯问之后,帕克斯的故事终于现出了全貌。从自己睡着到看见岳母的面孔,中间的事情他都不记得了。但是调查人员发现,在帕克斯失去记忆的那段时间里,他做成了不少事情。他先从长沙发上起身,穿上鞋和外套,然后走出家门,驱车23公里,中间在三个红灯前面停下,继而走进岳父母家中,先和岳父打斗并掐了岳父的脖子,接着又将岳母刺死。然而对于这一切,他完全没有印象。 医学评估没有发现身体疾病或药物滥用的迹象,其后,四位精神科医生也一起参与进来,以期推进案情进展。在他们看来,帕克斯显然被发生的一切给吓坏了,而且他也没有预谋杀人的迹象。他没有明确的作案动机,因为杀死岳父母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他也没有控制攻击性方面的困难。他智力达到平均水平,没有妄想、幻觉或任何精神疾病。因为精神医学检查一无所获,四位评估人感到十分吃惊,也说不出所以然。 后来在一位神经科医生的帮助下,他们意识到帕克斯的情况可能和睡眠障碍有关。他历来睡得很浅,有时还会梦游,他家族的许多人都有这毛病。他的梦游经历始于童年。有一次,几个兄弟甚至看见他在熟睡中爬出了一扇窗户,他们合力才把他拉回床上。他还有过尿床、夜惊和说梦话的问题,而这些都与梦游相关。那位神经病学家建议用“多导睡眠图”给他做一次全面睡眠评估,这种设备能够同时测量睡眠者的脑波、眼动、心率、呼吸频率和肌肉运动。结果显示,帕克斯的慢波睡眠显著多于常人,而这正是长期梦游者的典型特征。当所有证据汇总完毕、呈上法庭,法官裁决帕克斯袭击岳父、杀死岳母时处于梦游状态,他的两项罪名均不成立。正如一位法官的判词所言: 虽然“自动行为”一词在不久前才首次进入法律界,但嫌疑人在行动时并非自愿,却向来是辩护的理由,这是一条基本原则。只要能证明嫌疑人的行为并非自愿,就足以无条件宣告他完全无罪……在普通法中,某案件参与者只要在案发时处于意识丧失或者意识不全状态,他就没有罪责。同样,如果他因为精神疾病或者缺乏理智,无法辨别一项行为的本质和特性,也无法判断从事该行为的错误,则他同样无须担责。我们的刑法有一条基本准则,那就是,一个人只能对自己有意识、有意图的行为负责。 …… 第八章 为什么分裂的人格不能戴同一副眼镜?论人格、创伤和对自我的保护 伊夫琳住进精神科病房的时候状况很差。这位35岁的单身母亲属于法定失明,要靠导盲犬帮助才能外出。她的失明原因不详,病历上的旧诊断说她“双侧视神经受损,导致先天眼盲”,但这个说法没有证据。病历中没有记载她接受过什么检查,她也说不出有哪项检查确定了她失明的原因。不过,将伊夫琳引入精神病房的并不是她的眼睛,而是她的皮肤。 她的前臂上深深刻着“肥猪”和“我恨你”这几个词。她不知道这些字是怎么刻上去的,也说不清皮肤上为什么有旧的烧灼痕迹。查看医院记录,我们发现伊夫琳一年前就来就诊过,当时她皮肤上刻的是“笨蛋”和“疯子”。她宣称自己没有自残,也想不出有谁会做这事——和她一起生活的只有年幼的儿子而已。 为什么伊夫琳无法指认残害她的人?也许这和她自己描述的记忆反常有关:当伊夫琳第一次在皮肤上发现刻痕时,她记不起之前的几个小时发生过什么了。从小到大,她常常经历这样的“断档”或“时间丢失”,她的记忆常会漏掉几个小时。她自己是这样形容的:“自打记事起,我就常常发现自己会漏掉一段一段的时间,小时候觉得这很可怕,长大了又觉得很神秘,我不敢告诉别人,生怕大家会把我锁起来然后丢掉钥匙。” 她始终不明白那些缺失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但是偶尔也会找到一些线索:“等到回过神来,我会发现一些玩具,就像是我儿子上学前玩的那些。我还会发现购物袋里装满了好几样东西,都是我平时不会买的。” 伊夫琳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她的童年。她成长在一个可怕的环境中,尚在襁褓时就被人从生母身边带走,因为母亲对她施行身体虐待和性虐待。儿童保护机构发现她被母亲锁在衣柜里,于是立即把她送进了寄养机构。她两岁那年给人收养,等长到10岁,养父母也离了婚。养父和生母一样,也对她施行身体虐待和性虐待。家里还有一个比她大9岁的哥哥,常常把她捆绑起来,要勒死她。一家人都责备伊夫琳,说养父母离婚都怪她,因为她的视力缺陷太难处理,拖累了全家。 8岁那年,伊夫琳在医生的安排下转入一所盲校就读。医生说她之所以失明,大概是因为眼球结构有点问题,而在这之前,她都一直以为视力缺陷和在学校的艰难全是她自己的错。她在养父母离婚后即刻转入新学校,之后不久就经历了第一次“时间丢失”。有一天晚些时候,她在自己的手臂和腿上发现了淤青和小块擦伤,但不知道这些伤是怎么来的。她说不出自己遭遇了什么,也不清楚从失忆起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 伊夫琳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在她手臂上刻下了文字?是不是她曾经遭到侵犯,只是后来忘记了?又或者是她自己在伤害自己?医生很快就发现,这两个猜想都有一点道理。 经诊断,伊夫琳患有“解离性身份障碍”,这种精神疾病一度称为“多重人格障碍”,症状是她有着几个不同的人格。其中一个是成年女性“法兰妮· F”,她有一个小宝宝名叫辛西娅。另一个是“长相怕人”的10岁女孩莎拉,她长着“打绺的红发”、棕色的眼珠还有雀斑。最后一个是“貌如天使”的4岁女孩吉米,有着蓝色的眼珠和金色短发。她的仪态会随着人格而变化。作为伊夫琳的她智慧、成熟,口齿伶俐。变成吉米后,她的声音一下子变得稚气,连普通的字词都会说错,比如把紫色上衣说成“纸色”。她说总统是“我爸爸”;还会激动地向人宣布,“橙”原来可以既指一种颜色也指一种水果,好像她才发现似的 ;她还说她哥哥正在教她写自己的名字。下面是吉米和精神科医生的一段对话: 医生:你几岁啦? 吉米:我4睡了。 医生:你4岁啦?哎呀,是个大姑娘了呢!你在干什么呀,吉米? 吉米:嗯,我在乖乖地坐着,我要做个乖孩子。 医生:哦,孩子就要乖乖的是吧? 吉米:是。 医生:孩子为什么要乖呀? 吉米:因为不乖就会挨打。 医生:哎呀,真糟。是谁打你呀? 吉米:我的妈妈爸爸。 说到挨打,吉米紧紧闭上眼睛,手也牢牢抓住了泰迪熊玩具。后来话题变得阳光了一些: 医生:你喜欢玩什么游戏呀? 吉米:我喜欢玩转呀转呀都倒啦、伦敦大桥要塌啦、拿起钥匙锁住门、鹅妈妈……我还喜欢和熊玩。 医生:是真的熊吗? 吉米:不是真的,但都是我的朋友。 当伊夫琳在不同的自我间切换时,变化的不只是她的人格而已。例如吉米用右手握铅笔写字,而伊夫琳却是左撇子。最惊人的结果出现在精神科医生给这些人格做视力检查的时候。以标准视力表衡量,伊夫琳的视力是0.1,属于法定失明。法兰妮·F和辛西娅的视力也是 0.1。不过莎拉的视力却有0.25,吉米更是超过了0.3。0.3和0.1,一个只需要戴一副度数较浅的眼镜,一个却是法定失明。伊夫琳需要牵导盲犬,而她的另一个自我却只需要一副眼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是不同的人格,用的也是同一双眼睛啊。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首先,一个人怎么会拥有几个人格呢?它们仅仅是情绪的极端波动,还是真的是相互分隔、独立运作的身份?如果是后者,如果这些不同的自我真的是相互分离又各有意识的个体,那就会引出一个最明显的问题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伊夫琳?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自我”感。我们不仅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秉性,还觉得自己存在于头脑中的某个地方,正从那里观望着外面的世界。我们似乎有着一种内在本质,它在痛苦时麻木,在兴奋时战栗。这个内在的身份不仅是一个消极的感受者,也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我们无论是反省自己的想法、斟酌自己的抉择还是发起行动,似乎都是出自某个内在的中央指挥者。我们的头脑里有一样东西,它是“我”这个字的指称对象,在时间过程中表现得单一、统合且一致。然而伊夫琳的例子却表明,这个自我可以是分裂的。它可以打散拆开,分解成一个个零碎的人格,各自独立地成长发育。 透过本书,我们已经见识了脑中的意识系统和无意识系统如何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而人的自我就在这两个处理单元之间的某处涌现出来,这就将许多人引向了那个费解的问题 :我究竟在我脑子里的什么地方?在研究多重自我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从一个自我开始研究吧。所谓的“自我”(self) 和“身份”(identity),这些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自我这种现象是在脑中的哪个部分产生的?这也许是神经科学最大的谜题,要找到它的答案可不容易,但我们还是要尽量找找看。其实我们从本书的第一页起就在不知不觉地做这件事了。那我们现在又该从哪里着手呢?按神经病学的惯例,研究脑中的任何系统,第一步都是观察它出故障后的情况。 人类神奇行为一览 听声辨位、梦中杀人、左右互搏、多重人格、心灵操控……这些小说般的情节都真实存在!本书展现了很多超乎想象的人类行为。每章都从一个惊奇问题开始,带领读者不断解谜,充满阅读推理作品的快感。 神经科学一本通 覆盖神经科学的各领域和多种方法,习惯、记忆、梦境、疏忽、幻觉等等日常心理现象都得到了解释,在快乐阅读中了解人脑和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 帮你在生活中少走“弯路” 经常回到家才想起路上该买的东西没买?是否知道要减肥的话不能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电视?怎么抵御商家在不知不觉中为你植入剁手诱惑?还有躺在床上就能健身这种好事?……理解这些心理和行为的机制,更有意识地在生活中躲开陷阱,抄到“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