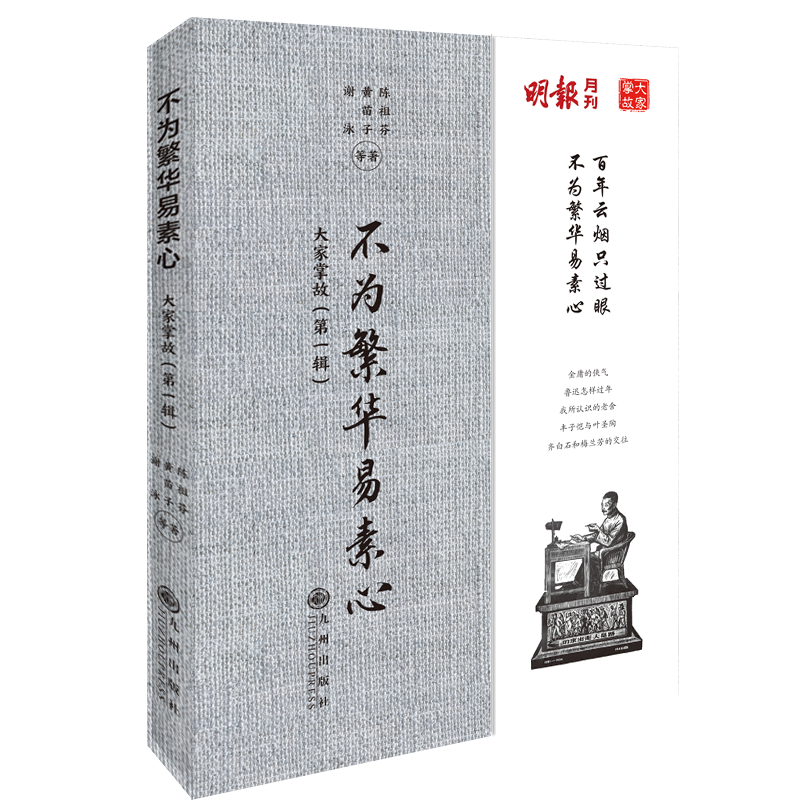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大家掌故 第一缉 不为繁华易素心
ISBN: 9787510893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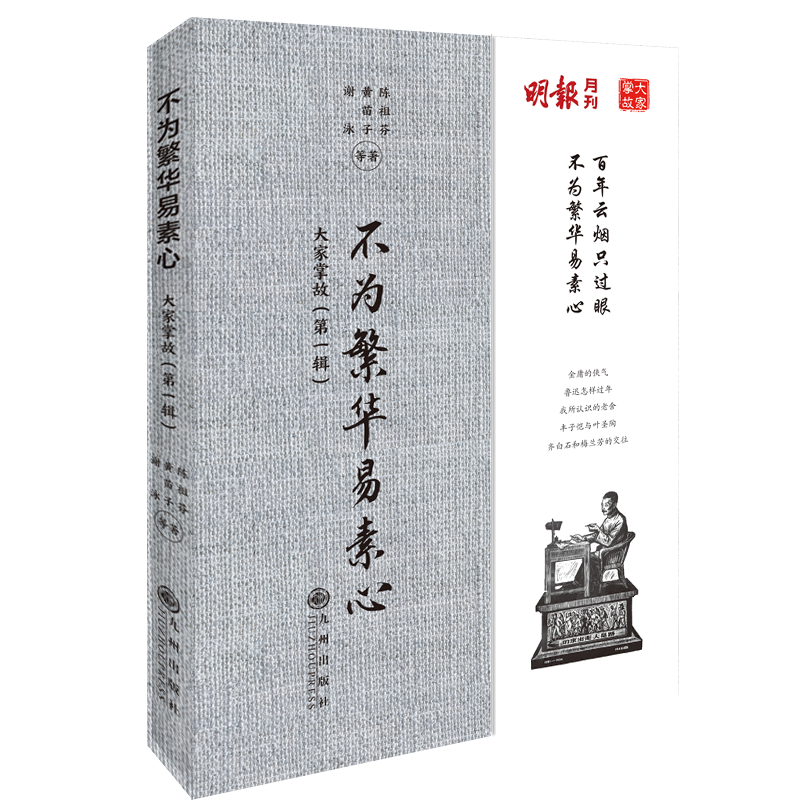
司马新:旅居美国多年,系哈佛大学文学博士。曾就学术问题等与张爱玲晚年有书信往来。 陈祖芬:陈祖芬,女,1943出生,上海人,作家。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现为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北京作协副zuxi,北京文联副zuxi,全国政协委员,曾连续五次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及其他文学奖几十次,已出版个人作品集二十多种。其丈夫是著名学者刘梦溪。弟弟为著名围棋大师陈祖德。 池田大作:池田大作(1928年1月2日-),日本东京人,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创价大学创办人,是一位著名宗教家、作家、摄影师。曾任日本创价学会会长(1960年—1979年)。池田与创价学会致力于推动文化、教育、和平,1983年获联合国和平奖,1989年获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的人道主义奖,1999年获爱因斯坦和平奖。在中国获得的奖项有:中国艺术贡献奖(1959),中日友好“和平使者”称号(1990),“人民友好使者”称号(1992),中国文化交流贡献奖(1997)。 其他作者的作者简介不一一列出,共汇集二十多位海内外知名的作者。
一个人名噪一时并不稀奇,但一生饮誉却难得一见,梅兰芳是这样为数有限的人之一。他经历北洋军阀统治、guomin党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北京杨梅竹斜街或鲜鱼口照相馆的橱窗陈列,如走马灯似的,一会儿袁世 凯,一会儿黎元洪,一会儿又是冯国璋;冯“大总统”的肖像换上徐世昌、段祺瑞,未久,又让曹锟、吴佩孚、 张作霖、冯玉祥所顶替,然后是蒋中正……可是梅兰芳的玉照却“我自岿然不动”。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和几位蓄须明志的梅兰芳同事自重庆转往上海。在大后方住了多年,一旦旧地重游,恍如隔世,对那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生活,看不习惯。昔日的租界虽说收回了,满街却是趾高气扬的美国兵。刚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的上海市民,瞪眼望着那群飞扬跋扈的花旗“烂水手”,憋着一肚子气。请看今日城中是谁家天下?那时从天上飞来的和从地下钻出来的“五子登科”之徒,竟把上海看作殖民地,沦陷区的人都被戴上了“伪”字号的帽子,不但汉奸是正牌的伪官、奸商,连普通老百姓也成了“伪百姓”,一切都乱了套。难怪洪深教授一回到上海就叹气:“除了电车还在轨道上跑,一切都出了轨!” 我们几个从大后方来的记者,有时在咖啡馆小坐,闲谈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忽然有人提出:“去访问梅兰芳,怎么样?这是位新闻人物呀!”这个建议立刻获得大家的同意。“双十节”将近,上海充满了节日气氛。市政府筹备这天清晨在跑马厅(人民公园)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会后是盛大的游行,晚间在兰心戏院演出精彩的文艺晚会,大轴戏是梅兰芳的《费贞娥刺虎》。由于他在敌占区坚贞不屈,蓄须明志,拒绝粉墨登场,人们对他的表演艺术望眼欲穿。他息影多年,为了准备演出,免不了忙于重新组班,自己也要勤吊嗓子、练身段。 我忖思,这个日子口约他访问不太可能。我向父亲提起这事,父亲说:“我打个电话试试。” 谁也没料到,梅兰芳一口答应下来,日期就是十月十日。 父亲提醒他:“你这天有戏,够忙乱的,还是改日吧?” 梅先生答:“就这天合适。人家都知道我晚上有戏,白天不会来找我的。” 就这样,我们在胜利后的第一个辛亥革命纪念日,作为大后方的第一批记者,采访了这位举世闻名的艺术大师。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会见梅兰芳。他的名字,我最初知道还是儿时从父亲口中听到的。梅先生是男旦,当时演员都有艺名。我小时候以为“梅兰芳”如同“白牡丹”一样,也是艺名,突然问我父亲:“梅兰芳的真姓是什么?” 父亲大笑道:“傻孩子,梅兰芳不是明明姓梅?”我好纳闷,这样一个女性的芳名! 民国初年,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幼伟)、吴震修、李释戡、许伯明等先生和我父亲以及一些文苑名流,热爱梅兰芳的戏曲,钦佩梅兰芳的人品,与之结为忘年交。这几位老先生被时人视为“梅党”,被梅先生的表演艺术所倾倒。无量大人胡同“缀玉轩”中,时常能见到他们的踪迹。老人们在一起,或击节歌唱,或研讨剧情,或推敲音韵,或撰写唱词,或讲究服装、身段、扮相等,酒酣耳热之际,豪兴大发,放论古今,不久,一个剧本就产生了。 梅兰芳能在他周围有这样一个强大阵容的“参谋团”,对今天任何一个名角儿说来,是不可能的事。 我第一次接触梅先生,是在北伐战争时的上海。那时我还是一个弱冠的学生,随长辈去串亲戚。亲戚家正主办《诗钟》,梅先生也来了。我不能厕身父执辈中,对梅先生也只是隔窗窥视,可称“望梅止渴”。 来到思南路梅宅,阶前木叶殷红斑斓,一只主人豢养的猢狲在草坪上自由自在地玩耍。客厅内这时却静悄悄的,如同大战前夕的宁静,完全出乎我们意料。这位新闻人物家中,既没有如云的宾客,也没有丝竹管弦之声,更无形形色色的人事纠缠他,连电话铃也未响过一次。如果不是姚玉芙开门肃客时告知:“梅大爷正在候驾呢!”我们还以为走错了人家。 这座小楼连同草坪虽占地不广,却异常玲珑舒适。据他后来自己说,房子的业主是新华银行,仗着冯幼伟的说情,才暂缓追索积欠的租金。梅先生在沦陷时期的生活窘境可想而知。我正端详壁上悬挂他学画的老师汤涤(定之)先生的巨幅墨梅,主人已经含笑安详地走入客厅。那次谈话,我曾写过访问记,作为专栏文章刊于《立报》第一版,可能是(抗日)胜利后第一篇关于梅兰芳的报道吧。 梅兰芳是一位可敬的爱国者。对他的蓄须明志,自己认为“这不过是国民的天职”。在香港,在上海,他都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下,言论行动不能自由。他手中无qiang,无以驰骋疆场杀敌。他手中没有马班之笔,无从对敌伪口诛笔伐。他竭力所能办到的是拒绝粉墨登场,不为所谓“王道乐土”粉饰太平。并不像什么人说的,凡天才都是天生的革命家。 梅兰芳自不例外。在他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之前,他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未必了解。他与左翼文化人有接触,也访问过苏联,但他对国家和爱国的概念,并非一开始就明确的。当我告诉他,大后方的人们很想念他时,他脱口而出:“我准备收拾收拾,把家安顿好之后,就上重庆向蒋委员长致敬!” 在当时,举国一片胜利的欢腾,“元首”就是国家的象征。当人们还未彻底认清jiangjiesi的面目之时,梅兰芳有那样的说法又何足怪?事实教育了梅兰芳,他后来并未去重庆向jiangjiesi致敬,也没有去南京给蒋祝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既未出走香港,更未逃亡taiwan。梅兰芳深明大义,待人温柔敦厚,即使在他经济困窘时,也照常供养他的旧班底、老伙计、厨师、司机、仆役,直至梅先生本人辞世。他毕生不忘提掖他从艺的恩师与挚交冯幼伟、追随他多年的策士李释戡和秘书许姬传。 梅兰芳是京剧改良运动的先行者。从来历史上伟大的艺术家都是革新运动的首创人。蹈袭前人,只能是跟着人家屁股后头跑。墨守成规,口口声声以不逾越祖师爷的规范而扬扬自得的演员,只能是抱残守缺,一代不如一代。从《天女散花》《邓霞姑》到《生死恨》《战金山》以及晚年的绝响《穆桂英挂帅》都验证了他不断追求进步的足印。 梅兰芳不但在表演艺术方面足以雄视梨园,他的戏德,他的为人谦恭,也值得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一次戏剧节大会演中,他和周信芳先生合演《打渔杀家》。这出戏生旦并重,而以萧恩略占上风,本来以梅先生的声望论,可以不轻易给人配桂英,然而他毅然接受周的提议,排出这个戏码子,破例为周挎刀,用周的琴师,出场时也让周先cutai亮相,而自己闪在一边。这样,并无损于梅兰芳的声誉。相反的,愈使人佩服梅先生谦让的戏德高人一等。 有一天,梅先生在我家便宴,座中大都是前辈老先生。梅先生在老辈面前,执礼甚恭,决不夸夸其谈,而是有问方答。老先生们坐在沙发上谈天说地,梅先生一句也不打岔,选了近窗的靠背木椅落座,默默倾听。我和他相隔两把空椅。这时,我问梅先生:“那天您和信芳合作的《打渔杀家》真不赖。我相信你们一南一北从没配过这出戏吧?” 梅先生正在注视老先生谈笑,不料我陡地有此一问,很快挪过两个位子,靠近我侧耳倾听。我顿时意识到我的失礼。我和他讲话,按礼节应该走过去挨近他,怎么反让他“移樽就教”呢?我感觉不好意思,梅先生却泰然自若,低声答话,生怕干扰老人们的谈兴。 “可不是。我还头一回跟周先生配这出戏呢。”梅兰芳以愉快的心情回答我。 “可演得严丝合缝,一点儿瞧不出来。听得出,您是有意压低调门来配合信芳的。” “哪儿的话!是该我凑合周先生。可惜时间太短,才对了一回调儿就上场啦。我是尽量依周先生的戏路子,可惜没配好,真不过意。” 想到今天有的京剧演员刚刚有点名气,功夫还没到家,就争头牌、抢大轴,为争名次而吵红了脖子,成冤家对头的,大有人在。 一九八六年我游香山,偶经万华山麓,拜谒了梅兰芳长眠之地。翠柏夹通,一座花岗石梅花雕刻的石板墓穴中,安息着一代宗匠。墓碑上只有“梅兰芳之墓”五字,没镌刻任何头衔,也没有雕栏玉砌的华表玄堂,素朴庄重。其实,任何赞美的头衔和辉煌的建筑也难以概括和显示他一生的伟大业绩。 梅兰芳在千万人的心中,永远留下美好记忆的丰碑! 大师风范?真实回忆?隐秘往事 明报月刊五十年精华选集金?庸大师一手创办?二十余位海纳外学者心血之作?揭示中国近现代百年中国文人精神细节权威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