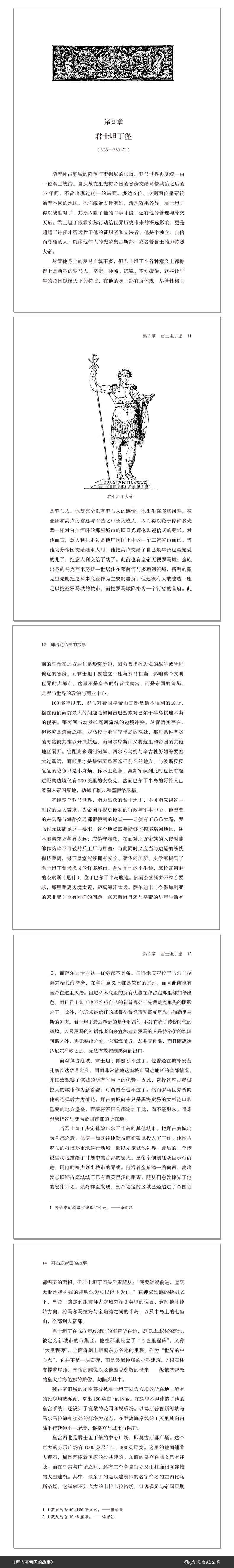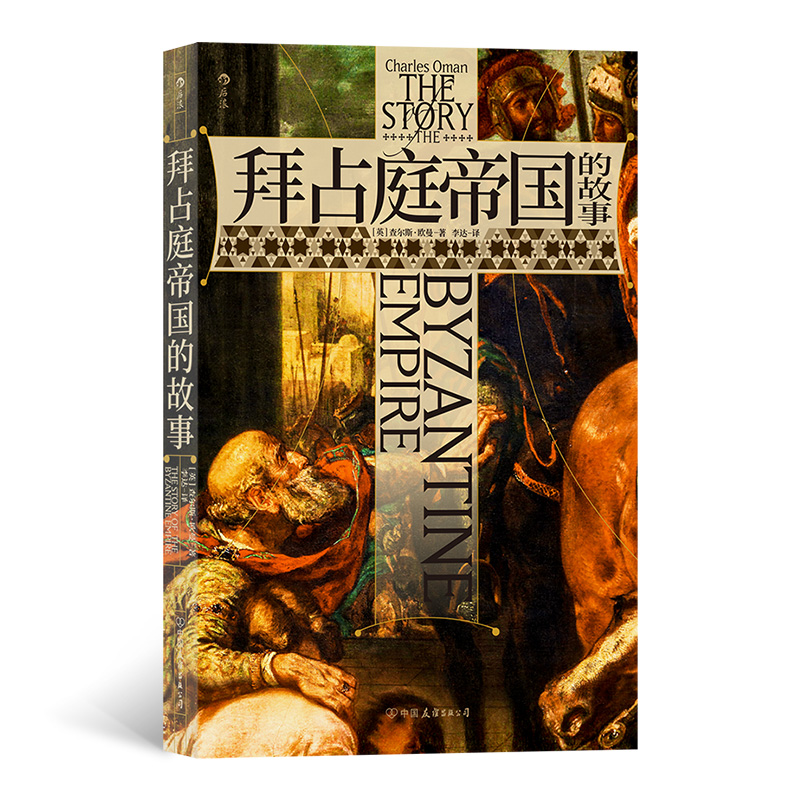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友谊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26.90
折扣购买: 拜占庭帝国的故事
ISBN: 9787505755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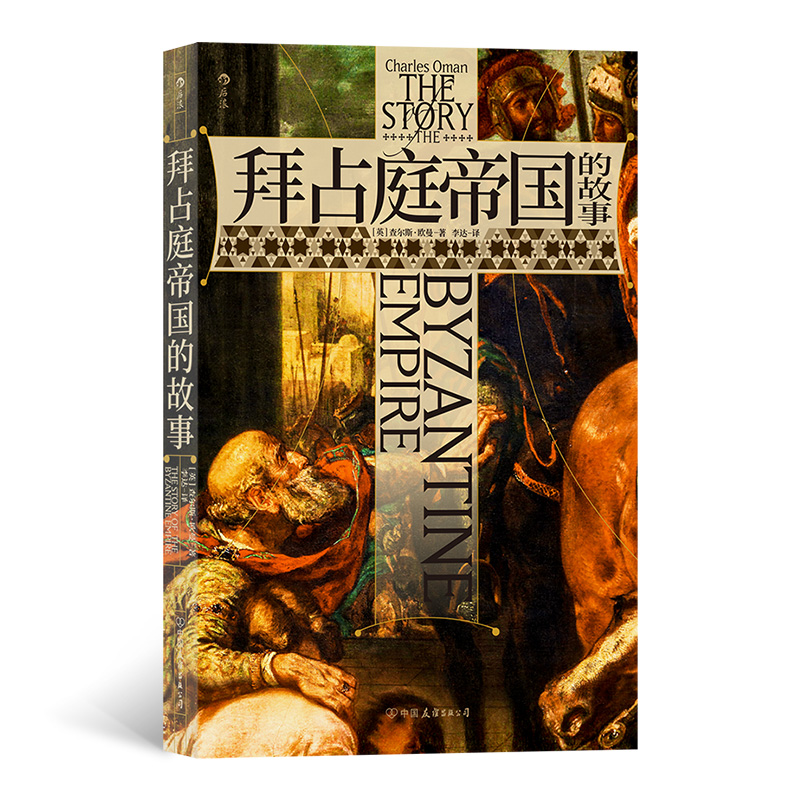
著者简介 查尔斯·欧曼(Charles Oman,1860—1946),英国历史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他专注于中世纪史研究,尤其专注于军事史。著有《中世纪战争艺术》《半岛战争史》《黑暗时代》等书。 译者简介 李达,浙江大学毕业,中世纪军事历史爱好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世纪军事史、拜占庭帝国制度史、中世纪东地中海-黑海交流史等。曾自译数本军事典籍与编年史。 内容简介 这是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欧曼创作的一本普及性历史书籍。作者用较为简短的篇幅,勾勒了拜占庭帝国千余年的政治史,从拜占庭城建立,讲到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陷落,这千年以来的一桩桩重大历史事件历历在目,向读者讲述了拜占庭帝国兴亡盛衰的历史进程,让人不禁为这一辉煌灿烂文明的衰败哀叹遗憾。 本书语言轻松,线索明晰,记事简明扼要,没有太多学理性内容,能让读者轻松了解拜占庭帝国悠久的历史。本书配有大量版画风格的插图,能让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历史。
第2章 君士坦丁堡 (328—330年) 随着拜占庭城的陷落与李锡尼乌斯的失败,罗马世界再度统一由一位君主统治。自从戴克里先将帝国的省份交给同僚共治之后的37年间,不曾出现过统一的局面。多达六人、少至两人的皇帝们统治着不同的地区,他们统治方针有别,治理效果也各异。君士坦丁得以战胜对手,其原因除了有他的军事才能,还同样有他的管理与外交天赋。君士坦丁依靠实际行动给世界历史带来的深远影响,更是超越了许多才智远胜于他的征服者和立法者。他是个独立、自强而冷酷的人,就像他伟大的先辈奥古斯都,或者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 尽管他身上的罗马血统颇为寡淡,但君士坦丁在各种意义上都称得上典型的罗马人。坚定、冷峻、沉稳、不知疲倦,这些让早年的帝国纵横天下的特质,在他的身上都有所体现。尽管性格上是罗马人,他却完全不认同罗马人的身份。他出生在多瑙河畔,在亚洲和高卢的宫廷与军营之中成长,因而得以全然免于像许多的先辈一样,对台伯河畔的那座城市旧日光辉抱以迷信的尊崇。对他而言,意大利只不过是他广阔国土中的一个二流省份而已。当他划分帝国交给继承人之时,他把高卢交给了自己最年长也最受宠信的儿子,而意大利则交给了幼子。此前也有皇帝无视了罗马城:蛮族出身的马克西米努斯一世居住在莱茵河与多瑙河流域,政治家戴克里先则把尼科米底亚作为主要的居所。但还没有人敢建造一座足以挑战罗马城的城市,而把罗马降格为一个行省的首府。此前的皇帝在远方居住,是因为形势所迫,要安排边境的战争与偏远省份的管理,而君士坦丁则要建立一座与罗马相当、影响整个文明世界的大都市,这里不是皇帝的行营或离宫,而是帝国的首都,是罗马世界的政治与商业中心。 一百多年以来,罗马对帝国皇帝而言都是最不便利的居所,他们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需要击退蛮族对巴尔干半岛接连不断的侵袭;莱茵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边境冲突,尽管确实存在,但终究是疥癣之疾。罗马位于亚平宁半岛的深处,条件恶劣的海港使其难以开展航运;而阿尔卑斯山又将这里和帝国的其他地区隔开,距离多瑙河河岸和西尔米乌姆与辛吉杜努姆等要塞太过遥远,而那里则是最需要皇帝亲征前往的地方。与波斯反反复复的战争只是小麻烦,称不上危急,波斯军队至今也没有突入到距离边境仅有200英里的安条克,然而巴尔干半岛的哥特人已经深入帝国腹地,劫掠了雅典和塞萨洛尼基。 掌控整个罗马世界,承担如此重担的君士坦丁,能力完全足以看出这一时代的重大需求:为帝国寻找更便利的行政与军事中心。他想要的是能够从陆路与海路便利抵达的地点——即使有了条条大路,罗马也无法满足这一要求——这个地点需要能够监控多瑙河地区,还不能离东方各省太远;应有足够的地利,在面对北方蛮族的入侵时能够作为牢不可破的兵工厂与堡垒;与此同时又应当与边境的纷扰保持距离,保证皇室能够生活在安稳与华丽之中。史学家提到了君士坦丁曾考虑过的许多城市。首先是他的出生地,摩拉瓦河畔的奈索斯(尼什),位于巴尔干半岛腹地。然而奈索斯并不符合要求:那里距离边境太近,距离海洋太远。萨尔迪卡(今保加利亚的索菲亚)也有同样的问题。奈索斯尚且还与皇帝的早年生活有关,而萨尔迪卡连这一优势都不具备。马尔马拉海东端的尼科米底亚拥有漫长的海湾,在各种意义上都是较好的选址,而且此前也有皇帝在这里久居。但尼科米底亚的所有优势,拜占庭都加倍出色,而且君士坦丁也不希望自己的新首都处于先辈戴克里先的阴影下。此外,他近来最信任的基督徒们曾经遭受戴克里先与伽勒里乌斯的迫害。君士坦丁最后考虑的伊利昂,除了传说时代的辉煌,以及罗马的神话作者向来宣称是特洛伊的埃涅阿斯建立了罗马之外,再无突出之处。这里离海虽近,却并无良港,而且距离赫勒斯滂海峡太远,无法有效控制黑海的出口。 而对拜占庭城,君士坦丁再熟悉不过了。他曾经在城外安营扎寨长达数月之久,因而必然清楚这座城市周边地区的全部情况,并细致观察了该城的所有军事上的优势。因此,选择这座古墨伽拉人的城市作为新首都,可谓再合适不过了。然而罗马世界在听闻他的选择后依然大为惊诧,拜占庭城向来只是黑海贸易的大型港口和重要的地方堡垒,而要将帝国首都定址于此,尚不能服众。很难想象把这里变为帝国首都的所在地。 当君士坦丁决定排除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城市,把拜占庭城定为首都之后,他便一如既往地勤奋而细致地投入了工作。他采用古罗马的风格,郑重地巡行新城一圈并划定城池边界。此后的一个传说生动地描绘了这一计划的宏大:皇帝率领朝廷众臣步行前进,用他的枪尖划出城市的界线。他沿着金角湾一路向西,离出发点旧拜占庭城城门已有2英里多的距离,随从们也愈发惊异于他计划的宏大。最终群臣发现,皇帝划定的区域已经超过了帝国首都所需求的面积。但君士坦丁回头斥责随从:“我要继续前进,直到无形地指引我的神明认为可以停下为止。”在神秘预感的指引之下,皇帝一路走到距离拜占庭城东端3英里的位置,这时他才调转方向,将马尔马拉海与金角湾之间的半岛,以及半岛上的七座山,全部纳入城中。 君士坦丁在323年攻城时的军营所在地,即旧城城外的高地,被定为新城市的市集区。他在那里树立了金色的里程碑,上面将刻上前往东方各地的距离。作为“世界的中心点”,这一“大里程碑”并不是一块石碑,而是类似神庙的小型建筑,七根石柱支撑着屋顶,皇帝的雕像,以及他颇受尊敬的母亲——皈依基督教的皇太后海伦娜的雕像,均陈列其中。 拜占庭旧城的东南部分被君士坦丁划为宫殿的所在地。所有的民房均被拆毁,空出150英亩的区域,在这里不但建造了他的皇宫系统,还设计了宽敞的花园和娱乐场。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马尔马拉海相接处的灯塔为起点,在距离海岸线约一英里处向内陆平行延伸出一堵墙,将皇宫与城市分隔开。 皇宫的西北方向是君士坦丁堡城的中心广场,所谓的奥古斯都集会所。这个巨大的方形集会所有1000英尺长、300英尺宽。这里的地面铺着大理石,周围环绕着国家的公共建筑。东面的皇宫在前文已有述及。而在皇宫与广场之间,还有三个各自独立又用柱廊相互连接的大型建筑。其中,最东面的是以建筑师的名字命名的左西比乌斯浴池,它纵然不如庞大的卡拉卡拉浴池,但规模足与帝国早期的皇帝们在罗马建造的建筑相媲美。君士坦丁利用拜占庭城旧有的公共浴池,将塞维鲁夺取该城后重建的浴池加以扩大。他在建筑的前方与庭院之中布置了来自希腊与亚洲的各种雕像,都是免于十二任执政官和凯撒掠夺的希腊艺术精品,包括林多斯的雅典娜像、罗得岛的阿芙洛狄忒像、希腊人在击败薛西斯之后阉割的潘神像,以及多多纳的宙斯像。 浴池以北、奥古斯都集会所以东,是另一座宏大建筑:元老院。君士坦丁决定在新城市中安排与古罗马相同的元老院,也利用津贴与房屋的诱惑,劝说了许多古老的元老家族向东搬迁。我们可以确定这座建筑非常宏大,但君士坦丁主持建造的元老院因为在这个世纪两度被毁,其原貌已不可考。但和左西比乌斯浴池一样,这里也放置了古雕像来装饰,史学家提到其中希利康的九缪斯女神像在404年的大火中遭到损毁。 和元老院通过柱廊相连的是拜占庭主教的住所,而拜占庭主教也将在不久之后变为君士坦丁堡牧首,与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的牧首并列。这座雅致的建筑有宽敞的会客大厅和花园,然而牧首的居所却处于身后皇宫的阴影之下。牧首本人也同样如此:他距离君主太近,无法取得任何独立地位。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上,他都受制于皇帝,从来不曾摆脱帝国政府而获取独立地位,也无法和罗马教廷一样建立国中之国。 在奥古斯都广场以西,面对着前述的三座建筑的,是对君士坦丁堡公共生活意义重大的宏大建筑——大竞技场。在这块640腕尺长、160腕尺宽的场地上,上演着古罗马城的居民熟悉的竞技。代表着城中的各党派的战车竞赛,同样在拜占庭城中进行,而拜占廷居民对赛车的热情甚至比罗马城居民更甚。自城市落成之日起,蓝党和绿党就是城市之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赛车党派的影响远超赛场之外,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时常听到绿党支持阿里乌斯派,或者蓝党支持新皇帝篡位。他们不只是体育竞赛者,而是来自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他们选择并支持自己的党派。这一体系对公共秩序构成了相当的威胁,并时常引发暴乱,最终在523年完全爆发,而下文我们将对此详述。绿党向来从东北方向进入大竞技场,坐在东侧;蓝党向来从西北方向进入大竞技场,坐在西侧。皇帝的包厢占据了竞技场较窄的北侧,另有数百个席位留给皇帝的随从们。皇帝包厢中央的座位,就是臣民们最常见到皇帝出现的位置,也正是许多怪象的发生地点。暴民就是在这里为僭越称帝的希帕提乌斯加冕,后者使用妻子的项链临时充作皇冠。两个世纪后,查士丁尼二世也在夺回君士坦丁堡之后端坐于此,其对手利昂提乌斯和阿普斯玛跪的脚凳边,而市民则齐声唱诵诗篇,恰到好处地暗喻着彼时的情境:“你必践踏猛狮和毒蛇。” 大竞技场的中央是“脊”,也称作分隔墙。每一座竞技场都设计有这道墙,用于划分赛道。在那里装点了三座奇特的纪念碑,可以说是这座新城市建造时混杂风格的典型体现。最古老的第一个纪念碑是埃及的方尖碑,上面刻画着常见的象形文字铭文。第二个纪念碑是三头黄铜蛇像,是君士坦丁堡的古物之中最值得注意,却或许也是最缺乏美感的雕像,这是保萨尼亚斯和希腊人为庆贺前479年普拉提亚之战的胜利而献给德尔斐神庙的雕像,蛇头上的金三脚架在六个世纪之前就被不敬神明的福基亚人偷走了,但环绕在底座上的铭文存留至今,告诉当代考古学者它源自何处。赛道中央的第三个纪念碑是时代更近的青铜方柱,与旁边年代久远的文物形成了鲜明对比。幸运的是,三个纪念碑都存留至今。大竞技场的巨大城墙已经坍塌,但中央的装饰依然矗立在开阔的空地之上。土耳其人称大竞技场为“阿特梅丹”,意思是“赛马场”,依稀纪念着旧日的用途。 在大竞技场东侧墙外与奥古斯都广场西侧,有一系列小礼拜堂和雕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前文提到的大里程碑。起初雕像不多,但历代皇帝不断添加,让雕像填满了广场四周。君士坦丁添加的雕像是一根高耸的斑岩柱,上面是希拉波利斯城的庇护神阿波罗的青铜像,而皇帝将雕像的头凿下,换上自己的头像,并添加了一系列皇帝的仪服,用来代表自己。而在罗马,却发生了截然相反的故事。教皇们把科尔索石柱上的雕像进行了修改,把皇帝奥勒留的头像换成了圣彼得的头像。 大竞技场以北是君士坦丁为基督教臣民们建造的大教堂,献给“神圣的智慧”(即圣索菲亚大教堂)。当时建造的教堂还没有后世的著名穹顶,而只是一座类似巴西利卡形制的相对低矮的建筑。在5—6世纪两度被焚毁之后,教堂原来的风格已经荡然无存。从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西门出去,经过一道配有拱顶的木制走廊穿过广场,就能到皇宫的大门。皇帝可以就此免于穿过圣索菲亚大教堂对面的铜器市集,直接从皇宫前去礼拜。这个走廊的作用或许与佛罗伦萨连接彼提宫和乌菲兹的走廊相近。 我们描述的华丽建筑组成了君士坦丁堡的核心区。皇宫、大竞技场与大教堂,是城市历史中绝大多数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城市还向西北方向延伸了数英里,尽管无法与奥古斯都广场的周边区域相比,但沿途值得记述的建筑依然比比皆是。圣使徒教堂是君士坦丁指定的家族墓葬所在地,也是城市中第二壮观的教堂。在更加偏远的地区,值得一提的建筑还有港口一侧的谷仓,以及金门——向西的大路由此入城,另外还有首都执政官的府邸。君士坦丁的骑马雕像就位于首都执政官府邸之外。这尊雕像是君士坦丁堡的主要观光景点之一,存留到了中世纪末期,并衍生出了一些传说故事。 328或329年(准确的年份尚难以确知),君士坦丁决定将拜占庭城作为首都,并制定了城市建设的计划。早在330年5月11日,因为建筑施工进度超出预期,他便举行了城市落成的典礼。基督教主教为尚未完工的宫殿赐福,这是第一次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办的典礼。君士坦丁尽管尚未接受洗礼,却自建城之初便打算让这座新城市基督教化。多神教在城中的遗迹,只剩下在拆毁拜占庭旧城以便建造宫殿和周边建筑时免于被毁的少数旧神庙。搬到浴池与元老院旁边的雕像只是艺术装饰品,而不再受人尊崇。 为了填补这座大城市的人口空缺,君士坦丁邀请罗马城的许多元老,以及希腊和亚洲各省份中的许多富裕地主,搬到这座城市里居住。他在新元老院中给他们安排位置,还向他们赠送住所。不计其数的各级宫廷官员,以及他们的扈从和奴隶,无疑在新城市的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数以千计的画师和手工业者在各种特权的引诱之下搬迁至此,商人和水手们本来就是拜占庭城的常客,如今更是大量涌入,让旧城的繁盛商贸相形见绌。君士坦丁吸引移民来到新首都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古罗马城居民领取面包的特权,尽管其副作用是滋养懒汉。此前运往罗马供给市民的埃及小麦,如今转往君士坦丁堡,此后向罗马运输粮食的只剩下从迦太基出发的航船了。 330年城市落成典礼结束之后,皇帝颁布敕令,将这座城市定为新罗马,刻着这份敕令的大理石板就放在皇帝的骑马雕像旁边。但“新罗马”最终仅仅用于诗文和修辞之中:从一开始,世人便坚持以建造者的名字命名这座城市,称之为君士坦丁堡。 牛津中世纪史大家的经典之作 讲述千年帝国的兴衰成败 一本书读懂拜占庭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