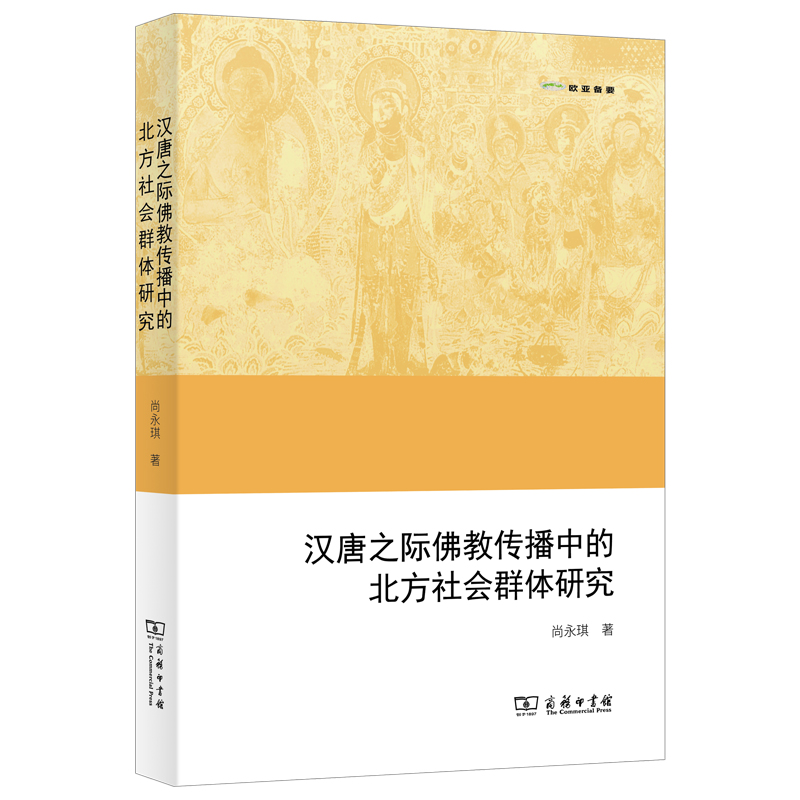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128.00
折扣价: 100.90
折扣购买: 汉唐之际佛教传播中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欧亚备要
ISBN: 9787100241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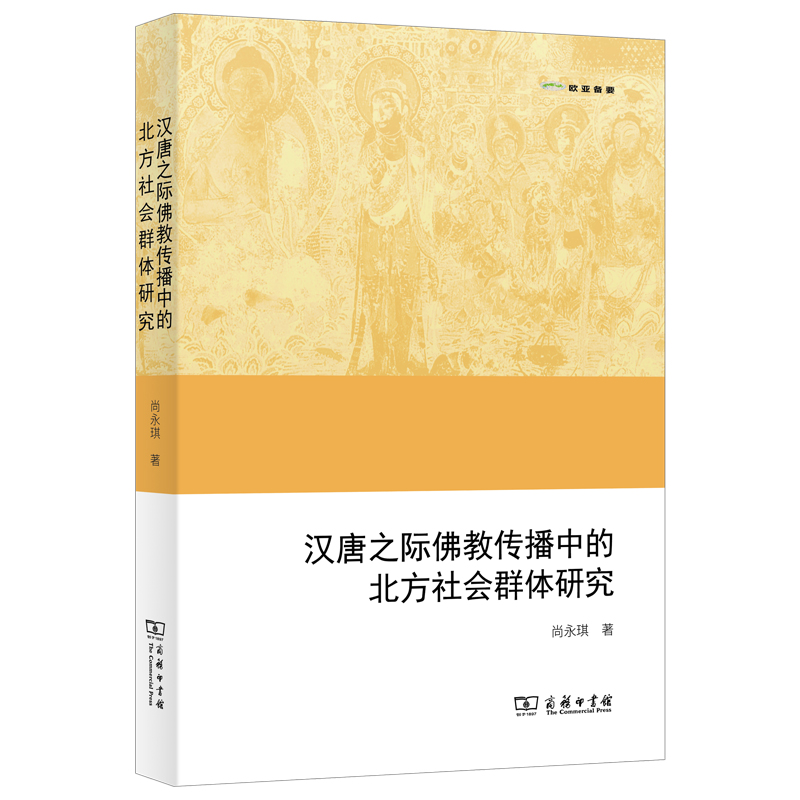
尚永琪,1969年生,甘肃省民乐县人,历史学博士,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等职。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史、丝路文明史、形象史学与动物史的研究。
编者的话 《欧亚备要》丛书所谓“欧亚”指内陆欧亚(Central Eurasia)。这是一个地理范畴,大致包括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东中欧。这一广袤地区的中央是一片大草原。在古代,由于游牧部族的活动,内陆欧亚各部(包括其周边)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有了密切的联系。因此,内陆欧亚常常被研究者视作一个整体。 尽管司马迁的《史记》已有关于内陆欧亚的丰富记载,但我国对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长期落后于国际学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急起直追,严格说来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筚路蓝缕的情景,不少 人记忆犹新。 由于内陆欧亚研究难度大,早期的研究者要克服的障碍往往多于其他学科。这也体现在成果的发表方面:即使付梓,印数既少,错讹又多,再版希望渺茫,不少论著终于绝版。 有鉴于此,商务印书馆发大愿心,选择若干较优秀、尤急需者,请作者修订重印。不言而喻,这些原来分属各传统领域的著作(专著、资料、译作等)在“欧亚”的名义下汇聚在一起,有利于读者和研究者视野的开拓,其 意义显然超越了单纯的再版。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出版时期、出版单位不同,尤其是研究对象的不同,导致诸书体例上的差异,这次重新出版仅就若干大的方面做了调整,其余保持原状,无意划一,借此或可略窥本学科之发展轨迹也。 愿本丛书日积月累,为推动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起一点作用。 余太山 初版后记 对于那些悲天悯人的慈悲智者,我从心底里深深地敬仰他们;对于如我一样在天地间如蝼蚁生存的微弱生命,我期望能同他们在人类良善的平民智慧中息息相通。这就是我要把佛教社会史的研究作为自己博士论文选题的主 要原因。当然,学术道路的选择是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造就的,学术境遇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1995 年我考入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师从陈维礼先生读硕士研究生,1998 年,以“六朝义疏的产生及相关问题考略”为题获得历史文献学硕士学位。2001 年我考回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师从张鹤泉先生读中国古代史博士 学位,方向是魏晋南北朝史。一入学,张老师便在授课的时候主张我们几名博士生以秦汉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问题为主要研究取向,这样在学术问题的把握和学术的地缘方面都会有一些相对的优势。仔细考虑,这确实是一 个很好的建议,也非常适合我,我是个性格粗疏的人,喜欢北方草原地区的那种粗犷、开阔,做北方历史的研究应该是比较顺畅的,至少契合性格。由于有读硕士期间对于佛教文献阅读和把握的基础,随后,我就确定了“魏晋南北朝佛寺考”这样一个比较大的题目。但是做了多年的编辑工作,对于原始文献的关注和阅读就显得比较薄弱,所以当时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多少自信,至少是不太了解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可用资料的数量等方面的状况。幸好,我的导师张鹤泉先生是个对于学生认真负责的老师,他的不厌其烦的督促和引导,使我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很快进入了研究状态。 2002 年,由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的推荐,我获得了台湾“中流与喜马拉雅基金会”的大陆青年学者基础研究奖助,记得主持此事的台湾大学政治系曹俊汉教授在一次学术恳谈会上非常关切地说:“做这样的冷僻研究是很辛苦的,你只要做出来,我们就一定资助出版。”遗憾的是,《魏晋南北朝佛寺考》最终因为涉及范围过大、工作量艰巨而不得不中途放弃。后来,我以“北朝佛寺考”为题搜集了大量材料,并初步定出一个写作提纲交给导师张鹤泉先生。张老师在几经推敲之后,建议我还是以其中的一部分 —“北方佛教社会群体”为题展开考察,这样就进一步缩小了研究的范围,避免了在宽泛的研究领域内漫无目的地四面出击,有利于深入展开研究。至此,我的博士论文题目终于确定为“3—6 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这是我同导师共同探讨、努力的结果。 学术论文的写作是一个精神愉悦的过程,当然也免不了会有一些艰难,但艰难仅仅是思维的曲折而已。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张鹤泉先生同我有过很多次的关键性问题探讨,为我理清了写作中出现的一些比较纷繁的头绪。从 同门师兄沈刚先生的书房中借来的大堆资料和参考书,为我的资料查询工作提供了方便,减轻了不少负担。2006 年 6 月,论文完成并进入答辩程序。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李凭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尊 敬的詹子庆、陈恩林、吕文郁、张鹤泉、王彦辉、许兆昌诸先生组成了答辩委员会,给我的论文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修改建议;严耀中、陈长琦、牟发松、张金龙等先生作为论文评议人,非常认真负责地对全文存在的问题做了 仔细校正,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上述各位先生的意见,使我文中的很多错误之处甚至一些相当低级的错误得到了及时纠正,衷心地感谢他们辛勤的劳动和真诚的指正,尤其感谢牟发松先生的鼓励。 认认真真地去完成一篇博士论文,确实是一件重要的甚至庄严的事情,从心底来讲,我从来不敢有半点松懈,我想我的至亲好友也是如此考虑的,岳父母和妻子晏宗杰的大力支持至关重要。我大学时期的老师雷紫翰教授多 年来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之一,他持续十多年不断的引导和帮助,为我走上学术道路廓清了很多糊涂的认识。硕士时期的导师陈维礼先生为我寻找各种资料,甚至从其朋友的书架上硬将一些他认为有用的书给我借了过来。可是 一向硬朗潇洒如年轻人的陈先生竟在 2005 年因病仙逝,这对我也是一个不小的冲击。维礼老师是我如师如友的慈悲长者,是我人生转折点上一个无法抹去的身影。从他的言传身教中,我得到了关于人生的很多慰藉与感悟。过 去的艰难生活和草根出身所赋予我的许多不良的狭隘思想,就是在陈先生的影响下渐渐淡化的,如果我在今后的岁月里能成为一个宽厚的人,都应该归功于陈先生,感谢这个悲天悯人的老人。我相信学术也是植根于生活的,我 的生活中出现的长者们总是给我各种关怀和启迪,陶冶我粗野的底色逐渐走向温和。为了我的成长,尚兰英等我的几个姐姐付出了慈母一样的辛勤,而我无以为报。有时候,真的希望自己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能独立完成自己选 择的事情。可惜,我很渺小,所以免不了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也像个寄生虫一样耗费亲友的力量,牵扯甚广而所获寥寥,真是惭愧得很。 让我感到慰藉的是,由于张鹤泉先生的厚爱,我的这篇论文被推荐列入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的出版资助行列,能够得以出版,这对我来说是学术上的一份沉甸甸的收获,衷心地感谢我的老师 —一个直率、可爱的先生,一位严谨认真的学者。我相信在一些成就的后面,总是凝聚了很多人的力量,为此,我对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主任朱泓教授、刘艳副主任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深深的谢忱,正是你们的不懈努力和辛勤争取,使我得到了一个展示学术成果的机会。 可能是出身草根的缘故,心底里一直对官家哲学或官家历史的那些堂而皇之的东西,有一种植根于血液的排斥感,所以希望自己能研究和关注底层人的“草根历史”。我还非常仰慕那些能认真生动地“描述”历史的历史学 家,多么希望自己能从《左传》、《史记》这样生动鲜活的历史典籍中学习到一丁半点的史学智慧,写一篇生动鲜活的历史文章。可惜我还是写了这样一篇语言干巴、内容寡淡的分析型论文,虽然这比较符合历史学研究的规范, 然而我还是认为一个学习了多年历史学的人,只能写这些半通不通的所谓专业论文,不能成为一个“描述历史”的人而成为一个拼凑词语的人,真的是一种极大的遗憾。 幸好,我的导师给了我最大的包容和鼓励性理解,我赖以谋生的杂志社集体是如此具有温暖色彩,使我能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生长出一些可爱而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也是一种幸运。为此,我借这一方文字,对帮助和关怀我 的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2008 年 5 月 8 日 后? 记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3—6 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于2008 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纳入《欧亚备要》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修订版。鉴于原版书名过长,斟酌再三,为精练起 见,还是改名为《汉唐之际佛教传播中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原本想在这个标题前面加个概括性词语“慈悲众生”,后来还是接受出版社建议,将其删去 —这样主题更精练,意蕴更明确。内容也做了一些增补,主要是消除文字错讹、完善注释要素、增加修正部分论述,但整体改动很小。原版有一些随文插图,修订版全部撤下,因为文字描述比较清晰,没有图版也不影响阅读和理解。2019 年 3 月份,我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调到宁波大学,由小编转为教师,研究领域也从早期佛教史转向了动物史的研究。工作性质不同,研究方向调整,学术兴趣与生活心态有较大变化,因此,再次仔细阅读、思考和修改将近 20 年前的学术作品,自然感触良多。在修订工作初期,我的研究生洪寅欣同学协助我校订、补齐了注释,晏宗杰老师协助编制了索引。2024 年的夏天真是个酷夏,本书校稿期间,我承担的国家重点课题“汉唐时代的动物传播与文明交流研究”书稿也到了最后的交稿期限,7 月份在宁波家中站着工作,居然会领略到腿脚肿胀的滋味,也是很深刻的记忆。很喜欢济慈的那句诗:“地球是生长灵魂的河谷!”我很忐忑,大半生陷在如本书这样鲜有人读的文字工作中,我的灵魂真的在这个河谷中得到如彼岸所望的生长了吗?在此岸,恐怕只能忐忑了。 2024 年 9 月 5 日 芸芸众生在3—6世纪佛教香火里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