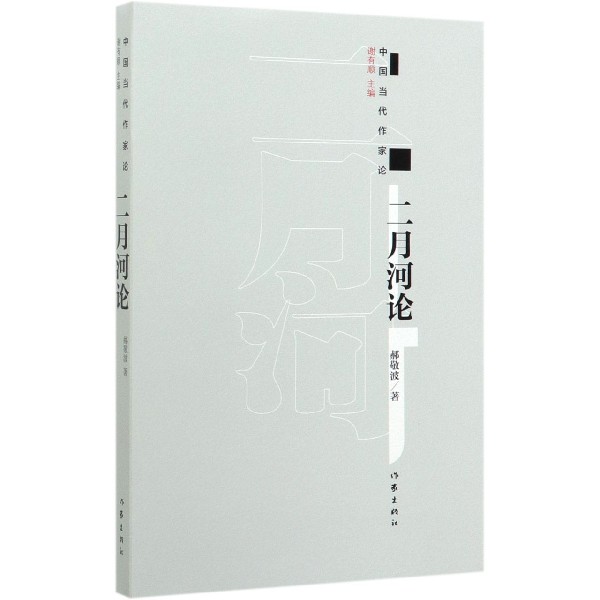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8.80
折扣购买: 二月河论/中国当代作家论
ISBN: 9787521207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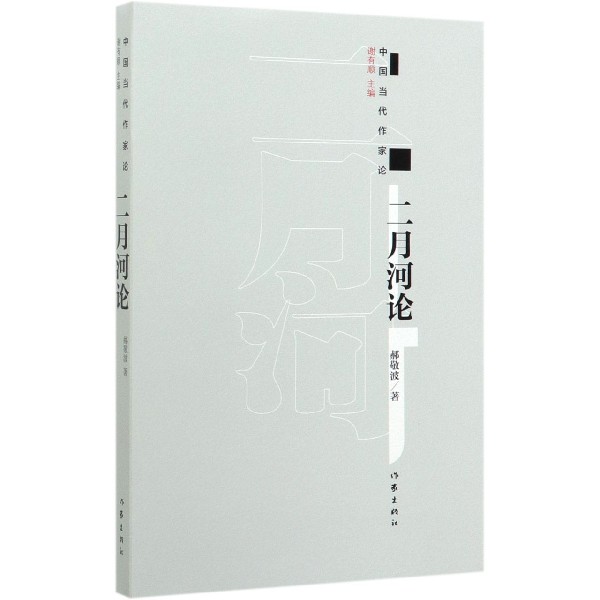
郝敬波,文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是近年来活跃在当代文学批评界的青年批评家,其对文学现场的关注和批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发表论文多篇。
第一章 二月河历史小说的阅读与评价问题 对二月河的讨论,我们从二月河去世之后“读者”对其历史小说的再次“发声”说起。或许我们都没有料到,二月河先生的离世竟引起人们对其小说的再次热议。现在,“读者”的声音在网络上还可以轻易找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尽量平心静气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检视自己的真诚与虚伪,反思自己的批评立场与批评姿态,并以这种方式走近一个作家,走进作家的艺术世界。在媒体和资讯发达的时代,我们不以任何理由回避任何一种声音。相反,我们尊重这些声音,正如有批评家指出:“对一个时代文学的判断应该是全体阅读者共同参与的民主化的过程,各种文学声音都应该能够有效地发出。这个时代的文学阅读,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一种互补性的阅读。为什么叫‘互补性的阅读’?因为一个批评家再敬业,再劳动模范,一个人也读不过来所有的作品。举个例子:一年五千部长篇小说,一个批评家如果很敬业,每天在家读二十四小时,他能读多少部?一天读一部,一年也只能读三百多部。但他一个人读不完,不等于我们整个时代的读者都读不完。这就需要互补性阅读。所有的读者互补性地读完所有作品。在所有作品都被阅读过的情况下,所有的声音都能发出来的情况下,各种声音的碰撞、妥协、对话,就会形成对这个时代文学比较客观、科学的判断。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都有命名的‘权力’、使命和责任。” 当然,我们需要辨别这些声音——连同我们自己的声音一起,我们需要知道它们来自于哪里,是否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声音”,能够回响多久。我们期望这样的初衷和讨论能够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让不同的读者参与讨论和辨析,以形成自己更明晰的情感和立场,以不同的倾向和方式参与当代文学的批评建构。 一、从读者与阅读说起 人们对于二月河去世的关注如同之前对于金庸去世的关注一样,充满了惋惜和追思的情感。置身其中,我们在新媒体对该消息的传播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这是当代文学发展的特征,它给我们提供了文学现场,让人如此切近地观察和感受,并一起见证、参与文学的进程。同时,这种“近距离”也给当代文学的评判带来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了当代文学评估的“难度”。如果把这种“难度”都付与未来的时间,丢给未来的研究者,这不仅不是一种积极的学术态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会造成当代文学批评的某种失语,正如吴义勤在谈到文学“经典化”问题时指出:“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很多人认为都是由后人完成的,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拿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它的经典化和历史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其实一直是同步进行的。胡适、周作人在五四时代就开始了白话文学史的写作,而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更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里程碑式的工程,它的‘导言’以其不可替代的权威性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化和历史化确立了标准和方向。我们今天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作家的评价仍然要以此为依据,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个‘大系’没有这个‘导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会是什么模样。”因此,我们应该在“文学现场”中来讨论二月河。近一段时间以来,二月河故去所引发的读者评判,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现象。我们就从这里为起点,展开对二月河历史小说的新思考。读者对二月河历史小说整体上是如何评价的?它可能的意义和价值有哪些?它对于我们评价二月河带来哪些反思?我觉得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地思考,而且应该在更为开放的视阈中进行展开。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哪些“读者”参与了对二月河的评论。我们常把读者划分为一般读者和专业读者,一般读者指的是社会上广泛的普通读者,专业读者多指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专门研究的读者。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对阅读和接受的讨论是以这两类读者为参照的。在市场化和新媒体发达的时代,“读者”的情况实际上要复杂得多。二月河小说因为与影视的“联姻”而广为传播,影响广泛,因而其拥有的“读者”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目前文学“读者”的类型和状况。 一是普通的文学“接受者”。这里“接受”可以通过一般的阅读,也可以通过影视作品来了解文学作品。从实际情况来看,后一种方式可能要更多,我们把这部分“观看者”也作为“读者”。之所以如此,我们基于两点考虑,一是1990年代以来文学仓0作、传播和接受的实际状况,二是避免对当代文学阅读研究的某种“遗漏”,因而采取这种较为“宽容”的类分。实际上,在新媒体传播时代我们有时很难区分传统阅读意义的读者和通过其他方式了解作品的接受者。譬如,“有华人处就有二月河小说”“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这样的描述就包括了各种的接受方式,这些“接受者”应该视为一类“读者”。P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