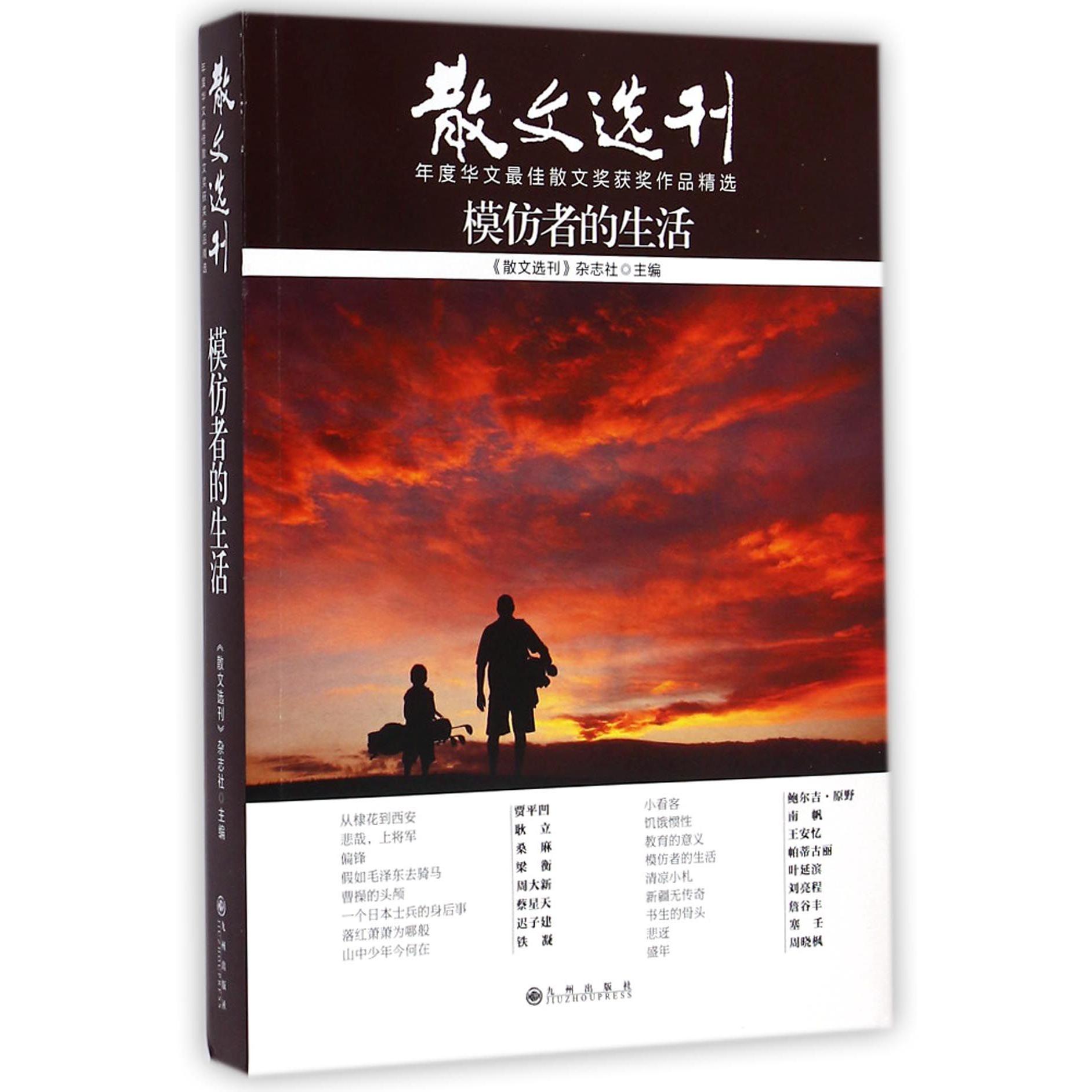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29.8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模仿者的生活(散文选刊年度华文最佳散文获奖作品精选)
ISBN: 9787510833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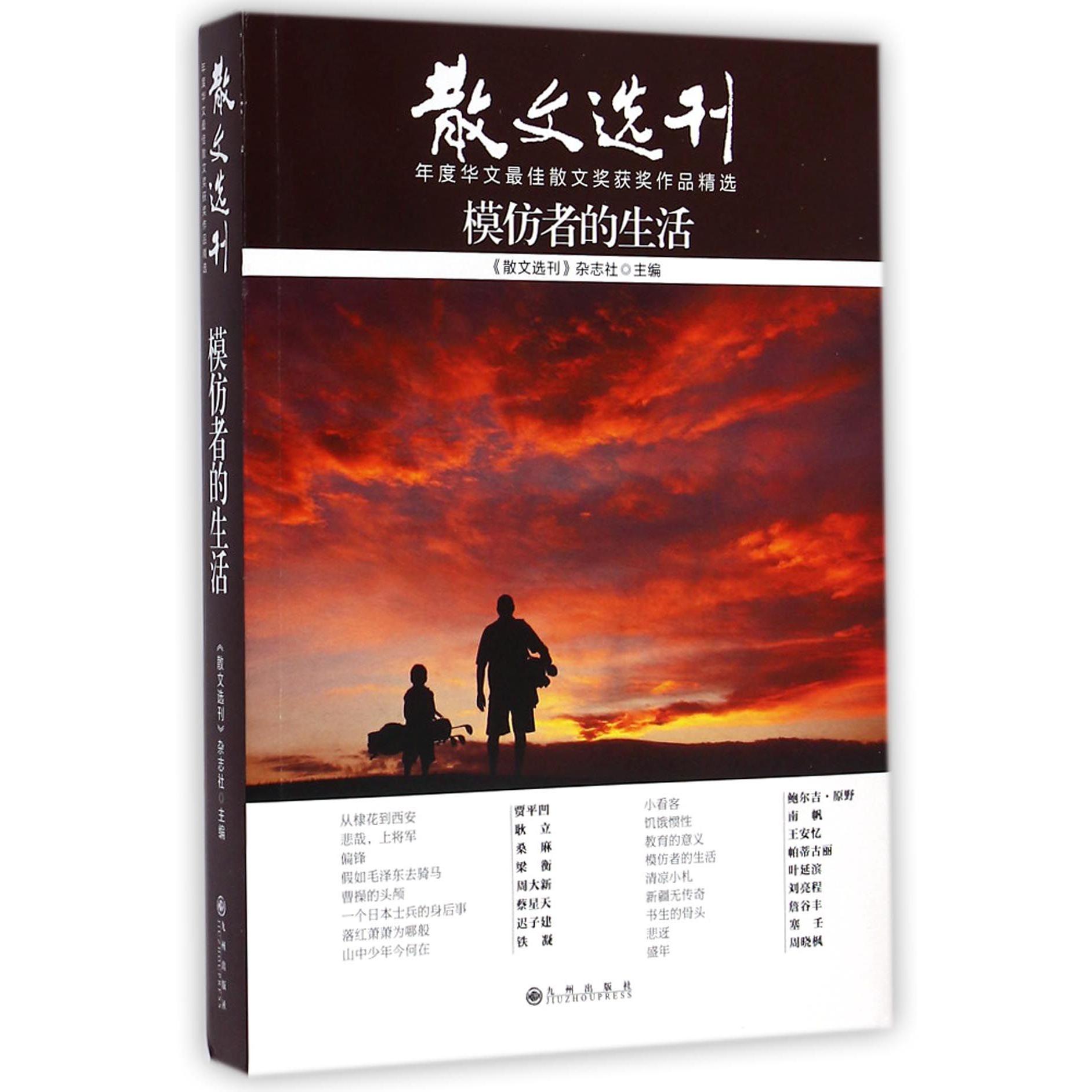
秦岭的南边有棣花,秦岭的北边是西安,路在秦 岭上约300里。世上的大虫是老虎,长虫是蛇,人实 在是走虫。几十年里,我在棣花和西安生活着,也写 作着,这条路就反复往返。 父亲告诉过我,他十多岁去西安求学,是步行的 ,得走七天,一路上随处都能看见破坏的草鞋。他原 以为三伏天了,石头烫得要咬手,后来才知道三九天 的石头也咬手,不敢摸,一摸皮就粘上了。到我去西 安上学的时候,有了公路,一个县可以每天通一趟班 车,买票却十分困难,要头一天从棣花赶去县城,成 夜在车站排队购买。班车的窗子玻璃从来没有完整过 ,夏天里还能受,冬天里风刮进来,无数的刀子在空 中舞,把火车头帽子的两个帽耳拉下来系好,哈出的 气就变成霜,帽檐是白的,眉毛也是白的。时速至多 是40里吧,吭吭唧唧在盘山路上摇晃,头就发昏。不 一会儿有人晕车,前边的人趴在窗口呕吐,风把脏物 又吹到后边窗里,前后便开始叫骂。司机吼一声:甭 出声!大家明白夫和妻是荣辱关系,乘客和司机却是 生死关系,出声会影响司机的,立即全不说话。路太 窄太陡了,冰又瓷溜溜的,车要数次停下来,不是需 要挂防滑链,就是出了故障,司机爬到车底下,仰面 躺着,露出两条腿来。到了秦岭主峰下,那个地方叫 黑龙口,是解手和吃饭的固定点。穿着棉袄棉裤的乘 客,一直是插萝卜一样挤在一起,要下车就都浑身麻 木,必须揉腿。我才扳起一条腿来,旁边人说:“那 是我的腿。”我就说:“我那腿呢,我那腿呢?”感 觉我没了腿。一直挨到天黑,车才能进西安,从车顶 上卸下行李了,所有人都在说:“嗨,今日顺到!” 因为常有车在秦岭上翻了,死了的人在沟里冻硬,用 不着抬,像掮椽一样掮上来。即使自己坐的车没有翻 ,前边的车出了事故,或者塌方了,那就得在山里没 吃没喝冻一夜。 90年代初,这条公路改造了,不再是沙土路,铺 了柏油,而且很宽,车和车相会没有减速停下,灯眨 一下眼就过去了。过去车少,麦收天沿村庄的公路上 ,农民都把割下的麦子摊着让碾,狗也跟着撵。改造 后的路不准摊麦了,车经过“唰”的一声,路边的废 纸就扇得贴在屋墙上,半会儿落不下。狼越来越少了 ,连野兔也没了,车却黑日白日不停息。各个路边的 村子都死过人,是望着车还远着,才穿过路一半,车 却瞬间过来轧住了。棣花几年里有五个人被轧死,村 人说这是祭路哩,大工程都要用人祭哩。 以前棣花有两三个司机,在县运输公司开班车, 体面荣耀。他们把车停在路边,提了酒和肉回家,那 毛领棉大衣不穿,披上,风张着好像要上天,沿途的 人见了都给笑脸,问候你回来啦?就有人猫腰跟着, 偷声换气地乞求明日能不能捎一个人去省城。可现在 ,公路上啥车都有,连棣花也有人买了私家车。 那一年,我父亲的坟地选在公路边,母亲就说离 公路近,太吵吧,风水先生说:“这可是好穴哇,坟 前讲究要有水,你瞧,公路现在就是一条大河啊!” 我每年十几次从西安到棣花,路经蓝关,就可怜 了那个韩愈,他当年是“雪拥蓝关马不前”呀,便觉 得我很幸福,坐车三个半小时就到了。 过了2000年,开始修铁路。棣花人听说过火车, 没见过火车。通车的那天,各家通知着外村的亲戚都 来,热闹得像过会。中午时分,铁路西边人山人海, 火车刚一过来,一人喊:“来了——!”所有人就像 喊欢迎口号:“来了来了!”等火车开过去了,一人 喊:“走了——!”所有人又在喊口号:“走了走了 !”但他们不走,还在敲锣打鼓。十天后我回棣花, 邻居的一个老汉神秘地给我说:“你知道火车过棣花 说什么话吗?”我说:“说什么话?”他就学着火车 的响声,说:“棣花——!不穷!不穷!不穷不穷, 不穷不穷!”我大笑,他也笑,他嘴里的牙脱落了, 装了假牙,假牙床子就笑了出来。 有了火车,我却没有坐火车回过棣花,因为火车 开通不久,一条高速路就开始修。那可是八车道的路 面呀,洁净得能晾了凉粉。村里人把这条路叫金路, 传说着那是一捆子一捆子人民币铺过来的,惊叹着国 家咋有这么多钱啊!每到黄昏,村后的铁路上过火车 ,拉着的货物像一连串的山头在移动,村人有的在唱 秦腔,有的在门口咿咿呀呀拉胡琴,火车的鸣笛不是 音乐,可一鸣笛把什么声响都淹没了。火车过后,总 有三五一伙端着老碗一边吃一边看村前的高速路,过 来的车都是白光,过去的车都是红光,两条光就那么 相对地奔流。他们遗憾的是高速路不能横穿,而谁家 狗好奇,钻过铁丝网进去,竟迷糊得只顺着路跑,很 快就被轧死了,一摊肉泥粘在路上。 我第一回走高速路回棣花,没有打盹,头还扭来 转去看窗外的景色,车就突然停了,司机说:“到了 。”我说:“到了?”有些不相信,但我弟就站在老 家门口,他正给我笑哩。我看看表,竟然仅一个半小 时。从此,我更喜欢从西安回棣花了,经常是我给我 弟打电话说我回去,我弟问:“吃啥呀?”我说:“ 面条吧。”我弟放下电话开始擀面,擀好面,烧开锅 ,一碗捞面端上桌了,我正好车停在门口。 在好长时间里,我老认为西安越来越大,像一张 大嘴,吞吸着方圆几百里的财富和人才,而乡下,像 我的老家棣花,却越来越小。但随着312公路改造后 ,铁路和高速路的相继修成,城与乡拉近了,它吞吸 去了棣花的好多东西,又呼吐了好多东西给棣花,曾 经瘪了的棣花慢慢鼓起了肚子。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