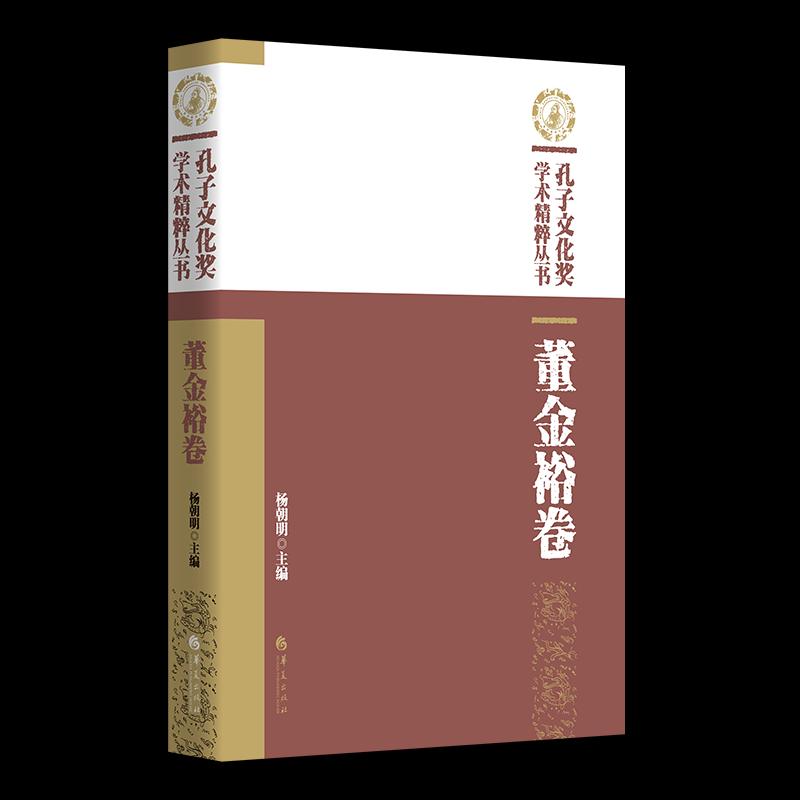
出版社: 华夏
原售价: 86.00
折扣价: 54.20
折扣购买: 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董金裕卷
ISBN: 97875080997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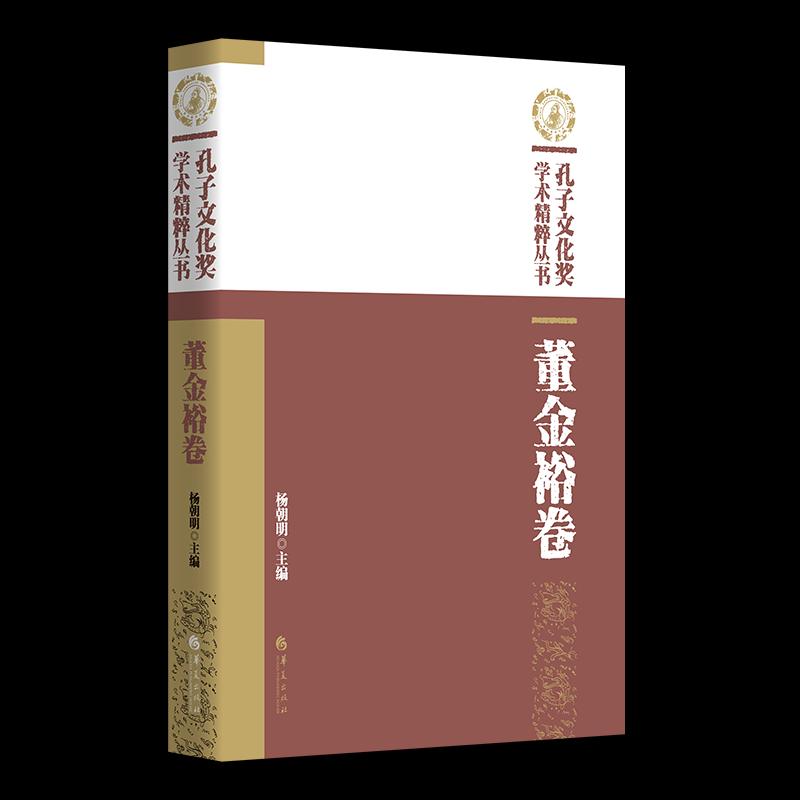
董金裕(1945—),台湾苗栗县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学士,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博士。曾任静宜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兼教务处处长,孔孟学会执行秘书兼《孔孟月刊》《孔孟学报》主编,中国经学研究会理事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等职。现任政治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台湾古籍保护学会会长、孔孟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等职。学术专长为孔孟思想、经学、宋明理学。著有《至圣先师孔子释奠解说》《经传中以数字显现的儒家之道》等专著十余本、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书摘(20%-30%) 十、黄宗羲“明夷待访”,待谁之访? 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在国破家亡,饱受刺激之余,以其对国家民族的关切之情,对政治事务的明睿之智,发挥其政治理想,从思想的立场,检讨明代政制的得失,并上溯我国自三代以来的政治措施,完成《明夷待访录》一书。对于政教军经种种措施,不仅能提出他的理论,更能够指出实际推行时的应兴应革之道;层面广泛,体用兼具;信为我国政治思想史上难得一见的较有系统的著作。因此在成书之始,即赢得了许多学者的推崇。 可惜,到了乾隆年间,《明夷待访录》却被列为禁书,以致未能对清朝的政治产生任何影响。直至清朝末年,由于西学的东传,大家发现此书有许多迈越前人之处,也可以与新思潮相发明,于是乃特别重视,又开始发挥作用,对于晚清的变法维新运动,甚至于推翻满清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政府,都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书的价值与地位,至此遂被重新肯定,而不断有人加以研究。但由于此书书名“明夷待访”牵涉到待访对象的问题,引起很大的争议。此种争议不仅有关于黄宗羲的人格,并且和我们中华民族的正气纲常有很大的牵涉,不容我们不加辩明。本文即尝试就此问题加以探讨,以阐明黄宗羲的苦心曲为。 (一)问题的症结 “明夷”为《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六卦的卦名,其卦象为椕,离楀在下,坤?在上,离代表日,坤代表地,日入地中,光明就被掩蔽了。夷的意思是损伤,太阳既潜藏于地下,无法焕发光芒,如同受到损伤一般,所以称“明夷”。此卦在人事上有双重的意义:一为代表昏君在上,明臣在下,不能发挥才干,实现理想,处境非常艰难困苦。二为代表目前的境况虽然暗淡,但若能坚贞自守,则前途仍是一片光明,就如太阳虽潜伏地下,最后还是会升出地平线,散发光辉,使大地化暗为明。 以此卦所显示的这两层意义,衡诸黄宗羲所处的境地及所怀抱的心情,可谓极为适切。但此卦的《彖传》曰: 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又此卦六五爻的爻辞及爻象曰: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是在《明夷》卦中,曾多次提到箕子。而“待访”之典出于《尚书》,根据《洪范》篇的记载,周武王平定天下以后,拜访商朝遗臣箕子,向他请教治理天下国家的至理要道,箕子乃向武王陈述九项治理天下国家的大法则。武王接纳他的意见,封赐诸侯,使上下尊卑各有等分,天下而获得安平太平: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 可见“待访”与箕子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又黄宗羲本人于其《明夷待访录》自序中亦云: 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 是可见黄宗羲也以箕子自拟。 从以上这些资料,皆可明白看出“明夷待访”之名,与箕子受武王之访一事有关。但箕子为商朝遗臣,武王则为周朝开国之主;准此而论,黄宗羲既为明朝遗老,则其待访的对象岂不就是满清皇帝?问题遂由此产生,而引起大家探讨的兴趣,提出许多莫衷一是的看法。 (二)对各家说法的商榷 《明夷待访录》成书以后,即得到许多学者的推崇,当时已有人对书名的出典感到不妥,而提出看法。晚清以来,由于此书受到特别重视,对这一问题表示意见者更多。兹将各家说法依时代先后之序胪列于下,并评述其说是否可以成立,以作为本文探讨此问题的基础。 1.黄肖堂说 全祖望《鲒埼亭集·黄丈肖堂墓版文》曰: (黄肖堂)尝与予读《明夷待访录》,曰:“是经世之文也,然而犹有憾。夫箕子受武王之访,不得已而应之耳!岂有艰贞蒙难之身,而存一待之见于胸中者,则麦秀之恫荒矣!作者亦偶有不照也。”予瞿然下拜,曰:“是言也,南雷之忠臣,而天下万世纲常之所寄也。” 据此,则黄肖堂与全祖望皆以为黄宗羲采用“明夷”“待访”之典,实由于“偶有不照”。 黄宗羲对经学极为重视,据载: 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说。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 其对于《周易》及《尚书》尤有精深之研究,所著《易学象数论》,为其重要著作之一,下开胡渭《易图明辨》之端;而《授书随笔》则为答阎若璩问《尚书》而作。对于后来清儒在此二经有突破前人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启发之功。以黄宗羲对此二经的熟习程度,引用出于这两本书中有关箕子的典故,而谓其“偶有不照”,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2.章太炎说 章太炎《章氏丛书·文录一·说文上》云: 黄太冲以明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 盖章氏以为黄宗羲所期待的对象即是清廷,因此对黄宗羲极为不满,而大加讥评,并斥之为“守节不孙”。 吾人若对黄宗羲一生的活动稍加考察,即可知章氏之说实有诬罔之嫌。盖黄宗羲自明思宗殉国以后,即不顾身家的安危,号召义兵,积极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甚至于还不辞风波之险,远渡重洋,希望能向日本乞得援兵。直至清朝已经平定整个天下,黄宗羲眼看大势已去,才开始不过问世事,专心致力于讲学著述。后来清廷曾屡次征召他出来做官,他都加以拒绝。若其所待访的对象确为清廷,则理当欣然就道,岂有严加拒绝的道理?而且当康熙十八年(1679),他最得意的弟子万斯同到北京同修明史,黄宗羲为他送行时,还告诫他千万不可以向异代君主奏陈太平之策。又于其临终之前,遗命家人,在他死后,不用棺木,只为遗体垫覆一褥一被即可,其意乃以为自己身遭家国巨变,期望遗体速朽。凡此作为皆可显现他不愿臣服于异族之意,则其所著书岂有“将俟虏之下问”的心意在耶? 3.梁启超说 梁启超为反驳章太炎的看法,于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曰: 章太炎不喜欢梨洲,说这部书是向满洲上条陈,这是看错了。《待访录》成于康熙元、二年,当时遗老以顺治方殂,光复有日,梨洲正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耳。他送万季野北行时,戒其勿上河汾太平之策,岂有自己想向清廷讨生活之理? 梁氏辨明章氏之说的非是,虽极有道理,但他以为黄宗羲之写作《明夷待访录》,乃因“光复有日”,“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恐怕也未能成立。盖《明夷待访录》开始撰拟于康熙元年(1662),完成于康熙二年。书成之时,桂王已于康熙元年六月遇害,鲁王也于同年十一月卒于台湾,明朝宗室至此已尽。而当时反清的唯一稍成气候的势力———郑成功亦在元年五月病死。虽然“顺治方殂”,但清朝实际上已掌握了整个天下,何来“光复有日”,“待清而兴者”?又据全祖望云: 是岁(指《明夷待访录》成书之年)为康熙癸卯,年未六十(黄宗羲年五十四),而自序称梨洲老人。万西郭为予言,征君自壬寅前,鲁阳之望未绝,天南讣至,始有潮息烟沉之叹,饰巾待尽,是书于是乎出。盖老人之称所自来已。 亦可见黄宗羲此时已对整个天下之大势相当清楚,当然也不会对明朝的复兴抱持任何希望了。 4.杨家骆说 先是,钱穆先生于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云: 考康熙己末(十八年),万季野至京师,梨洲送之,戒以勿上河汾太平之策。时已距《待访录》成书十五六年。则梨洲之不可夺者不确如乎。亭林诗亦云:“未敢慕巢由,徒夸一身善。穷经待后王,到死终黾勉。”亡国遗臣之不能无所待者,正见其处心之愈苦耳。 钱先生之言,意在驳斥章太炎之说,只是并未明指黄宗羲所欲待访之对象。其后,杨家骆乃就钱先生此论更加推阐曰: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所论,可谓能识宗羲矣,然犹未尽也,按“明夷”本《周易》卦名,其象为日入地中,明而见伤。宗羲即取以代“明遗”二字;复以日入地中,示明社已屋之痛,以明而见伤,示己之明必见伤于新朝。试读《原君》所论,非为公仆之人君,皆在所斥,岂冀见访于新朝者之所宜言乎?则其所待者非清室可知矣。“明夷”卦文有“箕子明夷”语,宗羲乃诡称“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以晦其旨。箕子虽受武王之访,而别立国于朝鲜,然则宗羲所待者或为如箕子朝鲜之延平海国也。盖宗羲此书成于康熙二年(1663),即明郑取台湾之第三年,吴三桂杀明桂王及鲁王薨于台湾之次年,“如箕子之见访”,不应释为“如箕子受武王之访以访我”,而应释为“如箕子一类人物之访我”。 杨家骆辨明黄宗羲所待者非清室,引《原君篇》内容为证,论据详审,甚有见地。但他认为黄宗羲自序所谓“如箕子之见访”不应解释为“如箕子受武王之访以访我”,而应解释为“如箕子一类人物之访我”,且据此认定“宗羲所待者或为如箕子朝鲜之延平海国也”,虽曲意为黄宗羲辩护,然不论就“明夷”“待访”典故所出的《周易》《尚书》本意而言,或就“如箕子之见访”的文章而言,皆不容做那样的曲解。更何况《明夷待访录》成书之时,郑成功已谢世,而郑经之懦弱不足以有为,黄宗羲也知之甚审,更不可能期待他的来访。 5.高准说 高准在其《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对象之探索》一文中,共举出十二点理由,以为黄宗羲所期待者,既非清廷,亦不是复明的志士,而是具有不忍人之心而能行天下为公之大义的豪杰,其言曰: 故吾人以为《明夷待访录》之著,实既非向清室上条陈,而亦非有待于抗清复明者之访。……则吾人以为梨洲所待者乃真具不忍人之心而能行天下为公之大义之豪杰也。 其基本立场在于认为黄宗羲并无民族主义之思想,且谓“《待访录》全书又绝无涉及夷夏之语”。并由此判定黄宗羲早岁的抗清活动盖出于传统的忠孝观念与朋友之义,更再三暗示清室可以成为黄宗羲待访的对象,曰:“若清室而能使万民安乐,固亦未尝不可奉之也。”“则设满清而能行礼教之治,梨洲固当以为不必抗之也。”“则梨洲岂非以为清亦可以为政乎?”“设清廷而真能弃种族压迫之旨,具天下为公之心,以期行保民而王之政,则推梨洲之意,当亦欣然愿其来观此书。” 高准以为“梨洲所待者乃是真具不忍人之心而能行天下为公之大义之豪杰也”,参照《明夷待访录·原君篇》所持之意,其言实甚是。但他认为黄宗羲并无民族主义之思想,则似尚有待斟酌。盖除前述黄宗羲早岁曾进行抗清之活动,晚年曾屡次拒绝清廷之征召,又于遗嘱中交代死后不用棺木,期望遗体速朽外,平日“于国难诸公,表章尤力”。又当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征召其弟子万斯同修明史时,万斯同本不欲赴召,黄宗羲乃以征存故国文献为勉,谓以白衣从事,亦以报国也;并戒其勿上河汾太平之策。且于《谢时符先生墓志铭》中云:“嗟乎!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悯黍离,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心人矣!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凡此皆可见其眷眷故国之思,又怎么说他并无民族主义之思想哉? 又高准以为黄宗羲之抗清,盖出于传统的忠孝观念与朋友之义,亦有待商榷。若然,黄宗羲之不顾老母、妻女及己身之安危,以与清兵相周旋,又岂合乎事亲之道,以及“亲在,不许友以死”的友交之义? 高准之论,最不足以服人者,厥为再三暗示满清可以成为黄宗羲待访的对象。其所假设的情况与清廷的实际作为皆无相符合者。考清兵南下之时,杀戮牵连之惨,以两浙一带为最甚。黄宗羲为浙人,感受之痛可以推想而知,清廷既非“真具不忍人之心而能行天下为公之大义之豪杰”,又岂可将之推想为黄宗羲可能期待的对象? (三)结语——黄宗羲的艰难处境与苦心悲意 综合以上各家的说法,以及笔者所做的检讨,我们盖可明白看出: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所期盼的对象,既不可能是清廷,也不是当时反清复明的志士;配合其书中内容所言,应该是如高准所说的“真具不忍人之心而能行天下为公之大义之豪杰”。然则,这位豪杰究竟是谁?鄙意以为,在黄宗羲的心目中并无特定的对象。只要确能合乎其书中所言者即为理想中的人选,但不必是与其同时的人物。顾炎武与黄宗羲书云: 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 所谓“著书待后”实能深得黄宗羲之意。我们如再加深究,又可发现《明夷待访录》的思想渊源及立意所在,诚如萧公权所言: 《待访录》之最高原理出于《孟子》之贵民与《礼运》之天下为公。其政治哲学之大要在阐明立君所以为民与君臣乃人民公仆之二义。 只是自孔子、孟子以来的许多怀抱高尚理想的学者,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的阻限,从来就没有人能真正地达成心愿。但现实的险恶不如人意是一回事,对于世道人心终不能没有理想。尤其是在面对大变局时,此种心愿更是强烈,故钱穆先生云: 亡国遗臣之不能无所待者,正见其处心之愈苦耳。 古仁人之伟大而足以令人崇仰处在此,其悲苦而令人报以无限同情处也在于此。 前面列举各家说法中,除章太炎以外,皆不认为黄宗羲待访的对象为清朝政府,但其中却有疑点存在,即黄宗羲所待者如确实不是清朝政府,那么为何要采用“明夷”“待访”以名其书?除黄肖堂、全祖望以“偶有不照”为黄宗羲做勉强回护,而我们判定为不可能之外,其他各家对此都毫无交代。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黄宗羲的用心所在究竟为何?据全祖望云: 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 就黄宗羲写作此书的时代而言,清朝刚以异族入主中国不久,正不遗余力地在铲除反抗势力;对于读书人,每每兴起文字狱加以箝制。尤其是康熙二年(1663),也就是《明夷待访录》成书的当年,庄廷鑨史狱才发生。可见黄宗羲在异族的高压统治下,为抒发自己的理想,乃不得不避嫌忌讳,故意以箕子见访作为全身避祸的托词。 抑又有言者,有些人喜欢摭拾黄宗羲的片言只字,认定他对于大节不免有所亏缺。其实全祖望对此早已有所辨明,曰: 若谓先生以故国遗老,不应尚与时人交接,以是为风节之玷,则又不然。先生集中,盖累及此,一见之《余若水志》,有曰:“斯人生天地之间,不能一无干涉。身非道开,难吞白石;体类王微,尝资药裹。以是叹活埋土室之难也。”一见之《郑平子序》,有曰:“王炎午生祭文丞相,其风裁峻矣,然读其与姚牧庵书,殷殷求其酬答。盖士之报国,各有分限,正亦未可刻求也。”是可以知先生之所以自处,固有大不得已者。盖先生老而有母,岂得尽废甘旨之奉?但使大节无亏,固不能竟避世以为洁。及观其《送万季野北行诗》,戒以勿上河汾太平之策,则先生之不可夺者又确如矣。是固论世者所当周详考核,而无容以一偏之词定之者也。 故我们若谓黄宗羲因老而有母,不容尽废甘旨之奉,因此晚节不如早岁之劲尚可,若以是而对其志节抱持怀疑的态度,则不免有厚诬古人之嫌。黄宗羲一生的行事,并非绝无可议者,但若能就其艰难的处境与悲苦的心意,虚心以求,则黄宗羲实为终能守大节而值得我们景仰遵式者也。 ——原发表于1989年11月 高雄中山大学第一届清代学术研讨会 孔子文化奖是由中国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设立的国际奖项,是中国文化部的最高奖项之一,主要表彰对全球儒学研究和孔子文化传播做出突出贡献的团体、个人和非政府组织。本套丛书是自2009年首届孔子文化奖设立以来,历届个人奖获得者的文集汇编,每卷书以“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为核心,以获奖人最具学术创见的观点、概念等为主旨,选录了作者最具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创新性的文章、著述、学术演讲录等。 董金裕——中华文化的弘扬者、推广者。他是来自台湾的知名学者、儒学研究专家,是推动中华文化基础教育卓有贡献的教育家。他研精覃思,博考经籍,致力于儒家文化研究数十年,尤长于儒家经 典和宋明理学的研究,造诣非凡,成果丰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