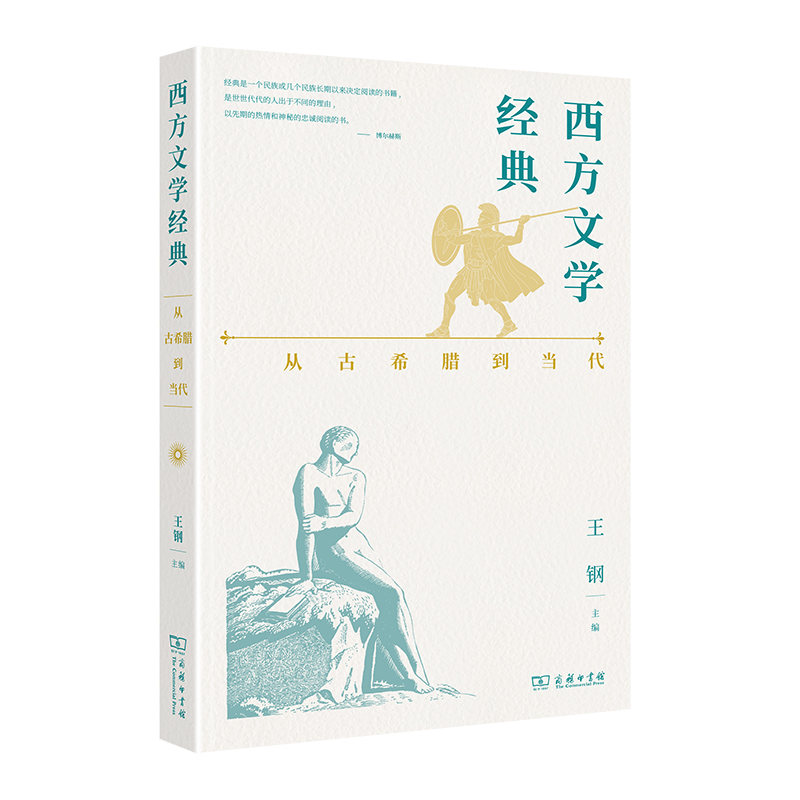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8.60
折扣购买: 西方文学经典:从古希腊到当代
ISBN: 978710021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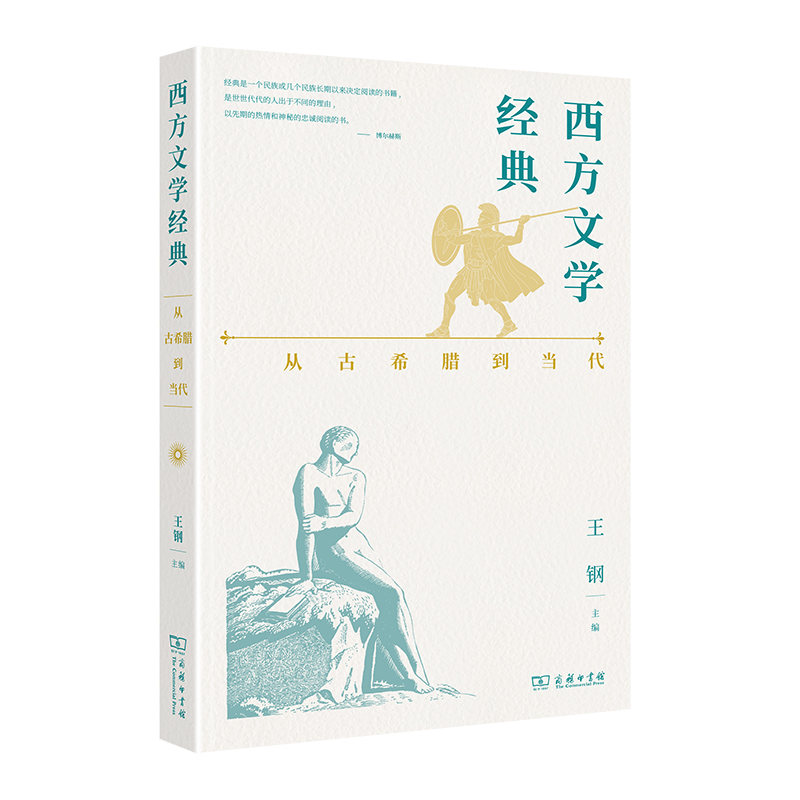
王钢,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外国文学评论》《南京大学学报》《南开学报》《东北大学学报》等国家级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文化诗学视阈下的福克纳小说人学观》《文艺心理学研究》《20世纪西方文学经典研究》3部学术专著,参编国家级外国文学教材3部;主持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吉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2项,吉林师范大学创新基金项目1项,参加教育部等项目多项;完成教育部项目、四平市社科项目、吉林师范大学博士启动项目等多项。获吉林省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省部级)1项,四平市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三等奖各1项。
导 论 (部分) 在现代英语中,“经典”主要涉及三个词汇:classic、canon和masterpiece。classic来自拉丁语词根classicus,是古罗马税收官用以区分税收等级的一个术语,后被引申用来评价作家的等级,逐渐成为“典范”(model)和“标准”(standard)的同义词。文艺复兴文学和17世纪欧洲古典主义文学都以推崇古希腊罗马作家为核心要义,故“古代的经典”观念得以进一步扩展。据《牛津英语大词典》(OED)的权威解释,classic的现代词义主要包括:有价值的、公认的一流作家、艺术家、作曲家、作品或范例,尤其是指古希腊、拉丁作家或文学作品;希腊和拉丁文学学者;古典模式的跟随者以及古典风格的汇总等。canon源自希腊语,原意为“棍子”或“芦苇”,后演变出度量的工具和“规则”等词义,再引申为《圣经》等神圣真理文本,至18世纪逐步确立为文学经典之义。《牛津英语大词典》标注canon的词义主要包括基督教传教士的法律和政令,尤其是传教士委员会制定的规则;基本的法律、规则、原则以及基督教教堂正式采纳的圣经书籍;天才的经典作品。而masterpiece的主要词义则倾向于“杰作”。通过语义学内涵与外延的梳理和比较,可以看出“经典”一词蕴含的基本语义要素:经典与文艺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往往指向文艺的古典风范或传统品格,与欧美文学的古希腊罗马发源以及古希伯来文化发源紧密联系在一起;经典既是典范,也是规则,其存在着自身内在的价值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典的归属。诚如当代美国学者大卫·丹穆若什所言,经典就是“具有超验性甚至奠基性价值的作品”。 一 文学经典是如何形成的?其内在的价值和品质如何?对于这些基本问题,作家和思想家们曾展开过详尽而漫长的论争和讨论。 诗人托·斯·艾略特(也译作“T. S. 艾略特”。后同)曾撰写《什么是经典作品?》的长文来论述文学经典的内在诗学品质:“假如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个词,它能最充分地表现我所说的‘经典’的含义,那就是成熟。……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候;语言及文学成熟的时候;它一定是成熟心智的产物。” 在艾略特看来,文明的成熟是经典形成的必备条件,是经典产生的温床,而这种成熟又往往会反映出生成经典的那个社会的成熟。“成熟的文学背后有一部历史:它不仅是一部编年史或是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手稿和作品,而是一种语言在自己的限度内实现自身潜力的过程。这一进程尽管是不自觉的,但却很有秩序。” 除了“成熟性”,艾略特指出经典作品还必须具备“广涵性”和“普遍性”。所谓“广涵性”主要是指:“经典作品必须在其形式许可范围内,尽可能地表现代表本民族性格的全部情感。它将尽可能完美地表现这些情感,并且将会具有最为广泛的吸引力:在它自己的人民中间,它将听到来自各个阶层、各种境况的人们的反响。”而作品一旦超出本国语言的“广涵性”而“相对于许多别国文学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时”,它便具有了“普遍性”。换言之,艾略特认为经典不仅是民族的、国别的,更为重要的是它必须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而具有世界性价值。 如果说艾略特的经典论主要着眼于民族性、区域性和普遍性的标准的话,那么阿根廷当代作家博尔赫斯对文学经典标准的衡量则侧重于时间和读者的检验。博尔赫斯认为经典应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在这里,“世世代代”很明显是一个时间标准,即文学经典要经受时间的考验。换句话说,流传不够久远的文学作品是不能成为经典的。关于经典的时间性,从古至今被普遍认同。塞缪尔·约翰逊在论及莎士比亚的历史价值时曾指出:“我们不能盲目地轻信昔日的智慧要高于今日,或悲观地认定人类文明在不断倒退,并因此才尊崇存在时间悠久的作品;我们尊崇这些作品,是基于这两个广被认同、无可置疑的道理:人们知道得最久的东西,也是他们最常思量的;他们最常思量的东西,也是他们体悟最深的。”在约翰逊看来,作品经过时间的锤炼被思量和体悟得越深刻,越有利于成为经典,而莎士比亚经典化的历史进程也验证了约翰逊的独到见解。美国当代学者爱德华·希尔斯则明确指出“经典”这一范畴本身就意味着“对文学作品长期以来做过的筛选和评价”,时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形成“某种类似于教规的准则”。而当代德国哲学家汉斯·伽达默尔更是干脆断言当代无经典可言,虽然这一论断未免带有武断之嫌,但足以充分说明时间的考验对于经典的必要性。而所谓“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则涉及读者的欢迎和接受程度问题。关于读者在经典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必须一分为二地加以看待。一方面读者对某部作品接受效果好、喜欢阅读肯定有利于该作品成为经典,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凡是受读者欢迎的作品都是经典作品。通过对读者接受理论的反思可知,读者的盲目性、随意性和不可靠性早已被证明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影响读者选择标准的因素也纷繁复杂。 如果说艾略特、博尔赫斯的观点代表作家心目中的经典的话,那么哈罗德·布鲁姆、弗兰克·克默德等则集中代表了文艺理论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书中详细梳理了经典形成的历史背景、渊源及标准等问题。在哈罗德·布鲁姆看来,当下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落期,究其根本在于媒体的不断兴起,它既是文字衰落的症候,又是文字衰落的缘由。在此背景下,经典问题可以归结为“那些渴望读书者在世纪之末想看什么书”。换言之,在全球化和媒体化时代还有哪些文字作品被保留了下来,这些文字作品凭借什么品质被保留下来。由此思路,布鲁姆提出了他的经典观:一是原创性,“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二是审美性,“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以及丰富的词汇”;三是记忆性,“认知不能离开记忆而进行,经典是真正的记忆艺术,是文化思考的真正基础。简而言之,经典就是柏拉图和莎士比亚;它是个人思考的形象,不管是苏格拉底临死之际的思考还是哈姆莱特对未知国度的思考”;四是经典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经典绝不是“一种统一体或稳定的结构”,经典会存在消亡或不朽现象,这是复杂斗争的结果,“能成为经典的必定是社会关系复杂斗争中的幸存者,但这些社会关系无关乎阶级斗争。审美价值产生于文本之间的冲突:实际发生在读者身上,在语言之中,在课堂上,在社会论争之中”。 哈罗德·布鲁姆以审美的创造性为基础和核心来诠释他心目中经典的标准,并指出这一创造过程既包含历史的传承和影响的焦虑,也包含真正意义的创新:“一位大作家,其内在性的深度就是一种力量,可以避开前人成就造成的重负,以免原创性的苗头刚刚展露就被摧毁。伟大的作品不是重写即为修正,因为它建构在某种为自我开辟空间的阅读之上,或者此种阅读会将旧作重新打开,给予我们新的痛苦经验。” 哈罗德·布鲁姆的审美性经典标准在英国理论家弗兰克·克默德那里为“审美愉悦”所替代。在《愉悦与变革:经典的美学》一书中,克默德避开经典的意识形态的讨论,转而展示出一套与众不同的评价经典的术语,包括愉悦、变革及机遇。克默德指出,尽管愉悦和经典是一对不稳定的搭档,但他仍认为提供愉悦是经典的“必要条件”。克默德赞同捷克批评家扬·穆卡若夫斯基关于审美愉悦的基本看法和观念,强调其有趣并富于启发意义:“为了获得某种美学功能,作品必须能提供愉悦,而且它还必须是新的。穆卡若夫斯基认为这样的作品有价值是因为它们给予了个体某种愉悦;同时,它具有社会的价值是因为在严肃读者的反应中有着共同的元素。”克默德接下来引述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的《文之悦》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观念来具体加以详细阐述并得出结论:“我们是‘受自我的灵魂’所崇拜,因此,我们就能够宣称我们有能力赋予词语或音符或色块(都只是对象)以艺术的荣光。如果对象不能为我们提供愉悦,无论它有多可怕,多令人沮丧,我们也无法这样做。” 克默德提出“愉悦”是经典的核心问题的同时,也指出变革同样是经典的核心。在克默德看来,变革是文本自身的需要,“因为仅仅那样就足以把它们从其他可能的命运—也就是说,最终成为垃圾的命运里拯救出来”。他还结合文学艺术接受史中的但丁、波提切利、卡拉瓦乔和蒙特威尔第等作家和艺术家经过变革被重新认识和发掘的实例来强调经典正是在变革中形成的。克默德还进一步提出了经典变革的历史性问题,指出“经典的变革反映了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文化的变化”,在此意义上经典便转化成为“关于我们历史性的自我理解是如何形成、如何修正的记录”。 除上述作家、文艺理论家的代表论述外,文学经典内在品质的讨论还广泛涉及经典与传统、经典与性别、经典与后殖民主义以及经典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话题。可以说,文学经典的论题俨然成为当今最为重要的“学术事业”之一。 ………… 引领读者快速入门西方文学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