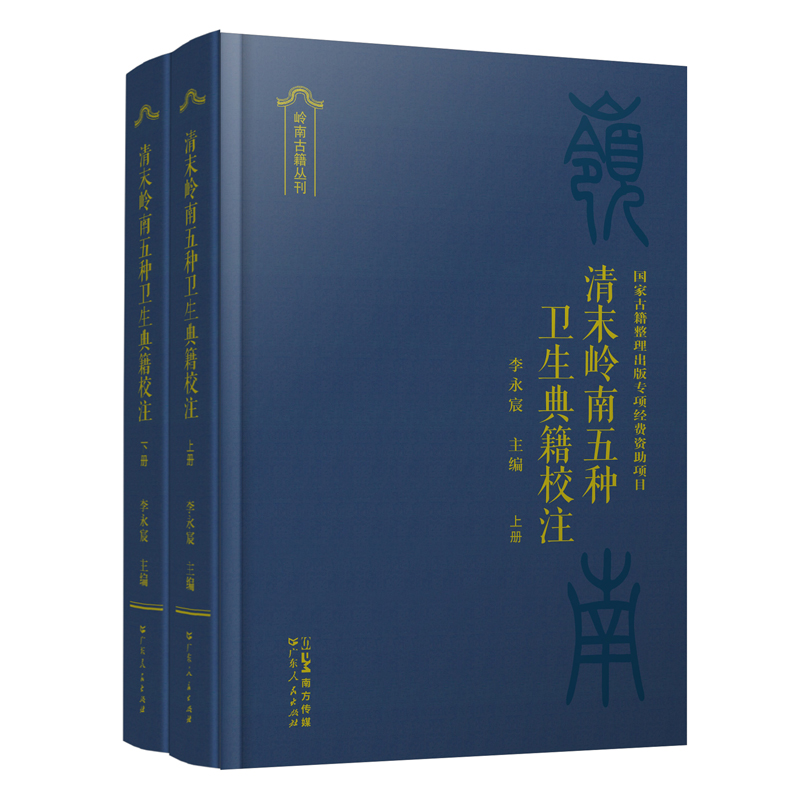
出版社: 广东人民
原售价: 248.00
折扣价: 156.30
折扣购买: 清末岭南五种卫生典籍校注
ISBN: 9787218161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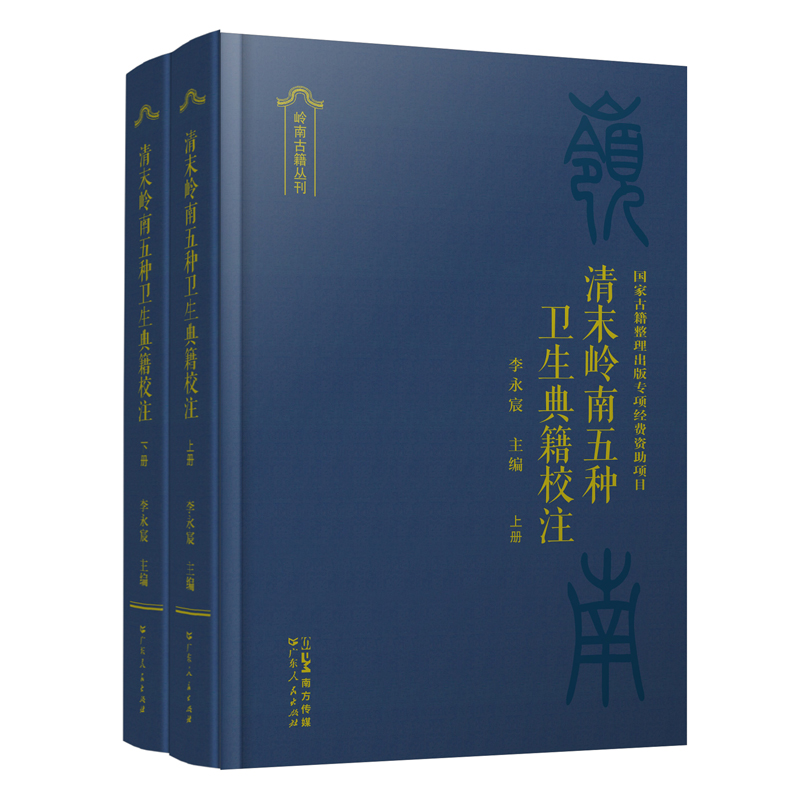
李永宸,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医医史文献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广东省医学会理事与医学历史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文分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近代公共卫生、瘟疫流行史、近代医家医案研究,以疾病医疗社会史与中医临床文献为研究方向,代表性专著《岭南瘟疫史》(与赖文合著)、《李廷安年谱长编》,《岭南瘟疫史》获广东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3等奖与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研究特等奖,副主编全国高等中医院校规划教材《医古文》。
清末岭南五种卫生典籍学术思想(代序) (摘录前两部分内容) 《广州大典》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广州历史文化史料著作的集成”,首次突破四库系列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框架,收录了《卫生要旨》《中外卫生要旨》《学校卫生学》《卫生指南》《卫生至宝图说》五种卫生典籍。五种卫生典籍涉及近代西医卫生内容,与《岭南卫生方》等古代治瘴养生著作不同,是近代西方公共卫生思想与中国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运动在医界的反映与中国传统“治未病”思想的延伸和发展。 清末岭南五种卫生典籍具有鲜明的中西汇通特色,既注重传统中医方剂在人口繁衍、疾病防治中的作用,又体现西医优生优育思想;既重视小儿家庭护理,又关注学校卫生与体育锻炼之于小儿健康的影响;一方面继承传统慎居处、节饮食的中医“治未病”思想,一方面又认识到择偶关系到夫妻幸福与种族康强。五种卫生典籍大都肯定中医的价值,主张以西医补中医之短,编译者具有中医学基础,又有学习西医的经历。“中西医学各有专长,近数十年来,泰西医学流入中国,华人染病,往往有中医皆穷于术,延西医治之,恒奏奇效。盖西医治证,诚有足补中医之不及者也。然非先通中医之理,而但学西医,则亦时有偏蔽之患。” 一 “卫生”一词始见于《庄子》:“卫生之经,能抱一乎?”意为“养生”,中国近代以前中医典籍之“卫生”多为此义。 “养生”是“研究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理论和方法”,是“人类个体有意识的自我调养身心、保养生命的一类自主性活动”。“养生”本质上是保养元气。“卫生”概念的内涵比“养生”丰富。当“卫生”作“养生”时,含义有三:与“伤生”相对,即“卫生”是保卫生命,而不是伤害生命;与“医”相对,即“卫生”常指预防疾病,而“医”则指治疗疾病;专指生理上的保养,常与“养性”或“养心”相对。此外,“卫生”还包括“医药医疗”“卫生保命”“济世救民”。 “卫生”作为近代新名词传入中国时,时人没有沿用传统意义的“养生”,而使用“卫生”。其原因有三:一是现代卫生行政制度已在欧美、日本建立起来。与此相应,1905年,清政府在巡警部设立卫生科,“卫生”已成为现代化与时代进步的象征。二是传统“养生”的“保卫生命”“预防疾病”内涵,已经无法涵括卫生行政、制度管理、公共卫生等新内容。三是近代“卫生”与“种族康强”“国之盛衰”紧密相关,甚至把近代中国人口增长出现停滞,归结为“中国男女,迩来不讲卫生”。因而,近代“卫生”一词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内涵:“它是光绪以降在西方卫生知识的传入、日本近代的‘衛生’(eiseyi)用语与卫生制度的引介以及中国士人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利用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与hygiene对应的现代概念的。”“‘卫生’一词被纳入国家正式行政机构名称之中。” “‘卫生’包括了管理医疗活动的行为”“(卫生)成了追求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环境的专门学问”“(卫生)涉及社会乃至民族国家的公共事务”。 二 清末,西学日渐溶入中国社会,“洋务运动使近代科学和技术成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部分,是促使中国社会从封建向现代转折的重要力量”。洋务人士开办具有现代意义的制造局,同时翻译各类西方科技著作。“海禁既开,外侮日亟,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同时同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会于中国者,相继译录。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所译之书,包含不少医药学著作。《广州大典》收录了这一时期二十种西医西药学典籍。 清末岭南五种卫生典籍成书于1882—1906年间,这一时期,一方面,中国受列强侵略,经历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反对八国联军的战争,民族矛盾空前激烈;另一方面,朝廷与地方大臣推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爱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五种卫生典籍频频出现“公益同胞,救吾同种”“种族康强”“国家之强弱,国力之消长”“民种魁伟,国富兵强”“国之盛衰”等强种、强国词汇,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五种卫生典籍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在医界的反应。郑观应受到中法战争失败的刺激,主张建立新式学校,“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其医学教育“不分中外”的思想在《中外卫生要旨》中得到充分体现,“余阅海昌王君士雄所纂《随息居饮食谱》,有益于卫生者不浅,爰复将西医格致卫生之理补入,以备卫生者考察焉”。受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与穗港鼠疫大流行的影响,江英华“纂集《卫生指南》一书,出而问世,实欲公益同胞,救吾同种。深望阅者,通达卫生,遵守其法。虽曰不能尽免危亡,或可藉此补救于万一,从此种族得而康强,同享益寿延年之幸福”。落后的卫生状况导致近代岭南疫病频仍。岭南879年至1911年共有年代明确的疫情记录991县次,其中光绪(1875—1908)、宣统(1909—1911)年间的37年内,共有疫情记录645次,占全部岭南古代疫情记录的65.1%。1894年穗港鼠疫流行,“省会毙于此劫者,不下10万余人,其间贫苦者居多,大都因其饮食不佳,房屋狭隘之故”。《申报》亦报道1893年广州的卫生状况,“城厢内外,人烟稠密,各街道粪草垃圾堆积如山,一至炎天,秽气熏蒸,闻之易生疠疫”。1894年以后,岭南疫情不断,疫死者众。“比年以来,疠疫流行,传于各埠,朝发夕亡,不可救药。计自甲午至今十余年来,未之或息,白杨瑟瑟,类多惨死之魂,荒冢累累,半是疫亡之骨。触目伤心,曷其有极。呜呼!天之虐待斯民,顾如是哉!然要非天之故为虐待也,实人之不自卫其生,有以致之也。”染疫而死者华人远多于西人,“近见天灾流行,历年疫症不绝,遭此不幸,西湾之青冢累累,逢此危亡,南山之白坟叠叠,兴言及此,谁不伤心。又即年中,染此症而丧命者,中西相较,华人每居十之七八,而西人仅得十之二三”。 清末瘟疫频仍,既有“天之虐待斯民”的自然因素,更有“人之不自卫其生,有以致之”的人为因素。染疫而死者华人远多于西人,其原因为“西人之所幸免此灾者,总因卫生有法,善顾卫生,而华人常多不知卫生,每视卫生之例为畏途”。 中国人口居世界之冠,“中国四万万人之数,其说始自乾嘉之时”。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口应在10亿以上,然而,近百年来,中国人口仅增长2000余万,卓凤翔把这一百年中国人口增长出现停滞归于“中国男女,迩来不讲卫生”。“中国四万万人之数……迄今已越百年,以理论之,当一衍而为四五,是中国今日之人数,当在十余万万以上矣……李文忠通饬各省,一律统查,合东三省计之,于四万万外,所增只二千余万,是此百数十年中,生民之少,实出人意料之外。虽盗贼水旱疾疠,近三四十年内,人之死亡者,不可数计,然亦何至欲一衍为二而不可得?推原其故,盖由中国男女,迩来不讲卫生,有以致之也。” 一百年后的人口史研究印证了卓凤翔的推测。自咸丰元年(1851)至宣统二年(1910),战争、灾荒与瘟疫使中国人口的增长停滞了六十年之久。 至于广东人口,经历顺治、康熙、雍正朝的缓慢发展和乾隆年间的大发展,以及嘉庆、道光年间的持续增长,至鸦片战争前的道光十九年(1839),已达22864万;自鸦片战争以后,社会环境出现剧烈动荡,各地灾害接连不断,人口增速明显下降。从道光二十年(1840)到1911年内,年平均递增率由鸦片战争前的181%降至033%;加之吸食鸦片、卖淫、赌博成风,在1800—1849年间,广东人口平均寿命为男性337岁,女性388岁,可见早夭也是人口增长放缓的原因之一。到了20世纪30年代,人口年平均增速进一步降至0.28%,呈明显的停滞状态。 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有清一代,岭南与海外交往最为频繁,西方国家最早在此地建立医院。鸦片战争后,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国家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的医院如雨后春笋。据王吉民考证:第一所天主教医院(澳门,1569年)、第一所基督教医院(广州,1835年)、第一所外人在华的施诊所(澳门,1820年)、第一所私立医院(澳门,1827年)、第一所麻风医院(汕头,1867年)、第一所中西医院(香港,1872年)、第一所精神病院(广州,1898年)均设立于岭南。医学传教士培养本土西医,形成了新医群体。他们或著书立说、或翻译西医著作,形成了数量可观的早期西医著作。《广州大典》所收录外籍寓贤医籍,不仅包括外籍名人寓居广州期间所撰写或翻译的医学著作,也包括广州人翻译的外文医籍。据统计,《广州大典》所辑外籍寓贤医籍共二十种,以博济医局和博医会出版,以及嘉约翰及其华人学生单独或共同编撰、译述者为最。它们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与自强自立运动在医界的反应。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研究发现“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最多,由教士多业医也”。 儿童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学校卫生的普及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粤人周起凤所译《学校卫生学》是“我国首次完整翻译外文的学校卫生著作”。该书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国运之盛衰系之”,欧美各国,国富兵强,是因为“数百年以来,注意体育,儿童有坚忍不拔之气象,敏捷锐迈之智识也”。因此,“学校卫生者,国民之强弱系之。学校卫生之普及与否,国家之强弱、国力之消长应之,岂非教育之基础哉”。中国公共卫生的重要先驱李廷安站在国家民族与生存竞争的高度,来认识学校卫生的重要性,指出“欲求国家之强盛,须先有健全之民族,而健全民族之培植,宜从学童入手”。李廷安将学校卫生的重要性概括为三点:第一,欲求国家之安存,先须有健强之民族。而健全人民之培养,宜从青年入手。因此学校卫生之重要,皆为列强政治大家所公认。第二,学校卫生为必须事项,例如儿童健康之养成,校内传染病之预防,校舍之卫生设备,卫生教育之实施等事,皆不能忽略。第三,公共卫生为一经济问题。教育卫生机关有完善之学校卫生设备,学生疾病自然减少。种种因病而起之损失均能挽回。 近代以前,“卫生”一词之义是通过调饮食、慎起居、适寒温、节喜怒等方式,达到身体健康、延年益寿的理论、方法,与“养生”义同。杜志章将其内涵概括为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养性养心、医药医疗、卫生保命、济世救民。近代“卫生”的外延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养生”的概念,而是与国家、民族发生紧密联系,赋予了“保种”“强国”的内涵,甚至将近百年中国人口增长出现停滞的原因归于“中国男女,迩来不讲卫生”,国人体弱是因为“未知卫生之法”,如果国人明白“卫生之理”,讲究卫生,“则中国无弱民,而中国且成为强国”。可见,“卫生”一词含义的变迁与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疾疫流行、人口增长停滞、西学东渐、健全国民的培植等社会历史背景密不可分。五种卫生典籍的产生既是民族救亡运动在医界的反应,也是西方公共卫生理论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相结合、中西医两种文化碰撞的产物。 …… 第一,五种卫生典籍成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产生与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疾疫流行、健全国民培植等社会历史背景密不可分,与国家、民族强盛联系在一起,是近代中国民族救亡运动在医界的反映。 第二,近代“卫生”不是传统的“养生”,是中西医两种文化碰撞的产物。研究五种卫生典籍对于探讨“卫生”一词含义的变迁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分析卫生行政管理思想的产生、发展,比较中外卫生思想的异同等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具有鲜明的中西汇通特色。既涵盖中医传统养生思想、经典中医方剂,又涉及环境、学校卫生、卫生制度、生理生化等西医卫生内容,内容丰富。 第四,较强的现实性,契合当下需求。五种卫生典籍中的传染病防治方法、卫生理念、预防养生等内容为当下提供具有借鉴价值的回顾性史料,有助于增进个人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第五,书中所载中医知识,继承传统中医药智慧,有助于全面了解与客观认识中医养生学说、疫病学说、方剂学说的历史价值,丰富中医相关学科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