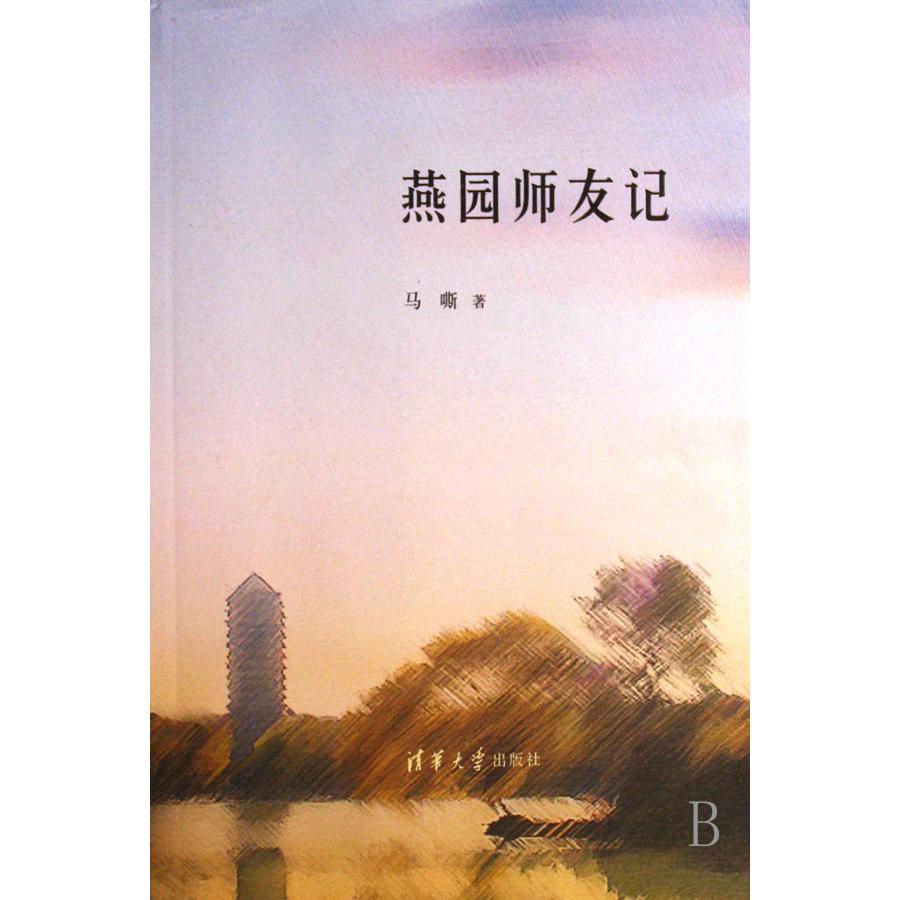
出版社: 清华大学
原售价: 29.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燕园师友记
ISBN: 97873021668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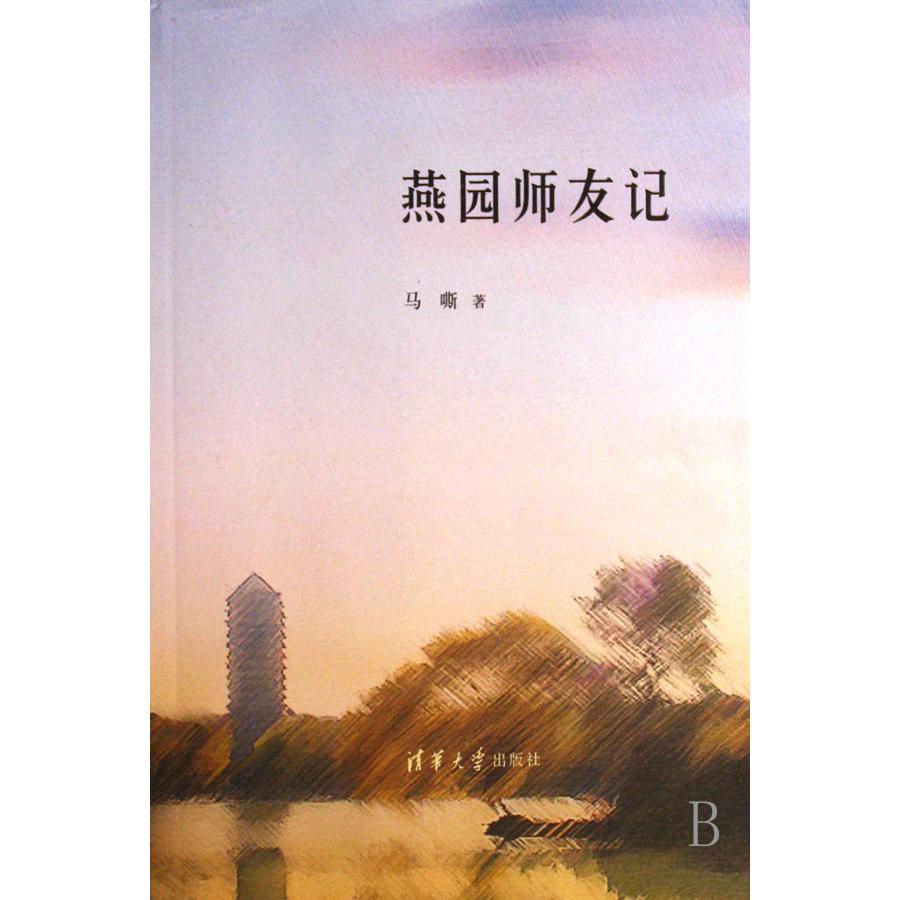
马嘶,1934年生于河北唐山,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长期从事文学创作、评论和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燕园师友记》、《负笈燕园》、《紫骝斋文学论评》、《学人往事》、《百年冷暧: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1937年中国知识界》、《一代宗师魏建功》、《往事堪回首一百年文化旧案新解》等十余部。
建国初期,“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几位文学巨匠依然活跃在文坛上 ,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谢冰心等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作家, 如浩瀚星空中的几颗璀璨夺目的星座,放射着奇光异彩。他们当中,最为 贴近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影响最大的要算是冰心先生了。每一个人,从少 年时代就知道了她的名字,没有一个没有读过她的《寄小读者》和隽永的 小诗、短文,也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像热爱母亲般地热爱着她。 来到燕园之后,我们就听说,二三十年代,冰心先生曾在幽僻的燕南 园里居住,她的《南归》等作品就是在这里写出的,在《南归》的稿末, 明明就有“1931年6月30日夜,燕南园,海淀,北平”的字样。被好奇心驱 使着,我曾经偷偷地在燕南园里寻找她当年的居住之处,但由于无人指迷 ,我终未能找到。我也曾在从燕南园通往未名湖的小石径上,忽发奇想地 去寻觅她当年走过的足迹。我想象着,她也会是像如今的周培源、冯友兰 、侯仁之几位先生那样,常常在这儿走来走去。当然,这不过是天真幻想 。 班上的同学们常常谈论起冰心先生,都有意去拜访她,听说她就住在 离北大不远的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住宅楼里。她的爱人吴文藻先生任中央 民族学院教授。 1955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我们七八个同学邀集在一起,终于到冰心先 生家中去了。我们是在事先并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去拜访她的,我们似乎谁 都没有想到这是不太礼貌的行为。就如同去到住在校园里老师们家中一样 ,想起来,拔腿就去。冰心先生住在极普通的一栋灰色住宅楼里,我们按 照了解到的地址,贸然敲响了她的房门。门开了,一位身材瘦小、衣着朴 素却又神清气爽的中年妇女站在面前,极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客厅里。当我 们认出这就是渴慕已久的作家时,那欣喜之情是难以言状的。 客厅很宽大,也很朴实,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我立时联想起她曾住 过的燕南园别墅式小楼,虽然我未曾找到,但可以想象得出,这里的环境 同那里相比,肯定是逊色多了。 那一年,冰心先生是55岁,清瘦而干练的身子,很结实、硬朗,慈祥 的面孔上老是带着温和的微笑,让人感受到一股烘烘的暖意。她的手中还 拿着一团毛线和竹针,她正在织着毛线活儿。看到这些,我立时感到像是 回到了母亲跟前,敲门时那种胆怯和拘束顿时烟消云散。我们也立时感觉 到,这正是我们心目中的那个冰心,这正是我们从她的作品中了解到的那 个冰心,那个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贴得很近的冰心。 我们本没有明确的访问目的,也没有具体的访问计划,我们只是想同 她见见面,随便谈谈。因而她的谈话也就非常随便,像朋友们会在一起拉 家常。我们随随便便地坐在长条沙发上、椅子上。 她谈北大,自然而然也便谈到她的母校燕京大学(她原在协和女子大 学读书,后协和女大并入燕京大学),因此她把自己引为北大校友,这样 ,我们更感亲切了。她问起北大一些教授们的情况,在他们当中,有不少 是她的朋友和旧相识,谈话中,她不免讲起他们的一些旧事。她问我们住 在哪些宿舍,她知道,原燕京大学的学生宿舍早已不敷使用,又盖了不少 新宿舍。她说,她的儿子是清华建筑系毕业的,北大有几栋简易的学生宿 舍楼是他们在校时设计的,那些宿合设计得有很多缺陷,住进去很不舒服 ,屋与屋之间的隔墙很薄,又不封顶,根本不能隔音,大家都有意见。她 说,她的儿子为此都不愿从那宿舍前走过,说得大家笑起来,她对日常生 活中的这些琐事记得颇为清楚,可见她是个关注生活的作家。 正谈得兴浓时,冰心先生忽然问我们:“你们每个人都有外号吗?” 她的话把大家问乐了,大家立时活跃起来,她接着就挨着个儿问:“你的 外号叫什么?”“你呢?”大家七嘴八舌地回答着,引起阵阵欢笑。她接 着又说:“许多人都有外号,叫外号倒感到亲切。”她说,前些时,她同 夏衍等人出国访问,大家都叫夏衍“老乌鸦”,他自己也默认,叫他“老 乌鸦”他就答应。冰心先生这样同我们随随便便地交谈着,手中还不断地 织着毛线活。这样,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就缩小了,我们平等地交谈、说 笑,那气氛活跃而谐和。她仿佛就成了我们当中的一员,有话也愿意同她 讲,没有一点隔阂和拘束。我们对她的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善于与人接近的 本领颇为折服。 后来,她又谈起了她的早期创作,谈《春水》、《繁星》、《寄小读 者》的写作情况,我们也提出一些问题请她谈,那都是在读她的作品时所 遇到的问题。我在少年时代读她那篇小说《寂寞》,心中就有一种怅然若 失的感觉,我便把这种情况向她讲了,她听了只是笑笑,说:“人都是喜 聚不喜散的,何况又是少年时代。”她似乎不大愿意回答诸如“那一篇怎 么构思的”、“这一篇的创作冲动是如何引起的”之类的问题。对于她, 创作仿佛是生活中极其自然的事情,是心灵的自然袒露,感情的自然倾泻 ,也是她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为什么目的来写的,更 不是为了当作家才去写的。而她,倒是极其关心各种各样的生活,愿意听 别人讲各种各样的事情。她总是询问如今的大学生怎样生活,同学之间是 怎样一种关系,还问起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状况。通过与她的交谈,我们进 一步理解了我们从少年时代起就热爱着的这位作家,她似乎从来也没有想 到过要专门写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来达到什么预想的目的,完成什么计划 ,而是对她所关注的生活发表一些感想。她生活着,因而她写作着。也许 正是因为如此,她的心才同读者贴得那么近,她才能够同读者心心相印。 她从没有板起面孔发表过议论,她只是与人们亲切地絮语、交谈。这就是 冰心的个性。 从这间小客厅的一扇窗子,我看到了在另一间屋子里工作着的吴文藻 先生的身影,他似乎身材魁梧,戴着眼镜,胖胖的脸。这使我想起了在冰 心作品中常常看到的那位“藻”,那位与他相濡以沫的著名人类学家。 黄昏时我们才结束了交谈。从冰心先生家中出来,大家似乎都心满意 足,人们热烈地谈论着她,也交流着心中的愉悦与所得。更为难得的是, 每个人似乎都重温了一次母亲抚爱的幸福。 P4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