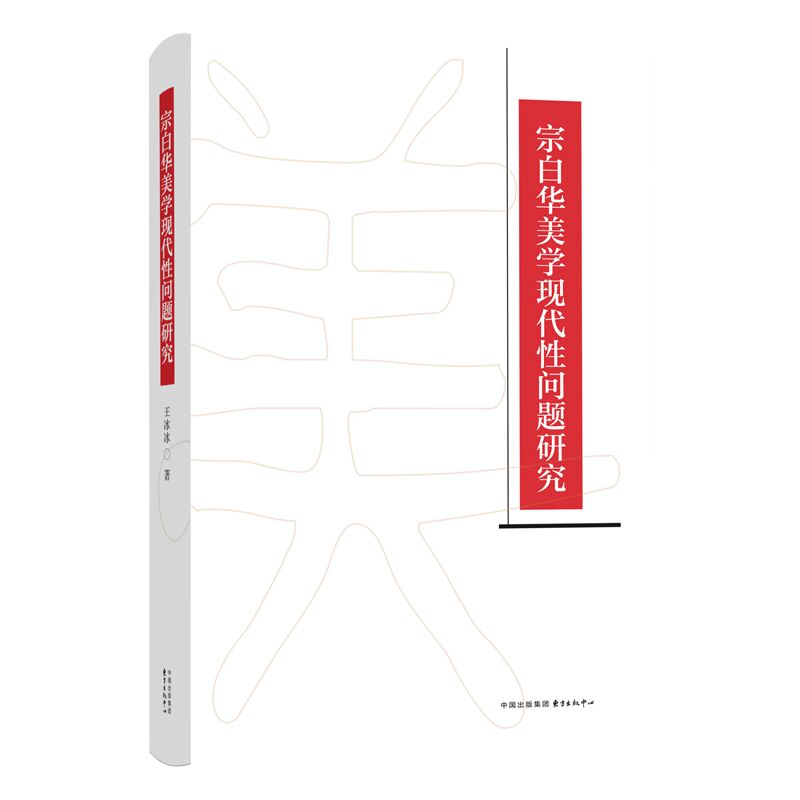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原售价: 89.00
折扣价: 57.00
折扣购买: 宗白华美学现代性问题研究
ISBN: 9787547322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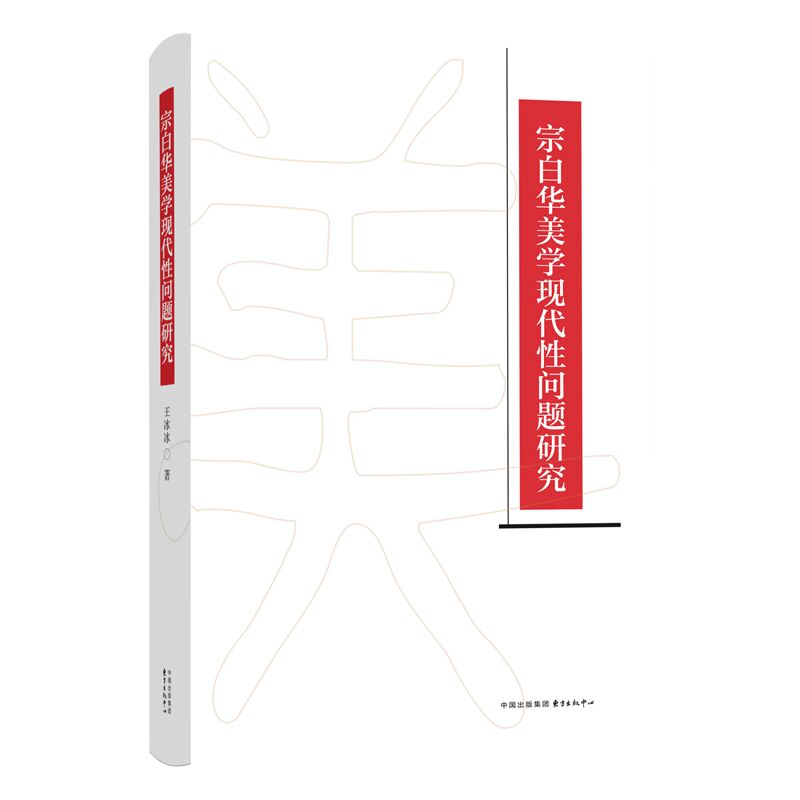
王冰冰,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江苏省“双创”博士。主要从事中西方现代美学理论研究与批评,先后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项,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新文学史料》《学术前沿》《宁夏社会科学》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作为一个舶来语,我们需要首先弄清“现代性”一词在中国文论话语中的引介与接受过程,以之作为宗白华美学研究的历史背景,这将有助于我们纵向考察宗白华美学与中国美学的现代性问题。在学术史上,一般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概念最早出现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中,是最近的十几年刚造出来的新的概念,李欧梵先生就取这种观点,并推测它可能源于詹姆逊1985年在北大做演讲时,连同“后现代”一词一起被介绍到中国的。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关注事实上远远早于这个时期。根据前辈学人考证,周作人、卢勋、袁可嘉等中国早期的文学批评家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就通过翻译外文将“现代性”这一术语引入中国。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的十七年里“现代性”更是被反复使用,有学者指出,仅这段时期国内发表的译文就有12篇,并全部译自苏联。 改革开放以后至今,“现代性”的使用情况则自不用多说了。 1918年1月,周作人发表的第一篇译文《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最先将“modernity”译为“现代性”并引入中国文艺批评话语,原作者是英国小说家W.B.Trites。文章中写道,“现代性是艺术最好的实验物,因为真理永远现在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近来复活的原因正是由于它“非常明显的现代性”。 一是陀氏小说中“深微广大的心理研究”,与当下蔓延的最新的文艺思潮——精神分析美学相契合;二是陀氏善写下等堕落人的灵魂,但这些“最下等、最污秽、最无耻”的像抹布一样存在的灵魂,仍然是道德与罪恶并存,悲哀但又极美,这种审美倾向明显区别于单一的理想化的古典审美风格,这是陀氏著作的精义所在,也是其小说仍具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周作人在文后译者按中写道,尽管《罪与罚》的心理描写极为精妙,“然陀氏本意,犹别有在。罪与罚中,记拉科尼科夫跪稣涅前曰:‘吾非跪汝前,但跪在人类苦难之前’。” 可见,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学人来说,文学现代性的关键在于对“人类苦难”的描绘,以唤醒蒙昧与黑暗的社会。在同一年的《新青年》杂志第5卷第6号上,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明确提出他的美学主张,“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而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新文学的提倡,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灵肉分离的非人的生活。也许周作人对“现代性”概念的翻译与使用是不自觉的,但这显然绝不是个人的喜好,而是时代使然,作为个体的“主体”之觉醒使得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更加迫切地需要“现代性”的变革。 直至1948年,中国学界出现第一篇明确以“现代性”命名的理论文章为《释现代诗中底现代性》(What is Modern in Modern Poetry?),它由中国新诗理论家、现代派诗人袁可嘉翻译,发表于1948年《文学杂志》第3卷第6期,原文作者是英国诗人Stepher Spender。这篇译文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文组与国内《文学杂志》的交换稿件,斯彭德喜欢用现代化的意象来表现社会问题,这篇文章便是围绕此问题展开。在这里,“modern”被用来否定自身,文中认为“modern”并非仅仅是指时间意义上的当代,不是一种时态性的概念。“modern”是作为一种目的而存在的,是现代诗人的一种追求。但作为目的而存在的现代性是会逐渐“过时”的,于是对“过时”的现代性就有了反思与批判的可能。文章中所说的“诗的现代性”即是指肇始于19世纪中期法国象征主义以来的各现代主义艺术流派,他们运用“特殊的写作手法”来描写“特殊的题材”。但斯彭德在文章的末尾又强调,并不是说采用心理描写,抑或使用如蒸汽机、汽车、电话铃等这些具有现代特征的意象就是现代诗。斯彭德指出,他所描写的现代性不是为了展示那些时髦的东西,而是企图将人的内在世界的感受放置于当下的某种关系中。也即是说,形式的革新和现代意象的引入是为了引起人们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只有反思当代人的生存景观,发掘现代人与当代世界关系的感受与情绪,诗才具有现代性。这种现代经验是传统诗人们所没有的。李欧梵先生在《上海摩登》的序言里也曾说道,“没有巴黎、柏林、伦敦、布拉格和纽约,就不可能有现代主义的作品产生。” 鲁迅也曾将这些现代主义诗人称为“都会诗人”,指出他们用“诗底幻象的眼,照见都会中的日常生活,将那朦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在尘嚣的市街中,发现诗歌底要素。” 在斯彭德那里,他进一步指出,这些现代工业文明的结晶体将我们组织成生活的工具,并夺取我们的人性。由此可见,这篇译文表明在中国学界事实上早已开启了对“现代性”内部矛盾的学理性思考,但紧随而来的国内形势的变化中断了这一研究趋向。受苏联文艺美学的影响,“现代性”被赋予新的内涵,从批判转向建构,成为“人民性”、“革命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的代名词。 本书系统阐述了现代性概念在西方哲学体系中的萌芽嬗变的过程和相关各种思潮,及其在中国引发的超过一个世纪的解释和讨论,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宗白华美学哲学体系中的现代性问题,分析了宗白华不同时期的思想观点,并结合他独特的中西比较视角、扎实的中西学术功底,关照近代中国的民族命运,对其深厚且独树一帜的中华性美学思想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做出了深刻的解释,使关于宗白华美学思想体系的研究焕发了新的时代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