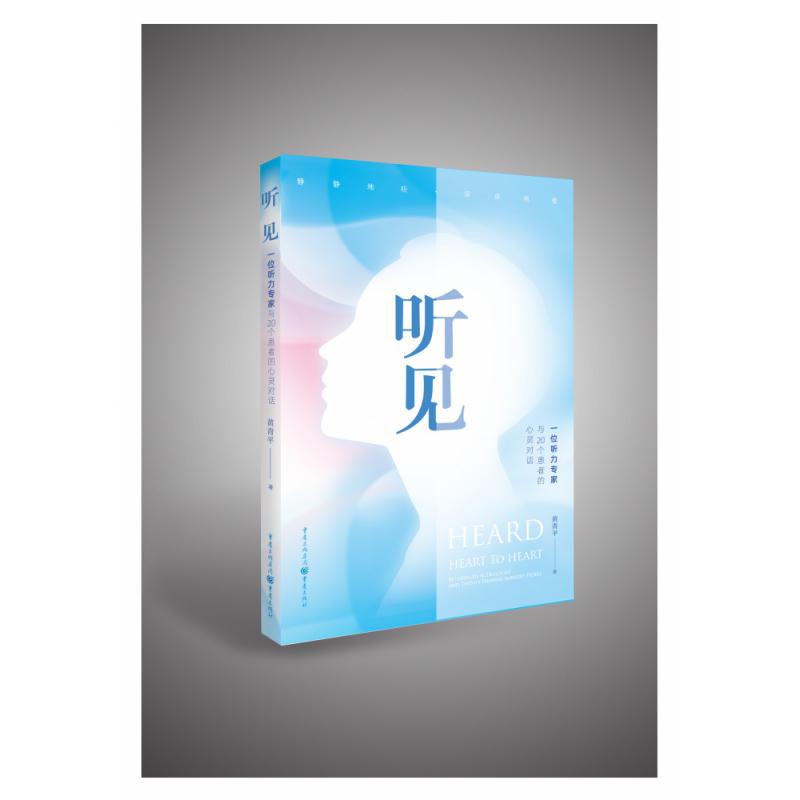
出版社: 重庆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29.80
折扣购买: 听见——一位听力专家与20个患者的心灵对话
ISBN: 97872291575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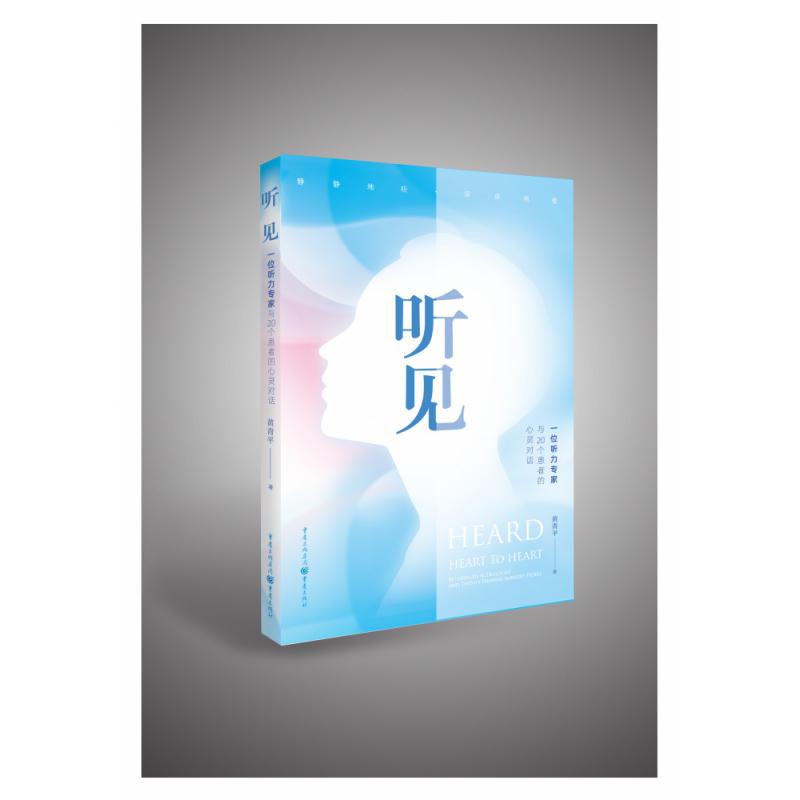
中国康复医学会听力康复专业委员会 常务委员 卫生部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助听器验配培训师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助听器专家委员会 委员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 考评员 职业技能竞赛 裁判员 《助听器验配技术指南》草案 撰稿人之一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耳鼻咽喉科 高级听力师 从事耳鼻咽喉科临床听力中心工作20余年,开展助听器门诊从建立到健全,为耳科学和听力学在助听器验配上的应用积累了丰富的一线经验;擅长 一对一为老人及成人助听器个性化验配;.对耳鸣的声治疗有较深入的探索;擅长将结合儿童的心理生理特点,做到安全、精准的听力检查、 助听器验配及康复效果评估;尤其擅长将专业的理论知识深入浅出地运用在培训宣教工作中,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创新突破。
没想到,她竟然愿意让我抱。 雯雯,出生两天时,新生儿听力筛查未通过,半岁开始戴助听器,从发现听力问题到进行听力康复,整个过程符合目前听力康复规范要求,一步步融入有声世界。 小女孩今年一岁半了,其实挺有个性的,不太爱说话但啥都能听懂,常常用眼神表达情绪,来我的门诊待几个小时,其间不哭不闹,一直关注着我们的交谈。 一开始她并不亲近我,只偶尔瞄我一眼,雯雯妈妈说她很认生,连亲舅舅都不让抱。雯雯颇有兴趣地不停地按计算器的数字键,计算器播报“2、6、7、9……”。 妈妈说,她在家就喜欢玩这些有声玩具。后来我把我女儿小时候玩过的玩具小钢琴放到办公桌上,弹了一曲《世上只有妈妈好》,雯雯妈妈在旁边跟着哼唱起来,雯雯的眼神开始转移到我的手指上。她一边慢慢地伸出小手拍击小钢琴的琴键,一边悄悄地看我,她开始亲近我。 但我真不知道她会主动伸手让我抱。直到我抱着她离开了妈妈的视线,小女孩的头温顺地靠在我的肩上,我才相信自己已经得到她全身心的信任,这让我的心也变得柔软起来。 临走时,一直不肯开口说话的雯雯,挥动着小手竟然清晰地连连说了好几遍“谢谢”“拜拜”。那一瞬间我仿佛听到了天籁。 “平时在家就喊她雯雯吗?” 多接触有声世界,多带她去正常人群中听听交谈声,待在安静的屋子里不利于孩子语言的建立。” 妈妈欲言又止,隔了好一会儿才说,她是小学语文老师,早上出门时孩子还在睡觉,一周里最多三天可以中午回家陪孩子睡个午觉,原计划晚上下班陪陪孩子、讲讲故事,但后来时间紧张,也没有做到。大多数时候是奶奶帮忙照顾雯雯,但是奶奶年纪也大了,不怎么喜欢带孩子出去。“想着孩子不能不听声音,我还买了一个天猫精灵,给她放儿歌、放《三字经》,让她可以一边听一边坐着玩。” 雯雯在地上坐着玩玩具,玩得高兴了还兴奋地叫几声。 “她精力真好。”我感叹。今天她们一大早就来医院排队复查听力,现在都大下午了,雯雯一直没有睡觉,我让她在休息室里睡一会儿,但是小女孩十分亢奋,把我办公室里的有声玩具反复折腾,一点儿睡意也没有。 “她很喜欢听这些声音,每次都玩得很投入,她有个螃蟹玩具可以发出声音,她总喜欢放到耳朵边上去听,或是看螃蟹的眼睛骨碌骨碌地转。”妈妈说。 听到我们在谈论她,雯雯朝我们挥手,抬手时拉扯到助听器的护理绳差点把助听器扯掉,助手正准备给雯雯戴上助听器,我示意说:“你把助听器拿走,看看她的表情。”我想借机观察小女孩的神情,如果能激发她开口说几句就更好了,目的是了解孩子现在发音的准确度。 雯雯的表情变得闷闷不乐,抿着嘴跑到妈妈怀里,但依旧没有开口。 我叮嘱助手检查一下雯雯的耳道和耳模①。孩子半岁以后耳朵发育得很快,雯雯一岁多时耳朵长大了,耳模就不密闭了,重新印制过一副新的耳模。 “一岁以后,她更喜欢说话了,虽然她说的有些话我们听不懂,但她还是喜欢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了,但简单的姐姐、爸爸妈妈、奶奶喊得很清楚了。”雯雯妈妈笑着说。 “她听得懂你们说的大多数内容吗?”我问。 “是的,每次我都叫她自己去扔尿不湿,现在都养成习惯了;叫她帮忙丢垃圾、拿个手机她也愿意;有时候电话响了她也会提醒我们。” 李志鹏总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 他第一次独自来我的门诊,从进门到离开,一个小时左右,脸上都挂着笑。哪怕说到因为听力下降,前妻跟他离婚,同事对他风言风语,学生在背后议论,他脸上都没有流露出一丝黯淡。 跟别的患者不一样。 一般来我们诊室的病人,都是带着愁容、病容,他却笑嘻嘻的。铮亮的脑门上斜着几根头发,光溜溜的脸颊上戴着一副细边眼镜,整个人显得很有光彩。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 别的病人说病史,都是医生问一句,病人答一句。他说起病史来,滔滔不绝,似乎打了腹稿,医生想知道的,他大都说到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小学副校长,四十三岁。 他的听力障碍是由中耳炎引起的,中耳炎病史长达四十年。 他说:“小时候经常到小河、水库里洗澡,有时候呛水了,脏水进入鼻子,引起鼻子发炎,类似于感冒症状。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也没重视,没得到治疗。刚开始不严重,后来鼻炎反复发作,又引起耳朵发炎。耳朵几乎每年要发炎好几次。” 但是中耳炎一直未引起他的重视,却不知慢性炎症就像温水煮青蛙。小时候耳朵发炎只会让他有一点点不舒服,时间久了,慢慢地身体似乎习惯了这种不舒服。后来耳朵里有水流出来,但耳朵能听见,他也没管。疾病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继续侵蚀着他的身体,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后果。又过了十几年,情况开始恶化,他说耳膜穿孔 了,耳朵经常流脓,导致听力逐渐下降。直到他从师范大学毕业后,当了老师,也有了收入,自己才第一次到县医院就医。那时他发现自己的听力已经明显减退了。这给他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前妻跟他离婚了,升职也不指望了。有人建议他戴助听器,但他还不想戴。他心里对恢复听力抱着一些希冀,他听说手术可以治疗中耳炎,就想试试。“或许手术后,听力也就恢复了?” 他的治疗过程不平坦,挺曲折,是许多此类患者中的一个。第一次,他先做了鼻子手术。当地医生说,要想治好中耳炎,必须先清除病灶——鼻子的炎症。他在县医院的亲戚找了一个熟人。熟人说:“我们县医院现在做不了这个手术。这样吧,我们把市里的XX副教授请到我们医院来给你做(鼻窦炎手术)。”志鹏并不知道,他是当时那个县医院的第一个鼻窦炎手术病人。在他之前,县医院还没开展过鼻窦炎手术。 “我吃了个哑巴亏。做手术的时候,给我打了局部麻醉。麻醉时间到了,手术还没做完,起码四个小时才完。没办法,我只能坚持。那感觉就像开凿石头,很疼很疼,很难受。但是我在手术台上很能忍,因为我再也不想被鼻炎中耳炎折磨了。” “当时那个手术做得还不错,鼻炎好了。”他用两只手在脸上比画了一下,“但是过了没多久,我的鼻子歪了,整个脸肿了起来,肿得像个熊猫。还是失败了。” 第二次,亲戚又推荐他到了市里的大医院,找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教授。“那个教授把我推到一个小手术室,一会儿工夫就做好了。手术很成功,我的鼻子不歪了,也不流脓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手术是鼻窦内窥镜做的,当时鼻窦内窥镜刚在我国部分三甲医院开展起来,没有手术切口,又叫微创手术。 李志鹏说鼻子从此后没再流脓了,但耳朵还是流脓。有时侧躺着睡觉,脓水会从耳朵里流到枕头上。他又到了另一家大医院咨询中耳炎手术。一位医生直言不讳:“不主张手术,手术能治好你的中耳炎症,但是对听力损伤了就不可逆转了。” 他不甘心,又挂号咨询了另一个医生。医生建议:“先用药物尝试控制,如果没效,再考虑手术。” 两位医生都不建议贸然做手术,他只能听进去。 吃了几个月的药,中耳还是发炎,还是有黄水流出来。他又去找医生,想做手术。手术前,医生给他讲解了手术的利弊,医生也希望能帮他保留好听力,但手术都有风险,其中可能就是导致术后耳朵听力损失加重。医生建议他先做一侧耳朵,万一因为手术导致听力下降,还有另一侧耳朵保留了听力。 “第三次,教授亲自做的中耳手术,给我补好鼓膜,现在鼓膜恢复得很好。教授说其他做同类手术的患者,术后有的出现过耳鸣,但是我没有。中耳的炎症终于得到控制,手术后的这个耳朵没有再流脓,效果很不错。但是,术后复查听力下降了,一个月后听力下降更明显。到医院再次复查,医生宣告内耳神经受损了,听力受损不可逆转。于是推荐我到西南医院听力中心配个助听器。”他说。 “但是你没来。” “我当时想,医院的助听器价格肯定贵,外面的专卖店卖得要便宜些。那时,一来我吃药手术已经花费不少钱,二来我以为配助听器像配眼镜一样简单,哪里都一样。” 这是很多人对验配助听器的误解。 助听器,不能简单地买卖。助听器本身质量很重要,但助听器的验配调试技术更重要,调得不好会再次影响听力。助听效果除了与助听器本身品质有关外,还与听力师提供的专业技术和服务质量成正比。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他们在其他地方买的助听器,质量也很好,价格也不菲,算是国际一线品牌。但是因为验配技术不专业,助听器调试不到位,助听效果就很受限,病人戴着助听器没有获得助听提升,有的反而感到声音难受,到最后只能选择放弃戴助听器。经过漫长的探求才找到我这里来。 有时我想,人为什么总要走很多弯路,碰很多壁,吃很多亏之后,才能找到真正能帮助他们的人呢? 就像李志鹏。刚开始他不相信医生的推荐,并没有到我的诊室,而是在外面门店配了一只助听器,原价近一万元,折后近六千元。打折力度那么大,他还以为自己捡到了一个大便宜,当时就订了一只。 “我当时试戴了下,感觉听得到了。他们喊我配双耳,我说不能戴双耳,万一配了不好怎么办?”他说,“幸亏只配了一只。回去后,我感觉戴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声音刺得耳朵很痛,脑袋也痛,嗡嗡作响。整个人状态很糟糕,心情很烦躁、焦虑。” “那只助听器你戴了多久?”我问他。 “起码断断续续戴了半年。”我奇怪:“你是教师,一定会有听众,一定要有互动,听力对你很重要。这段时间不戴助听器怎么去上课? 学生提问听得见吗 ?怎么跟同事交流?”他回:“原来我教数学,做了手术后,学生提问,我老是听不清楚,就没办法上 课了。”那半年是他最痛苦的时期,听力减退了三分之二,生活、工作一团糟。我问他,怎么个糟糕法?他说:“跟同事交流工作的时候,别人说了半天,我把耳朵竖起听,就是不知道 别人在说什么,我没法插话,就会很着急、烦躁、难受。感觉自己很没用,我以前也 是一个很能干的人,现在却连话都不敢说了。”他还说了这么几件事儿。他是学校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有时候跟校长交流工作,校长布置完了,对他 说:“你去安排吧。”他没法安排,因为校长交代的事情很多他都没听见。还有的时候,参加一些活动、会议,有的同事会好心提醒大家:“我们这个副校 长耳朵做了手术,听不清楚,你说话声音大一些。”“难堪啊。”他说,但仍然带着笑。他本来是教学能手,又是副校长,经常上台讲课、讲话。听力受损加重后,就没 办法上台讲,只能把方案做好后,让别人去讲。“本来这个机会是你的,却不得已只能让其他老师代讲,你就失去了展示的舞 台,心里很失落。”他说。“有没有人提出来,你不适合当校长了?”我问他。他犹豫了一下:“没有人当面提出来,但还是能够感受得到。你想啊,大家原本 在一起都是能够谈笑风生的,手术后听力受损加重,人家说话,你总听不见,当然会影响工作。有人可能就会想,长期下去你不能配合工作,合作起来也不愉快,或者已经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时间长了,就会考虑换掉你,或者让你隐退。” “你跟前妻离婚,也是那段时间?”“哎,是的呀。她是小学老师,教书不错,为人也热情,就是受不了我的耳朵。”“离婚是因为耳朵?”“不全是,但耳朵是原因之一。我听不见,她总说我是装的(假装)。再加上其 他因素,我们便离婚了。我为此非常郁闷苦恼。”他停了一下,继续说:“那种感觉 就像被全世界抛弃了一样,很无力,很无助,整个人都蒙了。”“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半年。”他说,“就是戴那只不好的助听器那段时间。”“后来呢?”“我想,这样下去肯定不是办法,无奈之中,只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了西南医 院听力中心。”他说。我笑了:“试一试……”“是的,来之前我也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我运气好,黄教授坐诊。我比较崇尚 专家,能当专家肯定是有水平的。”他也笑着说。 的确,他来的时候,虽然整个人都是笑嘻嘻的,但实际上对我们还没有建立信任,是抱着“病急乱投医”的心态来的。不过,他态度转变很快。我当时给他做完听力测试,告诉他不要着急,像他这样的听力问题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并给他调试了助听器。 他说:“戴起来很舒服,声音也很清晰,跟第一副助听器完全不一样。”当时他就要订一副。有些病人就是这样,很冲动。这种时候,我们有责任提醒他:“不一定现在就定 下,建议你回去与家人商量后再决定选配哪一款也不晚。”他很果断:“不用考虑,我信你。”十天后,他取到了定制的助听器。刚开始他答应得很好,一定会坚持佩戴。但是 不久后回访时,我们发现,他并没有完全按我们制定的方案坚持佩戴。他有时不戴, 有时只戴左耳。我问他:“为什么不坚持戴呢?”他说:“我是学校副校长,经常组织活动和上台讲话,感觉戴助听器很脏人,有 损自己形象。”脏人,就是很丢人的意思。这种心理,是大多数患者必经的心路历程。 我记得以前接诊过一位县委组*部长、一位中学校长,还有一位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刚开始他们都很害怕被人指指点点,但后来都能勇敢佩戴助听器了。 那位心理辅导老师是一位扎根山区的乡村教师,参加工作几年之后,感觉听力下降,并且日益严重,平时与同事和学生的日常交流比较困难,整个人心灰意冷,工作态度消极,彷徨迷惘,他甚至每天都在不停担心:自己还能不能在钟爱的教育事业上走下去? 2009年夏天,他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走进了我的诊室,配了人生中的第一副助听器。那之后,工作热情和干劲回来了,教学工作不但取得佳绩,还拾回了以前的音乐梦,参加琴箫兴趣小组,与师生共享天籁。 那副助听器,他戴了十年。十年的时间,他通过努力从乡村初中调到了县城高中,参加各种社会志愿活动,累计帮扶了两百多位贫困学子完成学业,帮助他们改变了人生轨迹,实现了人生理想。而他本人也被评为道德模范、文明市民。 我把这些案例讲给李志鹏听了,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坚持科学佩戴,终于走出阴霾。 2020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带着助手到他家回访。他非常热情、周到,两个小时的打了四五个电话,问我们到哪儿了。还安排我们一起爬山、赏花。那天下着小雨,山花开得灿烂,山间云雾缭绕,仿佛人间仙境。 真美啊,好久没爬过山了。整天在城市里看着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见到这样的美景,心里畅快不已。他非常客气:“黄教授,以后每年开花的时候,我都打电话请你来爬山啊,不加塞的啊,你们这大教授来,我们高兴都来不及呢,啥时候来都行啊!” “不加塞是啥意思?”我的助手是外地人,不懂这句方言。“就是不碍事儿……”他笑着回答。我问他:“上次你是什么时候上山看花的?”他回:“八年前。”那天爬山,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女儿、儿子。这是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女儿 独立能干,儿子阳光可爱,看得出来,他们相处得非常和谐幸福。 他的现任妻子是一位妇产科医生,比他小七岁。他眼里的妻子:“勤劳贤惠、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可能因为是医生,她对我的听力障碍非常理解,支持我大胆佩戴助听器。” 其实他的助听器是耳内机,他不说,一般人看不出来。他与妻子第一次见面吃饭时,她也没发现他戴了助听器。他主动说了,她才知道。“我跟她说,我有哪些优点缺点。又问她,我耳朵有问题,需要戴助听器,不知 道你介意不介意?”李志鹏说,“没想到,她完全不介意。”妻子的理解和支持,给了他很多温暖和信心。他不仅回到了最喜爱的课堂,还重新找回了那个“谈笑风生、乐观向上”的自 己。在任何场合,参加各种活动、会议都可以应对自如。领导、同事也非常信任他, 也没人在背后说闲话了。他是一个天生的教育工作者,说起中国的教育来口若悬河,别人很难插话。与曾 经那种“自卑、害怕、不敢讲话”的状态简直判若两人。显然,他已经战胜了曾经的心理障碍,不会再觉得戴助听器脏人。现在的他,整个人看起来很阳光、很自信。他说:“我经常鼓励自己,那么多人 身残志坚,我这一点点问题算什么啊。还是可以解决的。”他在QQ空间里写道:健康是1,金钱、事业、地位都是0。有了1,才有后面的0。以前这句话我理解,但 理解没那么深刻。经历了听力康复这段漫长的路,才真正理解。现在对名啊、利啊,都不在乎。以前还有冲动竞争校长,现在没那种冲动。就想踏踏实实做点实事。为学生们的成长做一点自己的努力。我对孩子的要求也没那么多,只希望他们健康快乐。 特别提醒 急性中耳炎治疗注意两个关键词:及早、彻底。 因为中耳腔是一个深藏在颅骨里的一个腔隙,只通过一个狭长的管道到达鼻腔与外界空气相通,受感染后的中耳腔相对密闭很容易残留细菌病毒,如果治疗不彻底,很容易多次复发后演变成慢性中耳炎。 慢性中耳炎治疗分为药物、置管、手术等。应当注意的是,胆脂瘤型中耳炎必须通过手术切除,慢性中耳炎久治不愈必然会因中耳的炎症侵入内耳导致耳蜗毛细胞受损,合并神经性耳聋。 耳朵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之一,手术需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操作,小小耳朵的手术难度很大,因此,一定要掌握好手术指征,尽可能保护好残余听力。 经临床药物手术等治疗后,听力仍不能恢复正常者则需要依靠助听器来提升听力。中耳炎患者佩戴助听器时应注意的是:助听器机壳或耳模上预留通气孔,尽量让耳道与外界空气流通,定期清洁耳道,防止外耳道再次感染。 3月3日,是世界听力日,也是我们的全国爱耳日。 2021年世界听力日的主题为:关心所有人的听力健康 2021年世界听力日,呼吁全人类采取行动,解决整个生命历程中的听力损失和耳部疾病问题。 本书作者、西南医院高级听力师黄青平医生,用20名听力受损者的治疗康复和身心成长故事,传递听力知识,揭秘康复要领,提点预防之道,解析社会环境,讲述医者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