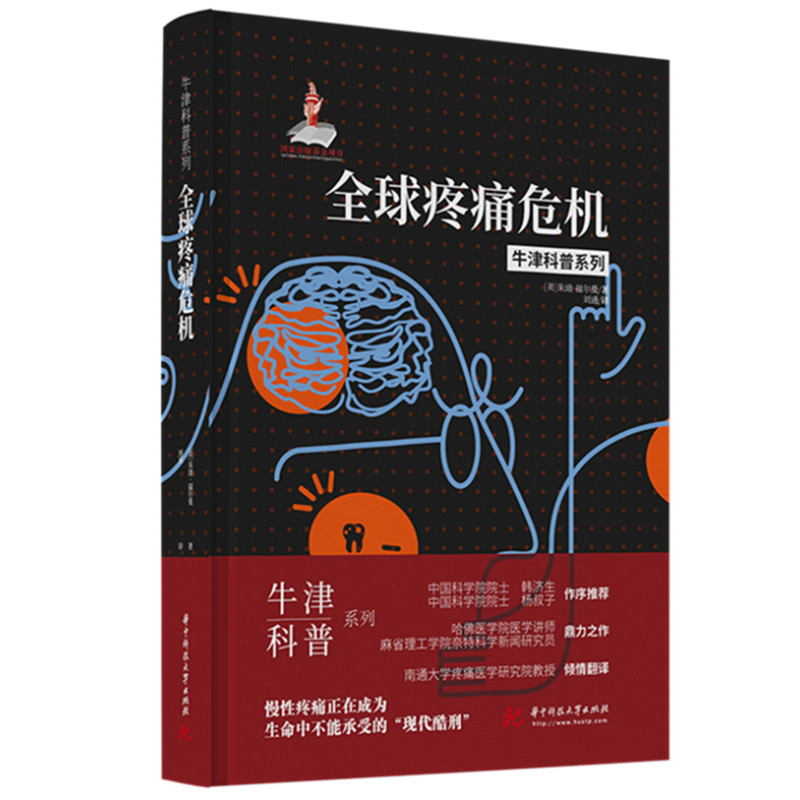
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1.80
折扣购买: 全球疼痛危机
ISBN: 9787568079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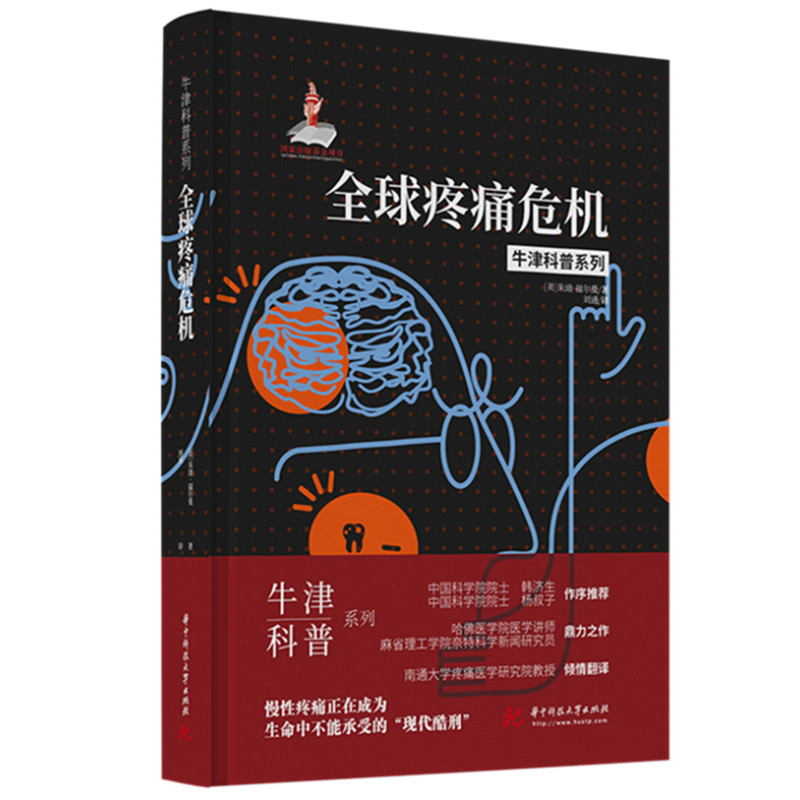
[美]朱迪·福尔曼(Judy Foreman),哈佛医学院医学讲师、医学伦理学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奈特科学新闻研究员,布兰迪斯大学舒斯特新闻调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余年来,作为健康专栏作家在各大媒体撰文,已获得50多个新闻奖项,包括1998年的乔治·福斯特·皮博迪奖、2015年美国国家科学作家协会颁发的社会科学奖等。
疼痛信号是如何传递到大脑的呢? 如果人们要真正地感知疼痛,那么疼痛信号就必须从脊髓背角向上传递到大脑,特别是脑干和丘脑(即所谓的“脊髓丘脑束”),最后到达大脑皮质的相关区域。这样一来,最终人体才会形成疼痛的感知觉。 首先,当疼痛信号通过脊髓背角时,脊髓背角中的神经细胞的作用就像“闸门”一样,负责直接向上发送疼痛信号或者对疼痛信号进行加工处理。 接下来,一旦疼痛信号到达脑干,脑干便开始向脊髓发送电信号或化学信号(下行调控),以试图阻止疼痛信号传入大脑。事实上,市场上不少的镇痛药(如抗惊厥药、阿片类药物和抗抑郁药),都是通过增强这种对疼痛的下行调控来发挥镇痛作用的。 但是,即使在脑干“试图”抑制疼痛信号传入的情况之下,一些疼痛信号也会继续向上传递,并最终到达丘脑部位。疼痛信号通过丘脑传递到大脑的三个主要区域:顶叶的躯体感觉皮质、边缘系统和额叶皮质。顶叶的躯体感觉皮质负责弄清楚疼痛信号来自身体的哪个部位;边缘系统负责联系疼痛的情绪反应;位于额头后面的额叶皮质负责控制大脑的思维能力,并赋予疼痛意义。这些功能真的非常重要。举个例子,人们很早就了解到,与同样受伤的平民百姓相比,充满了英雄主义和荣誉感的受伤的士兵感觉到的疼痛要轻得多,原因在于前者的疼痛没有被我们赋予高尚的意义。同样地,分娩也会使女性遭受地狱般的疼痛,但有些人却认为这是一段美妙的经历。原因在于至少在这段经历之后,女性遭受的疼痛换来了一个可爱的新生宝宝。 为什么大脑会感受到“幻肢痛”呢? 人的大脑躯体感觉皮质内部有一个令科学家们着迷的部位,对大脑这个部位的研究揭示了许多意义深远的重要科学发现。 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加拿大神经科学研究领域的先驱者、神经外科医生怀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在清醒并能说话的癫痫患者身上进行了著名的手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脑本身并不具有检测伤害性刺激的受体,所以大脑的急性损伤不会造成疼痛。他向患者大脑皮质的不同区域导入了轻微的电流,并同时询问患者身体中的哪些区域感觉到了刺痛或运动。根据这些信息,彭菲尔德医生构建了一张扭曲变形的“人体模型图”(小矮人)。“小矮人”人体模型图展示了躯体感觉皮质的相应区域如何处理来自身体不同部位的感觉信息。 大脑的躯体感觉皮质所形成的“小矮人”是一个看起来体型怪异、有点可爱的缩微“小人”,其本质上是关于身体的一张扭曲变形的“人体模型图”。人们注意到的关于这张“人体地图”第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负责处理来自口腔、舌头、嘴唇、脸部和手部的感觉信息的脑区在分布比例上非常不相称。显而易见,这一现象揭示了来自某些身体部位的信息对于人们的生存是多么重要。 正如神经系统的其他部分一样,大脑的“小矮人”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或可改变性。举个例子,钢琴家大脑的“小矮人”的“手”看起来与新生婴儿的就很不一样。大脑的“小矮人”理论, 对“幻肢痛”问题的解释起着关键作用。“幻肢痛”是指许多发生意外事故或因手术截肢的人,经常会感觉到缺失的身体部位,如手臂、腿部、乳房或身体其他部位,仍然存在且伴随有疼痛感。有时候,这种疼痛会令人难以忍受。例如,一个缺失手臂的人可能会感觉到那只早已不存在的“手”正扭曲地紧紧握着拳头,而指甲则嵌入手掌皮肤,痛苦不已。 举个例子来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有趣的实验,实验对象是一个因车祸失去左臂的患者。他们发现,在患者脑部的“小矮人”中,来自面部的体感区域非常接近来自手部的体感区域。在实验中,他们首先用棉签触碰患者的脸颊,然后问他感受到了什么。患者说他觉得他的脸颊被触摸了,但同时他那早已不存在的“幽灵拇指”也感觉到了触摸。研究人员推测,患者脑部的躯体感觉皮质“注意到”它没有从左臂获得任何信息(因为患者已经失去了左臂),但不知何故,原本分配给手臂的体感区域被来自面部的神经接管了。 随后,研究人员找到了一种可以帮助幻肢痛患者减轻疼痛的疗法(指“镜子疗法”)。他们用了一个盒子,在盒子上剪两个袖孔,将一个镜子放在里面,研究人员让患者把他的正常胳膊和他的残肢穿过袖孔并向内看。由于镜子的关系,这个人能“看到”他的“完好”的双臂。然后,研究人员要求该患者握紧他健全的手形成拳头然后松开,让他好像真的“看到”两个拳头同时紧握后松开一般。通过松开实际不存在的看似“完好”的拳头,让患者感觉好像两个拳头真的都松开了。随着治疗的持续,“镜子疗法”确实会逐渐减轻患者的幻肢痛。 身体如何将急性疼痛转变为慢性疼痛? 在相当大比例的人群中,发生在人身上的一系列不愉快事件,共同导致了急性疼痛向慢性疼痛的转变。神经系统本身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故慢性疼痛并非指不能消失的急性疼痛。2004年,美国西北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瓦尼亚·阿普卡利安(Vania Apkarian)对脑部的扫描研究显示,当疼痛慢性化的时候,它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患者的脑部结构。值得一提的是,就某些患者而言,慢性疼痛甚至导致了脑灰质的大量丢失。请注意,这种脑灰质的丢失相当于脑衰老加速了20年。 急性疼痛到慢性疼痛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就急性疼痛到慢性疼痛的转变而言,涉及的机制包括“神经可塑性”(神经系统的可改变性)和痛觉敏化的过程。痛觉敏化是指神经细胞对越来越弱的疼痛信号反而变得越来越敏感。这就像优秀的学生那样,神经细胞也能够通过“学习”,使其在传递疼痛信号方面的表现变得越来越好。 通常,这种变化会使神经系统进入一种近乎失控的过度兴奋状态,也被称为“紧发条”现象。事实上,神经细胞的性质发生了很大改变,以至于疼痛与伤害性刺激的发生、强度和持续时间不再相关联。这就使得短暂的急性疼痛转变为长期的、可自我维持的慢性疼痛。通常,周围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均可发生这种神经细胞的 “习得”性的超敏化现象。 如此一来,神经系统原先只对伤害性刺激作出反应,现在也能“学会”对无害的刺激作出反应。换句话说,神经系统作出的反应就好像这些无害的刺激也是有害的刺激一样。同时,神经系统也会对原本的有害刺激作出过度反应。这就好像神经系统对所有的刺激上瘾,并渴望越来越多的刺激。科学家将这种令人厌恶的新病理状态称为“痛觉超敏”。神经系统对外界刺激是如此过度反应,以至于现在神经系统感受到无害的刺激(如羽毛触碰皮肤产生的机械刺激)时,也感觉自己像是碰到了一个燃烧的喷灯一样,仅仅触碰一下皮肤就会诱发患者剧烈的疼痛。 那么当炎症性疼痛产生时,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当组织发生炎症时,免疫细胞开始分泌被称为“细胞因子”的化学物质,其中包括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IL-1)、特异性致痛物质(如缓激肽和前列腺素E2),甚至包括具有正常生理功能的神经生长因子(NGF)。这些化学物质共同作用于周围神经纤维的末梢,使得它们对疼痛信号变得越来越敏感。举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疼痛。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炎症性疾病,随着炎症病情的发展,疼痛会逐渐变得愈发剧烈。这种疼痛正是由上述炎症发展的过程所驱动的。 值得一提的是,痛觉敏化不仅发生于周围神经系统,也发生于中枢神经系统中,包括脊髓背角。脊髓背角是疼痛信号传导的第一个中继站。对于脊髓背角,周围神经的轴突将化学信号释放到突触间隙,并结合到第二级神经细胞的树突膜上,从而将周围的疼痛信号传递到大脑。 如前所述,作为兴奋性神经递质的谷氨酸是上述过程的关键参与者。当谷氨酸由C纤维的中枢轴突末梢释放时,它会结合于突触后膜上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受体上。其中,NMDA受体是这些受体中最重要的一种。NMDA受体是一种配体门控离子通道,当谷氨酸激活NMDA受体时,离子通道开放并引起胞外钙离子的内流,触发细胞内的一系列化学反应,从而导致细胞内更多的NMDA受体插到细胞膜上。由此可见,这一机制使得细胞对疼痛刺激更加敏感,并传递更多疼痛信号。 此外,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的研究表明,多巴胺也可能参与急性疼痛到慢性疼痛的转变过程。多巴胺是脑内另一种重要的化学信使。在小鼠模型实验中,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毒素来破坏一群位于脑A11区的含有多巴胺的神经元。结果发现,小鼠的急性疼痛信号仍然可以正常传递,但是慢性疼痛却消失了。 尤其重要的是,一旦中枢神经系统启动疼痛的超敏反应,维持这种超敏感状态所需要的周围痛觉刺激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就临床医生而言,这种机制具有重要的潜在应用价值。在周围疼痛发生之前进行干预,将对中枢敏感化维持在最低限度大有裨益。例如,有研究显示,医生在为患者进行前列腺手术之前,在患者脊髓部位注射止痛药,那么患者的术后疼痛比那些依照惯例处理的患者要轻得多。 然而,慢性疼痛不仅仅是因为神经系统“学会”了对无害刺激作出像受到有害刺激一样的反应。请注意,就某些类型的疼痛而言,特别是神经性疼痛,一旦神经受损伤,周围神经的电冲动可以在没有任何外界触发的情况之下持续地发放,从而导致患者的自发性疼痛。 打个比方,些神经纤维的活动,就好像在“滚球”一般。最初的疼痛一旦启动,后续的反应就无需外界触发因素。尤其重要的是,这时的慢性疼痛不仅涉及受刺激的神经纤维,还会涉及那些自发性发放的神经纤维。譬如,就像流感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样,受损神经临近的神经细胞也被卷入了整个过程。在最基本的神经病学层面上,疼痛信号变得具有传播性,从一个神经元传递到下一个神经元。在分子生物学层面上,受损伤神经元的基因表达活性也发生了改变。在许多发生慢性疼痛的情况之下,P物质(一种神经肽)、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和其他产生疼痛信号分子的基因表达活性有所增强。这是机体从急性疼痛到慢性疼痛转变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不幸的是,尽管如此,以上这些知识还不是急性疼痛转变为慢性疼痛的全部分子机制。值得一提的是,有研究表明,神经系统内的免疫细胞(胶质细胞),也在急性疼痛到慢性疼痛的转变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仅仅通过观察患者的面部表情来评估疼痛,效果怎么样? 虽然面部表情的确可以传达疼痛程度,但是仅通过观察面部表情来破译疼痛信号到底能做得多好,目前仍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患者可以通过伪装面部表情传达疼痛。 医生是人们希望的最能理解面部疼痛的线索的人。然而,事实证明,通常会低估患者的疼痛的人正是医生。但是,如果连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都有理由怀疑患者不是由于疼痛就医,而只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取毒品,那么医生误诊和低估患者面部的疼痛线索的现实情况就更严重了。接二连三的研究表明,在对待同一个疼痛患者时,医生对患者疼痛等级的评分远低于非专业人士。 举个例子,在一次实验中,研究人员拍摄了有关肩痛患者的视频,实验中要求患者以痛苦的方式活动他们的肩膀,然后把观看这段视频的120名医生分成3个不同的组别,并要求他们对患者的疼痛等级进行评估。第一组医生,仅给他们观看视频中疼痛的面部表情;第二组医师,在给他们看视频的同时,还给他们提供了患者对自己疼痛的量化评分;第三组医生得到的信息和第二组一样,但被告知视频中患者的疼痛表情是因为想得到阿片类药物而伪装出来的。结果发现,所有的医生都低估了患者的疼痛等级。同时得到了患者对自身疼痛评分的第二组医生对患者疼痛的评分更接近患者自己的评分。而那些被告知患者可能是伪装疼痛表情的第三组医生与仅看到痛苦表情的第一组医生,都低估了患者的疼痛程度。 但是,面部表情线索毕竟受到自主和非自主的肌肉运动的影响,故有一种办法可以判断人疼痛时的面部表情线索是否是伪装的。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假装疼痛时,面部会经常不适当地做出皱缩和鬼脸。患者假装疼痛期间,面部的肌肉运动与疼痛发生通常也是不同步的,通常是过度夸张的,几乎就像一幅有疼痛表情的人物漫画那样。 有意思的是,计算机在鉴别真伪方面做得比人的肉眼要好得多。举个例子来说,在几所大学的一项联合实验中,研究人员要求205名受试者根据面部表情线索来鉴别疼痛表情的真实性。在这项实验中,一部分受试者没有受到疼痛刺激,另一部分受试者则是在实验室确实受到了疼痛刺激。结果表明,人的肉眼很难鉴别出任何差异,但是计算机有85%的概率是判断正确的,这可能是因为计算机能检测到微小的或发生得太快的面部表情的差异。假装疼痛的人会经常张开嘴巴并且口型的变化较小,而这一差异只有通过计算机才能捕获到。 为什么女性会感受更多的疼痛呢? 有一种理论认为,对于男性和女性,其神经元中的化学通路被激活后可能有不一样的变化。在对大鼠的一些研究中,“二级信使”(负责传递疼痛信号的化学物质)在雌性和雄性动物体内是迥然不同的。雄性大鼠使用3种不同的“二级信使”,而雌性只使用1种。女性的皮肤中的神经纤维末梢的数量比男性的更多一些。此外,负责感受强烈刺激的痛觉神经细胞上,也布满了睾酮和雌激素这两种性激素的受体,而这两种激素的存在可以解释许多疼痛反应的性别差异。然而,人们离揭开全部的谜团仍相距甚远。 在童年期,也就是说,在青春期之前,男孩和女孩的疼痛反应表现出相似的模式。但是,一旦青春期到来,女孩中某些类型的疼痛则明显更为常见一些。即女性中疼痛疾病的患病率相同,女孩的疼痛程度也往往比男孩更加严重。 一般来说,睾酮似乎可以预防疼痛。例如,如果新生雄性大鼠被阉割,那么它们在青春期就不能产生睾酮。结果如何呢?它们对阿片类药物吗啡的镇痛作用变得不那么敏感了。如果给新生雌性大鼠注射睾酮,那么它们会从吗啡中获得更好的镇痛效果。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实际上男性会对疼痛逐渐产生更强的耐受性。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文化期待的差异,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一时期男性体内会产生大量的睾酮。 但是,如果说睾酮的作用机理是相对简单的(睾酮越多,疼痛的感觉越少),那么雌激素的作用机理就有些复杂了。 众所周知,女性雌激素水平在月经周期中变化很大,而女性报告疼痛体验的结果也同样会发生变化。一项关于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的研究发现,体内雌激素水平最低时,疼痛的程度最高,但是疼痛程度的增加也可能与体内雌激素水平的快速变化有关。 分子生物学家发现,雌激素会下调(或降低)一种与疼痛相关的COMT基因的活性。COMT基因的功能是处理“应激激素”,由此可见,如果COMT基因活性太低,那么身体就无法有效地处理“应激激素”。由于应激激素能直接作用于神经纤维以加重疼痛,雌激素作用于COMT基因的净效应是加重疼痛。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们首先测试了雌性啮齿动物的疼痛敏感性,然后通过手术切除了它们的卵巢(卵巢的功能是产生雌激素)。随后进行测试,失去卵巢的雌性动物对疼痛的反应更像雄性动物一些,也就是说,它们对疼痛变得不太敏感。如果再给它们注射雌激素,那么这些失去卵巢的雌性动物对疼痛的敏感性会很快恢复正常,就像在卵巢切除手术前一样对疼痛敏感。 人们可以将绝经期的女性视为以上大鼠实验的人类版本。绝经期女性的卵巢停止分泌雌激素,就像卵巢被手术切除了一样。为了治疗雌激素急剧下降引起的临床症状,许多绝经期女性开始服用外源性雌激素,也就是说,雌激素不是在体内自然产生的,而是作为药物服用。如果“雌激素会增加疼痛”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应该推测这种激素替代疗法会加剧疼痛。然而,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这种激素替代疗法时而加剧疼痛,时而又不会,甚至有时又能缓解疼痛。 其中,有一些研究表明,绝经期女性采用激素替代疗法后,确实会遭受更多的慢性疼痛。但是,也有研究表明激素替代疗法与老年女性的疼痛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还有研究表明,当绝经期女性停止采用激素替代疗法时,她们的疼痛反而会增加,这个事实恰好与“雌激素会增加疼痛”的理论预测的相反。事实上,一些曾经患有偏头痛的女性在停止雌激素治疗后的几周内,重新出现了偏头痛的症状。此外,一般来说,女性人群中更常见的三叉神经痛等一些疼痛疾病,要到女性绝经期才开始发病。 那么,这里就有更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当变性人服用激素来强化他(她)们新获得的性别特征时,对疼痛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意大利的研究人员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一项初步研究中,他们随访了由男性变性为女性的变性人,这些变性人服用雌激素来增强女性性别特征。结果发现,她们中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出现慢性疼痛,特别是头痛。研究人员还研究了由女性变性为男性的变性人,这些变性人服用睾酮来增强男性性别特征,结果发现,他们的慢性疼痛减轻了。所有这些现象都比较符合“睾酮预防疼痛,而雌激素增加疼痛”的提法。 为什么这些激素与慢性疼痛有如此复杂的联系呢?迄今为止还没有十分确定的答案。有这样一种理论认为,睾酮会抑制脑中的兴奋性疼痛通路,从而产生镇痛效应,而雌激素可能会阻断抑制性的疼痛通路,从而导致更多的疼痛。 对于绝经前的女性,雌激素水平在每个月经周期中是上下波动的。这是使雌激素与疼痛的联系变得更加复杂的主要原因。在月经周期的不同时间点,疼痛反应程度也发生显著的波动。许多疾病,包括肠易激综合征、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头痛和肌纤维痛,其疼痛都会在整个月经周期内发生显著变化,但并不总是与人们的预期结果一致。一方面,在月经周期中雌激素水平较低的时期,有些女性对疼痛会变得更敏感。然而,另一方面,在女性雌激素水平较高的妊娠期,女性感受到的偏头痛和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的痛感反而较少。当雌激素水平在分娩后突然下降时,女性患者偏头痛发作的次数会明显增加。这真是匪夷所思啊! 有鉴于雌激素与疼痛关系的复杂性,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怀疑,体内雌激素的绝对水平可能并不是疼痛的关键影响因素,而体内雌激素水平的快速变化才是引起疼痛的关键。换句话说,就是雌激素水平的快速改变所诱发的机体内稳态的变化,才是疼痛的真正诱因! ①权威性。本书作者、译者均为疼痛学领域权威专家,本书得到国家科学院院士韩济生、杨叔子倾情推荐,内容权威、可靠。本书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②前沿性。疼痛是人类疾病较常见的症状之一,但有些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这一观点需要被更多人知道。全球数以亿计的人深受慢性疼痛的折磨,中国约有1亿慢性疼痛患者,对他们而言,疼痛并不是忍忍就能好的。 ③时代性。在2007年,我国卫生部将“疼痛科”作为一级诊疗科目,是我国疼痛医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里程碑,十几年来,我国已在此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免除疼痛是患者的基本权利,是医师的神圣职责,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在这一点上,本书具有较强的时代性。 ④可读性。本书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展开,通过大量的事实、生动的案例以及前沿的科学研究成果,引导读者独立思考,让读者给出自己的判断和可能的解决方案,版式清新,内配彩插,生动有趣,可读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