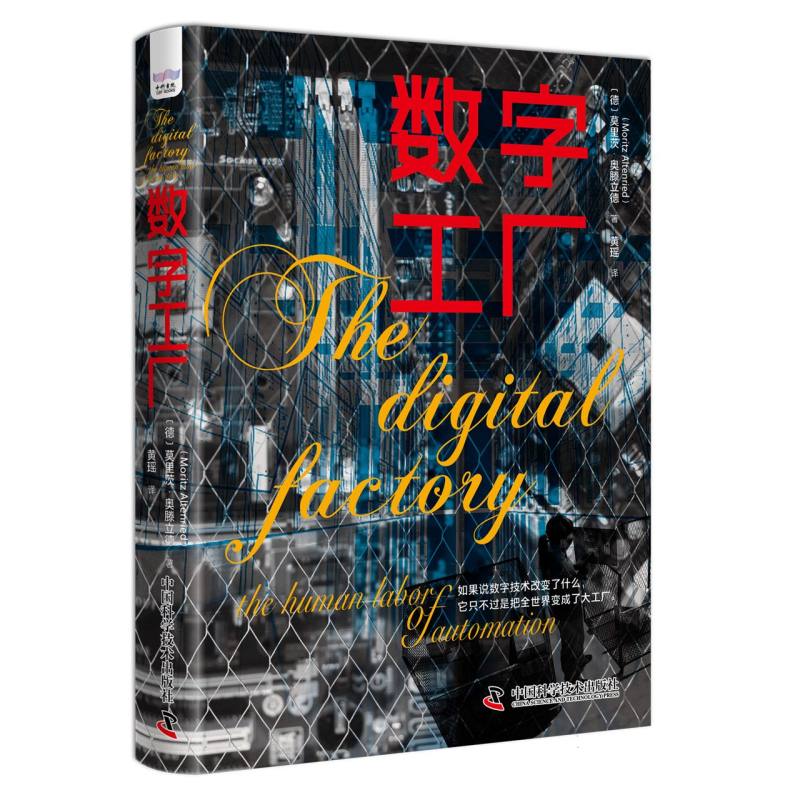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1.40
折扣购买: 数字工厂
ISBN: 97875236004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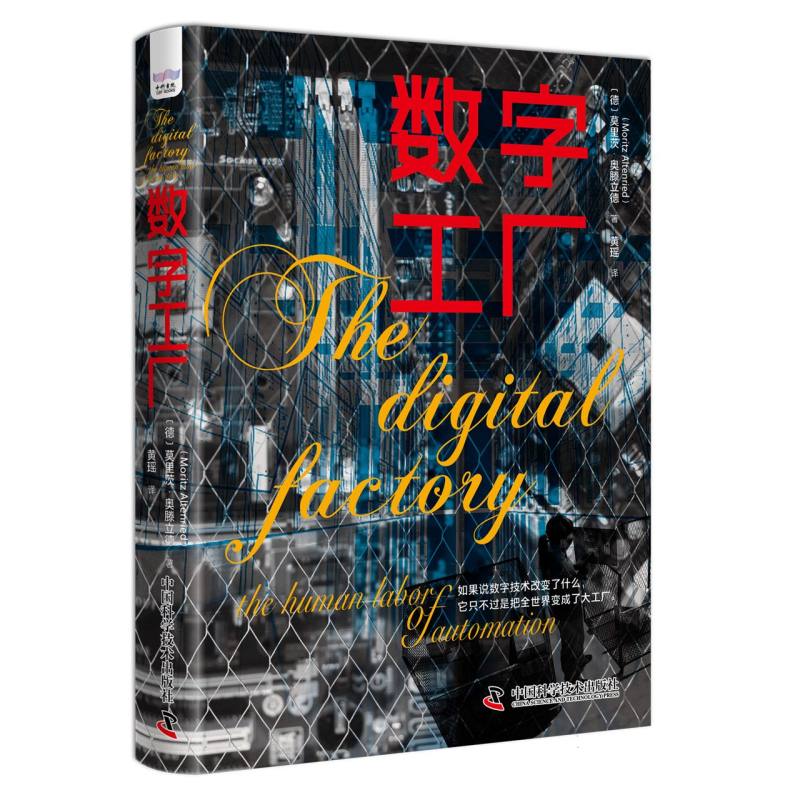
莫里茨·奥滕立德,柏林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和德国融入及移民实证研究所(BIM)研究员,研究方向包括数字劳动力、互联网政治经济学、城市空间下的平台劳动等。
第1章 双城记:“暗夜之城”和“光明之城” 人类喜欢讲故事,也擅长讲故事。其实,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讲故事,先是口耳相传,然后诉诸笔端,最后借助屏幕。心理学家认为,故事遵循了一种可识别的模式,满足了人们在看似无意义的事情中寻找意义的需要。人类学家认为,故事是人类生存本能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以帮助人类正确认识危险,当机立断作出决定。此外,鉴于人类讲故事的历史如此漫长,人类的大脑已经习惯了寻找故事或模式,哪怕这种故事或模式压根就不存在。故事赋予人类一种掌控感,人类可以与同伴分享自己的世界观以及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但是故事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故事不仅可以解释过去和现在,而且可以建构人类的行为,并进一步塑造未来。 人类为什么讲故事?这从城市中可窥得一二。人类的城市是独一无二又错综复杂的存在,仅凭浅显的理解和预测根本无法认识城市。因此,人类为了认识城市,一直在讲述与城市有关的故事,这也在意料之中。城市是文明的跳板,是艺术、文学、戏剧和民主的故乡,诸如此类的故事深入人心。此外,有些人把城市比作不公和罪孽的魔窟,有些人把城市形容为专注于贸易和商业的创业之地,有些人则打造出弗里兹·朗(Fritz Lang)镜头下大都会式的未来城市。尽管人们众说纷纭,但是在过去的约 150年里,有两个关于城市的故事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们分别是“暗夜之城”和“光明之城”。 “暗夜之城” 第一个关于城市的故事与剥削、荒凉以及痛苦息息相关。1929 年,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一位充满争议的著名英国作家——开始动笔书写英国的城市状况,这是一个他特别钟爱的写作题材。他认为,“英国人一直住在城市里,但是对如何建造城市、如何看待城市以及如何在城市中生活一无所知”。对劳伦斯来说,城市绝不仅仅是外在的建筑,城市的状况也反映了居民的状态: 大城市是美丽、高尚以及华丽的代名词。英国人却对大城市的这些美好品质嗤之以鼻,极力反对。英国就像用低劣住宅玩填字游戏,促狭小气,不上台面。英国人管这些低劣住宅叫“家”……这些(低劣住宅)就像红色的捕鼠笼,极为窄小。住在里面的人只会越来越孤立无援,越来越卑躬屈膝,越来越愤懑不平,一如捕鼠笼里的老鼠。 谴责城市,构想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作为替代,劳伦斯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但是他的做法却反映了当时的主流观点。19 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这种观点开始萌芽。这一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的黑暗面逐渐浮出水面。1880 年,苏格兰诗人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出版了诗作《暗夜之城》(the City of the Dreadful Night),这位早已被人遗忘的诗人在诗中写的就是这种阴暗面。这首诗因用悲观苍凉的笔调描写维多利亚时代的城市而闻名。但是,他抓住了维多利亚时代城市生活的本质,他笔下的城市到处都是贫民窟,是一个疾病和贫穷司空见惯的地方,大部分人都被迫在城市里讨生活。他把这样一个关于城市的故事传播开来,并强化了这个故事的影响力。对穷人和工人阶级这些普罗大众来说,“暗夜之城”就是他们每天要面对的现实。 暗夜之城的故事并非作家们的凭空想象。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热衷于开发楼盘的开发商和提供贷款的银行利用城乡间的反差,将城市描绘成藏污纳垢、无处立身之地。他们企图说 服中产阶级抓住机会,利用易得的资金和普及的汽车,去不断扩大的郊区买房。政府的作为又强化了这种消极的观点:建设新的城镇和城市,努力为技术工人和中产阶级提供“避难所”。 尽管城市存在贫困、疾病和犯罪的隐患,但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除了推行一些力度不大的措施,如改善卫生条件、为新的开发项目颁布建筑标准之外,城市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城市之所以缺少作为,是因为他们坚信城市贫民要为自己的处境负主要责任。极少数试图改善城市的举措也是出于私利,如政治和经济精英担心社会动荡或激进思想在贫民窟中传播,以及劳动力的健康受损会影响盈利。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有一种流行的消遣方式,富人会在导游的陪同下参观“贫民窟”,手里拿着标注着“最佳景点”的小册子,为贫民的生活惨状惊叹不已,这也让当时所谓的“贫民窟”阶层察觉到了统治阶级对城市的普遍态度。 数字时代的浪潮袭来,人类劳动即将被重塑? 展现数字化时代下真正的劳动场景,探究劳动形式的变与不变。 描摹数字时代下的数字工人群像。“扫描仪的‘哔哔’声就是我工作的声音”“一周7天,一天12个小时,我和我的同事都在打怪”“我找到了1000种描述窗帘的说法”“我看到的东西超出想象”......物流工人、送货司机、职业游戏玩家、众包工人、平台审核员等都是数字时代下新的数字工人,数字化如何将全世界的人类劳动前所未有地整合在一起,又是如何将人类劳动隐藏在网络与编码之后? 展现数字泰勒主义向传统劳动形式的回归。自动化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让人类远离重复性高、压力大、单调乏味的工作,在一些最具创造力的领域,甚至令人惊讶地呈现出传统工厂的特征。 揭示比被机器人取代工作更重要的问题。表面呈现为自动化流程或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背后,都有人类工人在训练软件、评估其工作、解决困难问题,或者实际上只有人类在劳动,只不过完全被算法所掩盖。与之相比,算法管理的崛起、劳动控制与测量的新形式、数字技术带来的新的劳动地理分布、新的性别与种族化分工、新的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偶然且灵活的劳动力带来的影响,远比因为机器人而失去工作带来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