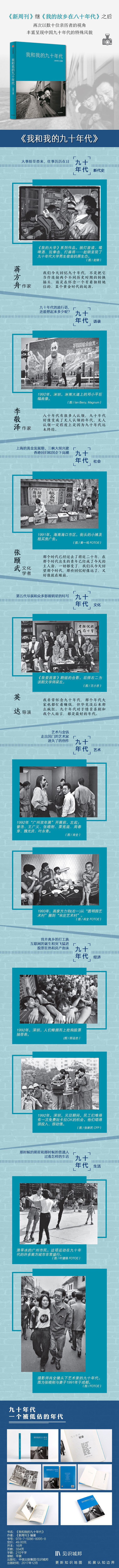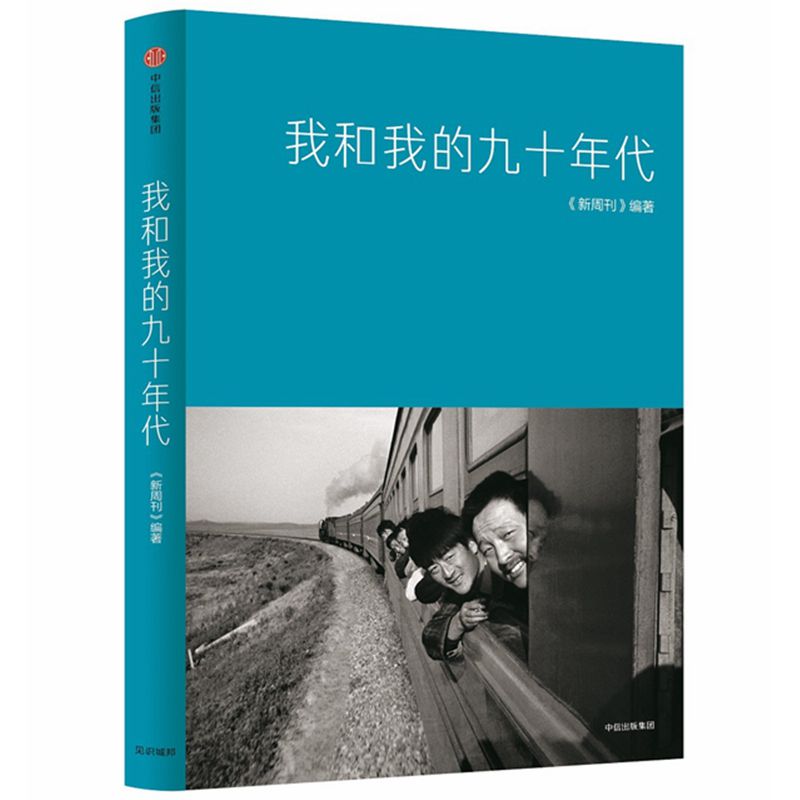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49.00
折扣价: 33.90
折扣购买: 我和我的九十年代
ISBN: 9787508680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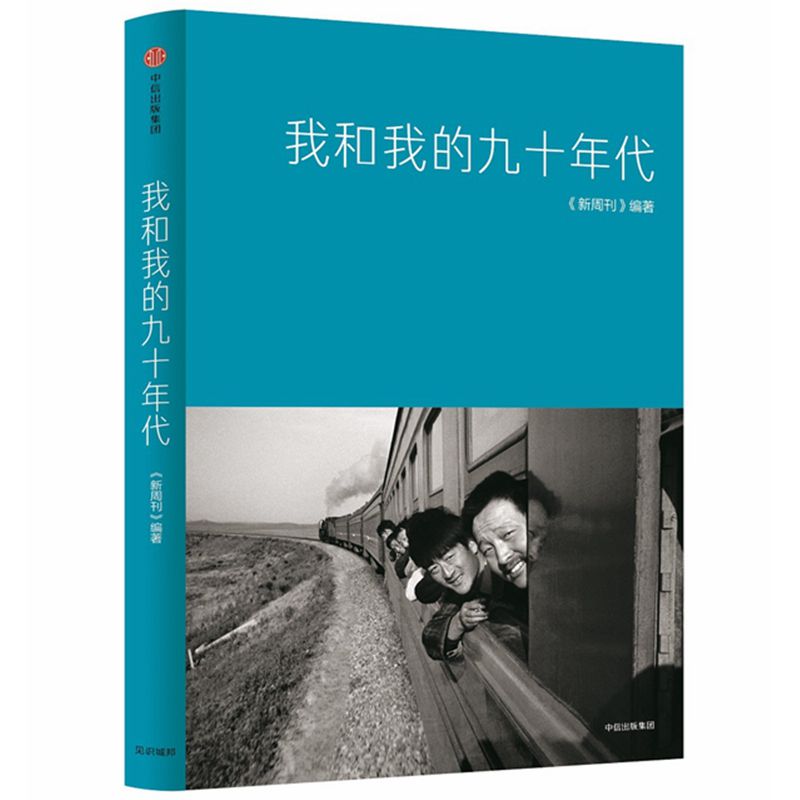
《新周刊》,“中国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创办于1996年8月18*,十二年猛进,已成为中国社会变迁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新周刊》是读者眼中畅快淋漓的“观点供应商”,它始终给读者带来新鲜的撞击与概念,引导读者关注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趋势。阅读着《新周刊》成长的新锐青年,如今已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中坚力量。
序一 一个被低估的年代 张颐武 这些年来,怀念八十年代(编者注:本书中出现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均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似乎是一个流行的风潮,一直有许多人对八十年代情有独钟。人们往往觉得**是一个并不浪漫和富于诗意的时代,但是,**中国的崛起所具有的力量和我们的社会文化状况,其实是八十年代根本无法想象的。近四十年的光阴仿佛一晃而过,我们还没有抓住八十年代,现在已经是“90后”和“00后”的天下。 而在**的“新世纪”和我们所缅怀的八十年代之间,有一个人们无法回避的、关键的转折年代,也是我们回顾这四十年历史时需要时时关切的重要时期——九十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时期的意义已经越来越被我们所感*到了。但人们似乎很不情愿提到这个时期,它的意义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知。不少人觉得那个时期不太合乎他们的理想,仿佛这是八十年代向下**的时期,是**和热情消退、平庸到来的时期。其实,这个时代的意义被低估了。 这种低估,其实来自我们对于**所缺少的东西的渴望。这渴望导致了我们不愿意提及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其实是一个转变期,是中国的未来由朦胧而清晰、由迷惑而明朗的关键年代。正是有了九十年代在文化上的转变,我们才可以进入一个新世纪,中国的**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才会有**的成果。**看来,九十年代正是四十年中国发展的一个过渡期,有了这个时期,八十年代的价值才会转化为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国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未来。所以,九十年代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新周刊》就出现在那个时代,现在,这家杂志愿意出一本书,从当下对那个时代提出新的思考和新的见证,这无疑具有独到的意义和价值。 遥想当年,八十年代末的巨变刚刚过去,“南巡”所激荡的风潮和新的期望刚刚被诱发,下海经商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刚刚开始创业。**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如马云、马化腾,都还是我们预想不到的未来;而王健林等人也刚刚开始自己的事业。从《渴望》《北京人在纽约》到《还珠格格》,是那个时代的共同的记忆所在。当年《渴望》主题曲在大江南北流传,**我们 从其歌词中仍能感*到那种社会的集体意识:“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这是一个真正开启了*常生活的感觉的新时代。那些宏大的叙事远了,新的生活的**和情绪开始出现。这是新的以大众为中心的社会。它显然提供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景观,也超出了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话语。它的形态是我们必须认知的关键。无论是张艺谋和陈凯歌的电影、《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等电视剧,还是王朔的作品以及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长恨歌》、莫言的《**肥臀》等小说,都提供了变化的轨迹。 那是知识界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人文精神”大讨论,一些对于未来充满悲观情绪的知识分子焦虑于在新的市场化环境下是否会出现一个社会崩溃的“旷野上的废墟”,并为此发出异常激烈的“抵抗投降”呼叫的时刻;那是一些人对于急剧市场化和**化的未来把握不定,也对于中国的前景犹疑、困惑的时刻;那也是另外一些人对于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了*多信心、*明智的分析的时刻。知识分子的大论战,正凸现了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同思考和观察。 九十年代,中国进入所谓“后新时期”,消费社会刚刚有了一个雏形,社会还处在市场化和**化的前期。许多**看起来简单的关于中国发展的事实,在当年还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在**所谓“后现代”“**化”或“中产群体”早就是老生常谈,当年却*到了众多置疑和追问。这些进程的背景是异常清晰的:一方面,中国的变化****了“新时期”的构想和预设;另一方面,中国在**化进程中的位置,也有了以往根本无法想象的独特性。**人们所看到的,竟然是“逆**化”浪潮在发挥作用。 要认识九十年代,我们首先需要从八十年代开始。八十年代的中国,刚刚从“**”中脱离出来,正处在一个精神解放的时代。当时的人们把一切都视为精神解放的表征,一件牛仔裤、一副“蛤蟆镜”,都意味着从精神上摆脱压抑、需求新的空间的努力。其实,八十年代的主题,就是如何将个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宏大的集体性话语中脱离出来。八十年代的“主体性”召唤,表达的就是这种“个人”存在的精神性的要求。无论是萨特还是弗洛伊德,其实都是为这个新的“个人”的出现发出的召唤。这个“主体性”的个人的展开,直接提供了思想和精神从原有的秩序中“解放”的想象。 八十年代文化的关键,正在于一种对于康德的“主体性”观念的新的展开。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有一个异常重要的附论——《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整个八十年代思想的核心的命题。李在这篇文章中点明:康德的体系“把人性(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突出地提出来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424 页)。而李泽厚的发挥似乎*加重要:“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同上,434 页)这里李泽厚召唤的康德的幽灵,其实是对于八十年代新的精神的召唤。“主体性”正是整个八十年代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话语中脱离的基础。而这个“主体性”,是新的“现代性”展开的前提。八十年代具体地展现了这一“主体性”话语。正是这种“主体性”的寻找,成了八十年代的“现代性”赋予我们的*大梦想。 进入九十年代,世界和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时期”追求的目标仿佛就要实现,但它本身又*到了巨大的冲击,历史根本没有按照预想的道路前行。在“冷战后”新的世界格局和**化的浪潮之中,中国的状况成为世界的焦点。中国九十年代的文化经验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个“后新时期”中,中国经历的**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是极其深刻的,它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导致了高速的经济成长,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新问题。 中国以一种特殊的“发展”方式,在九十年代**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一方面,政治性的象征系统维持不变,以作为避免急剧变化过程的社会混乱的策略。随着苏联、东欧的雪崩式瓦解,以及十年来俄罗斯的持续危机、**竞争的激化,民众的**认同也有所凝聚;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常生活经验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社会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的直接控制和管理已经极大削弱,**直接控制的工业资源已经不到30%,传统的“单位”体制已经越来越弱化,跨国企业和民间资本已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舞台。 而在越来越市场化的社会舆论和大众文化的**下,所谓“公共空间”也迅速形成。人们的生活经验已经不可能处于**的全面控制之下,而是明显地处于一种横向的联系之中,市**会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开始形成。而随着大量移民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发展、**投资的剧烈增长,中国的**化达到了***的程度。目前,中国在**化之中无疑不再是一个全能的社会,而是一个社会的“横”向的关系和**的象征,以及“纵”向管理交错的复杂的社会。 九十年代的文化的特点就在于一种“物质性”的出现。没有物质性的变化,我们就不可能有新的未来。虽然我们可能丢失八十年代宝贵的东西,但这丢失却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必然。八十年代的文化中,我们的想象是建立在精神基础上的。我们好像是用头脑站立在世界上,虽然仍然面对匮乏的生活和新的、来自外界的物质性的**,但纯粹的精神追求和抽象的理想,支撑了我们的想象和追问。所以,八十年代的“新时期”虽然有极大的物质性吸引的背景,却在精神层面上展开,它依然是不及物的。这里的追求几乎忽略了“物质”的**和吸引。但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却将八十年代的抽象精神转变为物质的追求。导演张暖忻点出了*初的消费**的力量,也点出了当年抽象的“主体性”在现实的**化和市场化时代的困局。这是将康德的玄虚的用头脑站立的状态,转变为用双腿支撑自己的“主体性”。 其实,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断裂中自有其连续性。九十年代将八十年代抽象的“主体”,变成了**化和市场化的实实在在的“个人”。八十年代的“主体”是以抽象的精神进入世界的,它仅仅表达了一个真诚而单纯的愿望,也提供了一个可能性的展开。其没有物质支撑的空洞性,正需要九十年代的填充。而九十年代的这些中国的“个人”,以实实在在的劳动力加入世界,用自己的劳动和低廉的收入寻找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世界。所以,正是九十年代给了抽象的八十年代一个具体的、感性的现实。八十年代那些抽象而浪漫的观念,正是被九十年代的消费愿望和物质追求具体化。八十年代康德的自由的“主体”,变成了九十年代黑格尔式“理性的诡计”拨弄下的“个人”。这些个人的成长和变化,其实是**社会凝聚和发扬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九十年代开启了二十一世纪的未来。 而中**部的变化正是**的变化。**化需要中国的参与,中国的发展本身也必然带来新的可能性。九十年代中**部和外部所展开的“物质性”力量本身,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力量,也是中国*坚实的基础。九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大的力量,就在于它终结了八十年代抽象、玄虚的“主体”,并找到“主体”赖以存在的前提。 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化进程其实是历史的新一页。它一方面告别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性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它也**了“五四”以来反抗西方的宏大叙事,而是在丰富而多元的文化中探寻新方向。 **中国丰富而复杂的形态,正是那个时代的结果。我们**所得到的或者所感叹的一切,其实都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的影子。**中国在**的影响和力量,正是九十年代的开放所奠定的。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在那个时代出生的青年已经成了**的主人翁。一切都变了,我们从**回望那个时代,那些回忆好像远了,又好像就在眼前。**的中国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正是从那里来的。我想,那个时代对于**的人们来说,它仍然活着,它仍然在我们之中发挥影响。 让我们从这部书回到九十年代,在回忆中领略那过去。而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也可以从这部书回到那个时代,那依然活在我们之中的时代。 是为序。 序二 我的九十年代,我们的九十年代 蒋方舟 联结一个世代的人的暗号,永远是他们共享的记忆。 对于美国婴儿潮一代来说,**他们青年时期的社会想象,围绕着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展开:从二战后的丰裕到古巴导弹危机;从越战到反文化与民权运动。不管政治和文化立场如何,同一代人总是在同一个记忆场域中成长并活动,这种共同记忆,展现出每个时代独特的时代精神。 当代中国的社会想象起源于九十年代。这并不是说中国庞大而沉重的过去没有发挥其无微不至的影响力,只不过,看惯进步、富裕和繁荣的国人所感知到的那个中国,只有相当年轻、浅近的历史。从打击“投机倒把”的中国到全民炒股的中国,从凭票供应的中国到电商疯狂打折的中国,并没有相隔一个世纪。对于已经是社会主心骨的60、70 后来说,前一个中国是渐行渐远的遗迹;对我这样的85年后生人,后一个中国是我们出生、成长的理所当然。 在我们还蹲守电视机旁的年纪,《太空堡垒》和《新世纪福音战士》是所有孩子的共同话题。没有人质疑**在**天好起来。生活的改善不只在《新闻联播》里,也在每一年的生活里。这片土地在我们的记忆里,从来就和动荡与不安无缘。我们懵懂地听到“亚洲金融危机”或者1998大洪水之类的名词,但举国一致的努力总是可以渡过难关。1997年香港回归是许多人爱国自豪的*初记忆,我们的九十年代结束于中华世纪坛迎接新千年的焰火,以及2001年申奥成功。 九十年代对于我们*多的是模糊和混沌,一如所有人回望童年仿佛都隔着层磨砂玻璃。但对我们来说,*加光明、清晰的二十一世纪和之前模糊的十年并没有明显的断裂:我们还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只是从不够好变得*加好。 在当时的我们无法感知到的幕后,九十年代是个*加粗犷、却从来不缺生气的时代。1992 年的“南方谈话”是它真正的开端。一切似乎都不允许了,但一切似乎都被允许了。冯仑和潘石屹开始炒房,瀛海威时空开通了中国*早的互联网王国,大学开始扩招,而毕业生开始自谋生路。世纪末的“野蛮生长”要到很久之后才开始被规范和整顿,为了满足“入世”标准并且为经济全面转轨做好准备,整个**开始了一场痛苦的转型。许多家庭的生活从此分成前后两个部分,而后半部分并不都是美好。 所有的一切都开始努力拥抱市场经济和“**化”,仿佛急切地要从上个十年突然结束的混乱与彷徨中找出道路和意义。“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是对八十年代的回答,也是对八十年代的判词。经世致用的*高律令下,法律、经管成了*新的时髦专业,生物学则是二十一世纪的学科。曾经统一在人文和启蒙大旗下的文化队伍愈发分化,一并坍塌的还有曾经坚不可摧的文化战线中的等级制,**和“社会”的认可不再是文化人单一的价值与认同的来源。 市场带来了困惑和混乱,但也开启了全新的可能性。九十年代是文化和产业**次并列的时代,也是我这种“离经叛道”的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走入“文坛”的特殊节点——到了文化产业真正繁荣的二十一世纪,整个“文坛”的重要性都已不复当年。 从*广阔的视角看待,九十年代的主题无疑是“变化”。但变化——有时是激烈的变化——从来没有离开当代中国历史的字典。九十年代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当代中国*为强大和持久的主题——“稳定、改革、开放、发展”——得以生根发芽的土壤。九十年代的“变”,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如今“不变”的基础,为变革应该有的方向和模式设定了标准。也正是因为如今的繁荣无非建立在九十年代所开创的基础上,这段记忆才能够作为社会各个世代的社会想象,服务于当今中国的话语系统。 我们**回忆九十年代,不是把它当作连接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换插头,而是在怀念一个有着独特地位的、某个黄金时代的起源。 ◎通过“九十年代断代史”“九十年代社会”“九十年代文化”“九十年代艺术”“九十年代经济”“九十年代生活”六大板块忠实记录九十年代中国社会风貌,为**的中国提供审慎的借鉴。 ◎中国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新周刊》继《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之后倾力出品,丰富、多元、忠实、怀旧,带你穿越回那个似乎已经逐渐远离的时代,找回你的情感寄托。 ◎本书既可以提供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忠实的社会记录,也可以为当今的各界人士提供深刻的经验教训。 ◎对导演英达、演员赵雅芝的采访,对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张艺谋的记录,完整收录。仿佛亲身回到九十年代的文化场景,考察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如何以纯粹的匠心经营一部部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