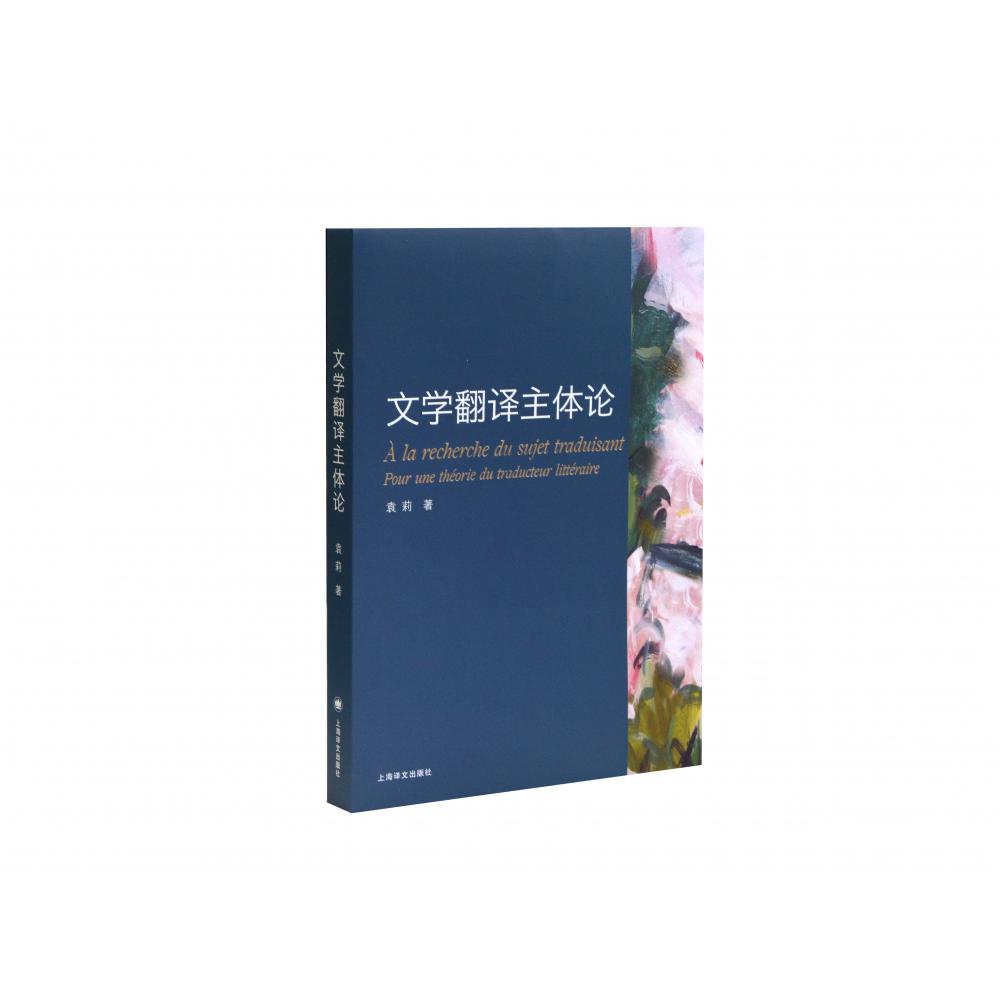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译文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7.70
折扣购买: 文学翻译主体论
ISBN: 97875327827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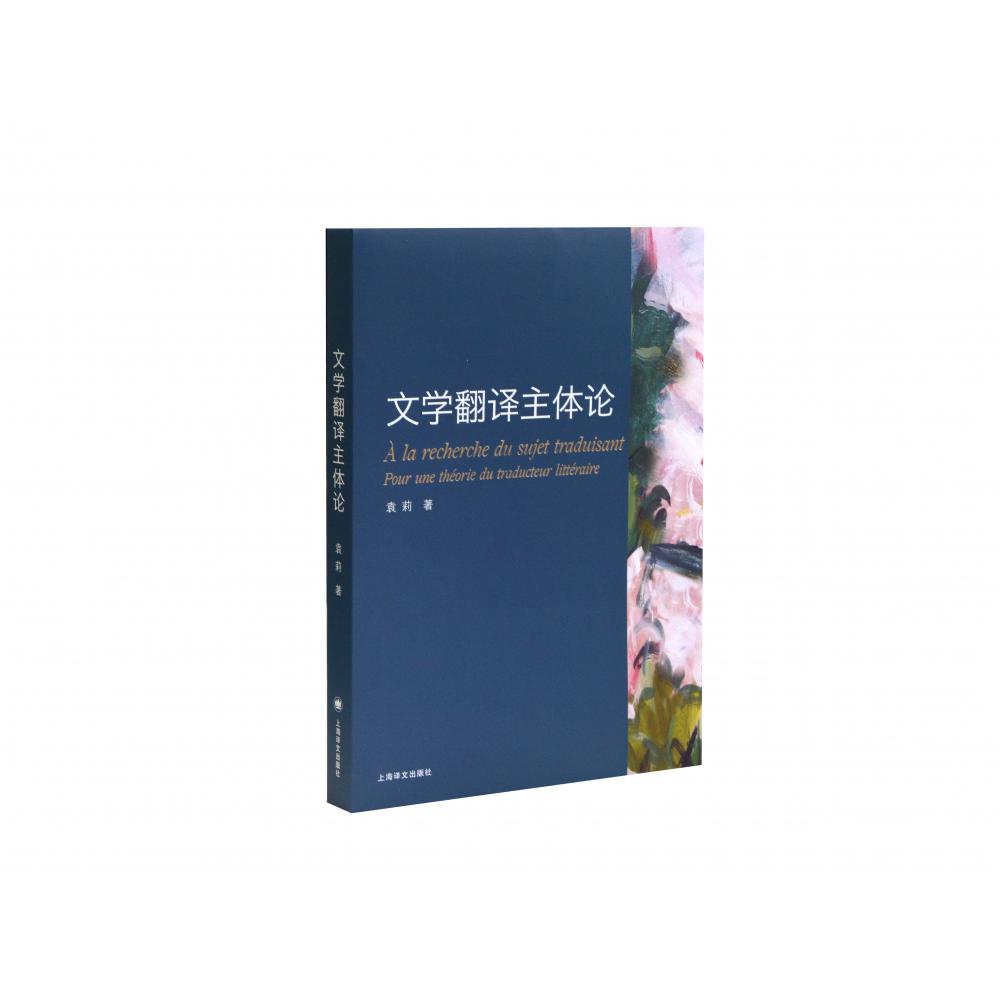
【作者简介】:袁莉,博士,副教授,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法语系主任,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0年获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2012年当选复旦大学光华人文基金青年学者,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的翻译与研究”子项目负责人,2017年5月至6月任法国巴黎高师Labex TransferS研究中心讲座教授。1999年以来发表译著百余万字,学术论文数十篇。著译作品曾荣获第五届(2001)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中国文联第七届(2010)文艺批评奖、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一届(2013)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代表译作有加缪《第一个人》、杜拉斯《爱》、罗曼?罗兰《名人传》、托多罗夫《我们与他人》等。
近年来,中国学界在翻译研究上的文化转向,引发了对翻译伦理问题的热烈讨论。翻译行为的实施主体——译者,面对被语境化和历史化了的文本,该如何处理“异与同”、“我与他”的关系,这是“翻译伦理”将讨论涉及到的最主要问题。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实施主体,译者在具体实践中全程都无法回避“忠实还是叛逆”的选择,他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必定体现了他的文化伦理观。那么,怎样才是“合乎伦理”的翻译主体性呢? 第一节 西方翻译研究的伦理回归 所谓伦理,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遵守的道德关系准则。《哲学大辞典》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把伦理界定为“道德关系及其相应的道德规范” 。即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寻找合理合法的准则或规范。翻译伦理,就是在翻译的实践过程和翻译结果上,进行是非判断。翻译伦理不应该等同于翻译规范,而是要强调译者主体在诗学、文化、社会和政治环境中的道德自省和自知能力。翻译活动是一项具有人文意义的活动,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具体实践,不光源出语文化会受到译入语文化的推广,译入语文化显然也会由于从源出语引进来的新鲜元素,而得到进一步的建构。因此,翻译伦理的研究具有非常强大且广泛的文化意义。传统译学围绕翻译规范、翻译标准等等的探讨,都忽略了翻译活动实施行为的核心——译者主体,经验派译论也好,盛行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语言学译论也好,都表现出了对译者主体性关照的明显缺失。 译者的主体风格,来源于译者个人的文化修为和审美爱好。译者的主体意识,还包括译者对自己在跨文化交流实践中所担负的文化使命的认识,他不光是要帮助母语文化的读者了解异质文化,还要帮助提升和扩充自己的母语词汇,建构自己的母语文化。对于源出语的文化而言,译者的主体性还体现在他翻译完成之后的后续行为和后续活动之中,比如他为译本写的序言、后记,他与读者的互动,对该作品进行反馈、评论反映至源语文化中,从而也会促进源出语的读者重新认识原著,重新考量和认识自己母语的文学传统。本书后文中将有一章详细分析“中法文化的摆渡者”程抱一先生,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 传统的翻译伦理,表现在对于“忠实”、“对等”、“信达雅”等原则的具体遵守。这一伦理层面上对译者的要求,并不能帮助译者更好地认识翻译的本质问题和文化特性。当代哲学诠释学理论对于文本意义的重新解释,后结构主义者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使得传统的翻译理论以“忠实”概念为核心的翻译伦理观受到了质疑。绝对的“忠实”是没有的,传统的翻译伦理因而站不住脚。随着文学翻译主体性的彰显,人们认识到由于社会文化因素和政治权力因素的介入,翻译研究应该跨越传统伦理,从全球化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译者主体的伦理追求。学界普遍认为,上个世纪末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干将韦努蒂 、皮姆 、切斯特曼 和斯皮瓦克 等是较早议及翻译伦理的专家。而事实上,法国学者安托瓦纳?贝尔曼早在1984年和1985年的两部著作里,就将“回归伦理” 这一概念,作为文化派的“翻译宣言”核心内容提了出来 。可以说安托瓦纳?贝尔曼是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西方学者。可惜贝尔曼1991年英年早逝,1995年和2008年,贝尔曼的夫人又为他整理出版了两部遗著《翻译批评论:约翰?邓恩》和《翻译的时代》,“翻译的伦理性”仍然是其中的核心概念。我们很乐意在此借用这位法国学者的理念来探讨译者主体的伦理问题。 迄今为止,贝尔曼的译学专著存世四部,每一部都在西方译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可以说,其富有前瞻性的有关伦理的哲学思考,启发了每一位后来的文化学派翻译研究者。贝尔曼认为“翻译有三大极限目标:伦理性,诗性和哲学性。”贝尔曼所说的“翻译伦理性”,不仅仅意味着传统意义上译作的忠实度和准确性,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将他者作为他者本身予以承认和接受。”他提出在翻译过程中,应该进行的是“面向异的教育”,即要求译入语文化承认并接纳源语文化的“异”,将其植入体内,使译入语文化成为源语“远方的客栈”,依附于“文字忠实”的手段,实现理想的“翻译伦理”。贝尔曼的理想翻译是“文字翻译”(la traduction de lettre),此处lettre一词,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字和词。它富有更广泛的含义,是“与文字密切相关的一切”,与本雅明所提出的“纯语言”概念类似。在对待“异”的态度上,贝尔曼选择了母亲般的慈祥与包容:“在异者自身的语言空间内打开异者。”不强制,不敌视,更不试图去征服,而是触碰异者、接纳异者。翻译是什么?在贝尔曼看来,翻译是将“自我”置于“他者”——即“异”的考验之下的场所。一反“美丽的不忠”、“本族中心主义”式的意译和超译,贝尔曼推崇荷尔德林、夏多布里昂式的“文字翻译”。“翻译伦理性、诗性和哲学性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在译入语语言中保留翻译的新鲜面孔,展示它纯粹的新。”贝尔曼以这样一种开阔的胸怀,面对异域文化进行思考,目的就是要滋养译者身处其中的本土文化,改造和丰富本土文化。 第二节 当代中国呼唤怎样的“翻译伦理”? 安托瓦纳?贝尔曼的著作,语言深邃而富有思想的光辉,但由于其观点的“叛逆”,一时曾在西方招来不少指责和攻击。但同时,或者说短短几年之内,他的学说仿佛一阵风,刮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译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也找到了大批的拥趸。无疑,贝尔曼是富有批判精神的,他的理论之所以在西方获得了较高的地位,是因为他质疑了西方百余年来的意译传统。 然而,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下,贝尔曼及其他西方翻译文化学者们所主张的“翻译伦理”观,是否也值得中国学者们大书特书呢?我们的翻译研究界在引进这一思想和理念的同时,是否多了一点盲目(如同其他一股脑儿照搬来的理论一样),少了几分反思呢?中国自“五?四”以来至于当下,整整九十年,大多是处于主动接受他族文化改造和丰富的时期。吾国吾民领略西方世界的强大日久,似乎早已习惯于以仰视的姿态去领受西方的文化和文明。观现今中国之潮流文化,绝不仅仅是“将他者作为他者本身”,而是“视他者为神圣”。无论是畅销读物,还是西方学术著作的引进浪潮,以西词乃至西式句法来取悦受众、欺世盗名者累出不穷,真正严肃、严谨的文学翻译和学术研究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当代中国究竟应该呼唤怎样的一种“翻译伦理”,恐怕不应该是照搬那么简单吧。一百年前中国新文化运动发轫之初,钱玄同、傅斯年、吴稚晖、陈独秀等新文学的先锋人物曾主张废国文,兴拼音文字。但这些人本身的旧学功夫深邃,中文功底深厚,痛陈文言末流的种种弊病,提倡文字西化,他们算是有资格的。而他们的文字,无论怎样存心西化,都如余光中先生所言,是能“西尔化之”的。如今中国的大学生,甚至大学者,其笔下的中文翻译早已是“西而不化”,“文字忠实”早已有过度之嫌。若将贝尔曼的“文字翻译”和“翻译伦理”观点,当做今天之“他族崇拜主义”者的挡箭牌,岂不是有误于广大西学爱好者,更有辱于贝尔曼的英名了。 举个例子,上海电视台曾经有个清谈节目,所谓“锋言锋语”。请注意,“风”字已遭篡改。主持人抛出运动员的心理问题,说“姚明何必care他歌唱得好不好,刘翔何必care他棋下得怎么样,只要不care别人说什么,一切就ok了。”我们不知道这算不算得是某种“文字翻译”,但如果这样的媒体语言任其发展,中文的式微想必要万劫难复了。英语的围困,网络语言的失控,翻译腔的大行其道……当一个民族的语言生存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文学翻译是否还要鼓吹什么“异化”和“移植”呢?伦理本无所谓对错,矫枉犹不必过正。面对中国当下汉语发展的现状,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对目前理论家们热议的“翻译伦理性”,作一个新的考量。 在西人追求文化“他者性”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该蓦然回首,重新审视一下“自我”呢?贝尔曼及其他西方翻译文化学者们所主张的“翻译伦理”观,本身是值得称道的。因为西人背靠强势文化,谈及翻译时能以开放、对话的姿态抵抗“本族中心主义”,在翻译研究中秉持“存异为异”的伦理模式,的确是值得国人尊敬和效仿的。但对于我辈学人而言,当下中国的文化语境,还是要求我们从“他族崇拜主义”中走出来,学学钱钟书,学学傅雷,学学余光中等,是时候回归汉语“雅言”的传统了。贝尔曼等西方文化派的“翻译伦理”是否该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怎样拿捏这个“异化”还是“归化”的度,怎样帮助译者主体处理好“我与他者”的关系,最终寻求一种对话、平衡、自省的解决方案,这正是值得中国翻译研究界再三斟酌的伦理问题。 今天我们的译学界应该呼唤汉语文字的复兴,而不是文字的革命。让我们如十六世纪的法国七星诗人一样,在从事文学翻译时竭力“保卫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字”!待得文学翻译界一片“归化”之声,归得“忘乎所以”之时,再找贝尔曼求救,这才称得上是对症下药吧。 第三节 自我与他者:动态伦理中的翻译主体性 上文提到,以译者-译本-接受者为核心构成的翻译活动诠释循环圈,其中重要的问题是:翻译的主要目的和动机是指向译本的接受圈,于是我们必然要考虑到译本之接受的可能存在空间。但是翻译活动实际上还有另一重目的,那就是基于本雅明对于“纯语言”的追求,以及安托瓦纳?贝尔曼对之所做出的解释 :翻译不只是为了不懂原文语言的读者而做的,译者的任务(La t?che du traducteur)还在于揭示语言背后的东西,找到不同语言的差异之处,通过差异寻回人类语言的最初状态(尽管事实上,已经碎了的语言片断是永远无法完美拼接的),那个永远高高在上的悬搁的“真”。有了这样的一重理解力,所谓“文学翻译没有定本”,“重译具有必然性”等等问题便不容置疑。 繁多的人类语言不过是些分裂后的碎片。以所有的语言碎片为基础,也许就可以获得最完全的纯语言。这就是本雅明花瓶的比喻,单个比较的话,这些语言“瓶子”的碎片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因此在这些语言碎片中寻找“相似”之处,是毫无意义的;而真正的意义在于把碎片重新组合。这便是译者的“任务”:把碎片语言组合“完整”,呈现出完好的纯语言,至少要是它的投影。 在巴别塔停建后的世界里,语言的“同一性”已被上帝打破,翻译成了人类交流和文化传播不可或缺的工具。千百年来形成的译学传统围绕着翻译的核心——理解与表达而展开,人们正是由于过分看重翻译的“忠实属性”,强调译文与原文的对等,才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展开无休止的争论。而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都是人为创造的,并且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语言本身并没有确定的含义,语言具有的所谓含义都是人为赋予的,更何况这种赋予是任意的。西方表音文字的语音与语义之间结合的任意性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在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符号系统,只能在“所指”层面达到一定的共享,建立在绝对正确理解上的忠实翻译,只能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梦想。然而,生活中总是存在着这样的悖论——越是不可能的事情,就似乎越具有必要性。人类重建“通天塔”的愿望就从来不曾放弃,如今“上帝死了”,翻译已成为事关人类自身生存的伟大事业。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承认真理存在的相对性,甚至承认无限接近而永不可得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美,那么,翻译何以不能成为一种绝望背景下的、“西西弗斯”式的悲壮而勇敢的努力呢?至此便诞生了一个迫切的追问——翻译在多大意义上是可能的?也许历经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伦理探讨的当代翻译学理论,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作者、译者、译文读者这三种平等的主体,六大阐释循环圈,使得翻译已不再满足于维持或再现原文的意图,而要从“源语中心”朝“译语中心”转向。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力求在语言维度、文化维度的转换上,与源语保持高度的关联,同时顺应译语的文化语境,对原作者的意图进行操纵性的重构。采用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不断地做出优化的译文选择,让译文读者轻松地获得作者试图传达的语境效果,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效果,这恐怕才是最终的出路。 今天,在译学研究的文化学派眼里,译文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原文,影响着译入语文化的诗学传统和多元文学体系。比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就颠覆了“原作是神圣且至高无上”的传统译论,尤为看重翻译的文化意义,更突出译文中的异质性,来抵抗主流的译入语文化的价值观。劳伦斯?韦努蒂极为赞赏法国学者贝尔曼的“还异为异”主张,提出了“存异伦理”和“存同伦理”的概念 ,认为只有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才能更好地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文化。安东尼?皮姆在名为《回归伦理》的一组文章前言中,强调翻译伦理在当下的跨文化交流语境中应该是首先考虑的问题。安德鲁?切斯特曼在《关于圣哲罗姆誓约的提议》一文中总结了回归伦理的五种模式 :表现的伦理,服务的伦理,交际的伦理,规范的伦理和承诺的伦理,进一步对译者主体的个性禀赋和自律性提出了要求。近年来,我国的翻译学界也有对于翻译伦理非常出色的讨论,其中段峰在其专著《文化视野下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中,对于译者主体性、翻译规范和翻译伦理的关系梳理十分清晰。王大智在2012年出版了《翻译与翻译伦理:基于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思想的思考》,以发生在传统中国的两次大规模翻译运动为历史与实践参照,运用多种相关理论,对华夏民族的传统翻译伦理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翻译伦理是多元的,也是流动的、不断发展演进的,其回归为更好地解读文学翻译主体性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 \"【编辑推荐】:本书建立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翻译主体研究”理论模型,走出文本、转向主体,聚焦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上海文学翻译家群体,阐明了文学翻译家在历史与当代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和关键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