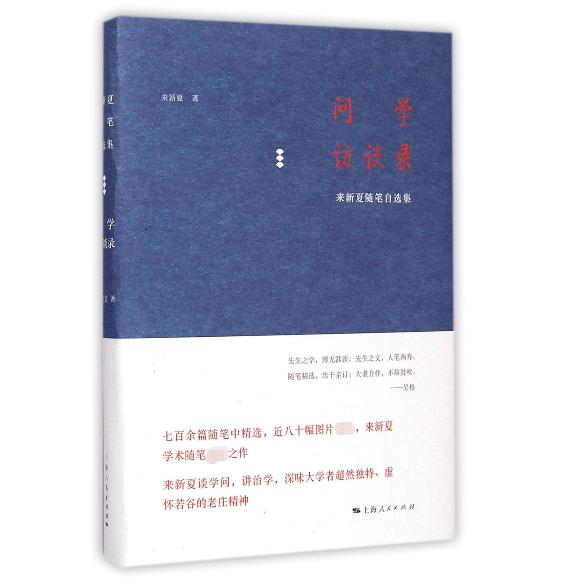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人民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5.00
折扣购买: 问学访谈录(来新夏随笔自选集)(精)
ISBN: 9787208127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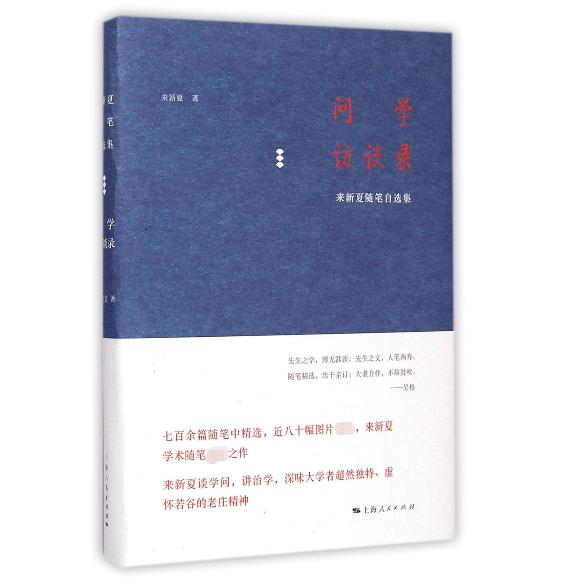
来新夏(1923-2014),浙江萧山人,字弢盫。194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主要从事历史学、目录学和方志学等研究,被誉为“纵横三学”。著有《清人笔记叙录》、《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古典目录学》、《北洋军阀史》、《中国图书事业史》、《中国地方志》等。“纵横三学”的来新夏先生“衰年变法”,晚年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随笔大家。
我的学术自述 1923年的夏天,我出生在江南名城——杭州的一 个读书人的大家庭里。父叔常年谋食四方,家中事无 巨细都由祖父主持。祖父来裕恂先生是清末秀才,曾 从师于晚清国学大师俞樾。20世纪初,留学日本弘文 书院,学习教育。在日本期间,曾在同盟会主办的横 滨中华学校任教务长。回国后,经蔡元培介绍加盟光 复会,在家乡从事新式教育的劝学工作。辛亥以后, 他敝屣荣华,依然在 门和各类学校任职。他一 生潜研学术,寄情诗词,笔耕不辍。所著有《汉文典 》(清光绪商务印书馆刊印本、1993年南开大学出版 社注释本)、《匏园诗集》、《萧山县志稿》(以上二 书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史》(岳簏 书社出版)和《易经通论》(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等 多种。我七岁以前,一直随侍于祖父左右,生活上备 受宠爱。但祖父对我的教育却很认真,非常严格地对 我进行传统文化的蒙学教育,以三、百、千、千的顺 序去读,去背诵,还为我讲解《幼学琼林》和《龙文 鞭影》等蒙学书,为我一生从事学术活动奠定了入门 基础。祖父就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我七岁那年, 因父亲供职天津,即随母北上。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祖父,以后虽然再未和祖父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仍然 不时写信来,指导我读书和修改我的习作,直到他年 高辞世为止。 我从小学到大学遇到过不少良师,他们都从各个 方面给我日后的学术道路以重要的影响。20世纪的三 四十年代,我先在南京新菜市小学读高小时,级任老 师张引才是一位刻苦自学,博览史籍的好老师,他常 和学生一起,讲述有益于学生的历史故事。这些知识 的灌输,无形中奠定我日后攻读历史专业的根基。后 来我到天津一所中学读书,有一位年轻的国文老师谢 国捷,曾在辅仁大学专攻哲学,是史学家谢国桢的六 弟。安阳谢氏,家富藏书。谢老师又很慷慨倜傥,师 生问十分契洽,因此我得以借读谢氏藏书。谢老师还 常和我谈些治学方法和经验,鼓励我写文章。我的第 一篇史学论文《汉唐改元释例》初稿就完成于此时。 此文后来在陈垣老师的直接指导下,经过多次修改, 终于成为我的大学毕业论文。 40年代初,我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有幸亲受业 于陈垣、俞嘉锡、张星烺、朱师辙、柴德赓和启功、 赵光贤诸先生之门,他们都为我日后走上学术道路耗 费心血,特别是他们谨严缜密、求实求真的学风,成 为我一生努力追求的方向。可惜我资质驽钝,虽全力 以赴,至今未能达到师辈的期许,而深感有负师教。 当时正处于日寇侵华的沦陷区,老师们坚贞自守的爱 国情操,更是一种无言的身教。 我大学毕业时,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一一 1946年,人们的心情都很兴奋,以为可以报效国家, 有所作为。孰知事与愿违,政府的腐败令人大失所望 ,我无可逃避地像许多人一样,走上一条毕业即失业 的道路,虽然经过亲友的帮助,曾在一家公司谋得一 个小职员的工作,但为时不久,公司倒闭。又赋闲了 一段时间,才经读中学时一位老师的介绍,到一所教 会中学去教书。当时÷解放战争已临近全面胜利的边 缘,天津的解放指日可待,我也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一 些革命理论和思想的灌输,热切地期望着新生活的来 临。 1949年1月,天津解放给我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欣 悦。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我积极投身于新的革命工 作。不久,经民青驻校领导人的动员,我和另一位同 事张公辅被保送到华北大学去接受南下工作的政治培 训。于是,脱去长袍,穿上用紫花(据说是一种植物) 煮染过的粗布所缝制的灰制服;不惜抛去优厚的工薪 制,而去吃小米,享受大灶供给制。一股唐·吉诃德 般的革命热情产生着革命的冲动。为了和旧思想、旧 习俗等旧的一切割断,做个新人,我们又学习那些先 行者改名换姓的革命行动,偷偷地商量改名问题。张 兄想今后要在革命大道上奔腾,就利用名字中骕字的 马旁,改名马奔。我则用名字的最后一字“夏”与“ 禹”相连而改姓禹,又大胆地以列宁自期,取名一宁 ,暗含着彼一宁也,我一宁也,也许有一股将相宁有 种乎的傲气。张兄一直沿用马奔这个革命名字,我则 幸亏以后又恢复了原姓名,否则“文化大革命”中这 将是一条大罪状——居然敢以列宁自期。政治培训期 满后,张兄南下到河南,我则被留在华北大学的历史 研究室,师从范文澜教授,做中国近代史研究生。从 此我就从古代史方向转到近代史方向,并在范老和荣 孟源先生指导下写出第一篇学习新观点的文章——《 太平天国底商业政策》,作为太平军起义百年的纪念 。 当时历史研究室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从整理北洋 军阀档案人手。这批档案是入城后从一些北洋军阀人 物家中和某些单位移送过来的藏档,没有作过任何清 理和分类。这批档案有百余麻袋,杂乱无章,几乎无 从下手,每次从库房运来几袋就往地下一倒,尘土飞 扬,呛人几近窒息。当时条件很差,每人只发一身旧 紫花布制服。每天工作时就戴着口罩,蹲在地上,按 档案形式如私人信札、公文批件、电报电稿、密报、 图片和杂类等分别打捆检放到书架上。因为每件档案 都有脏污之物,要抖干净就会扬起尘土,整天都在爆 土扬尘中过日子,所以每天下班,不仅浑身上下都是 土,就连眼镜片上都厚厚地积了一层灰尘。同事们看 着对方鼻孔下面一条黑杠,往往彼此相视而笑,但从 没有什么抱怨。在整理过程中,因为急于想闯过这个 尘土飞扬的阶段,工作速度较快,所以除了知道不同 形式的档案和记住一些军阀的名字外,几乎很难停下 来看看内容,只能说这是接触北洋军阀档案的开始而 已,还谈不上什么研究。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