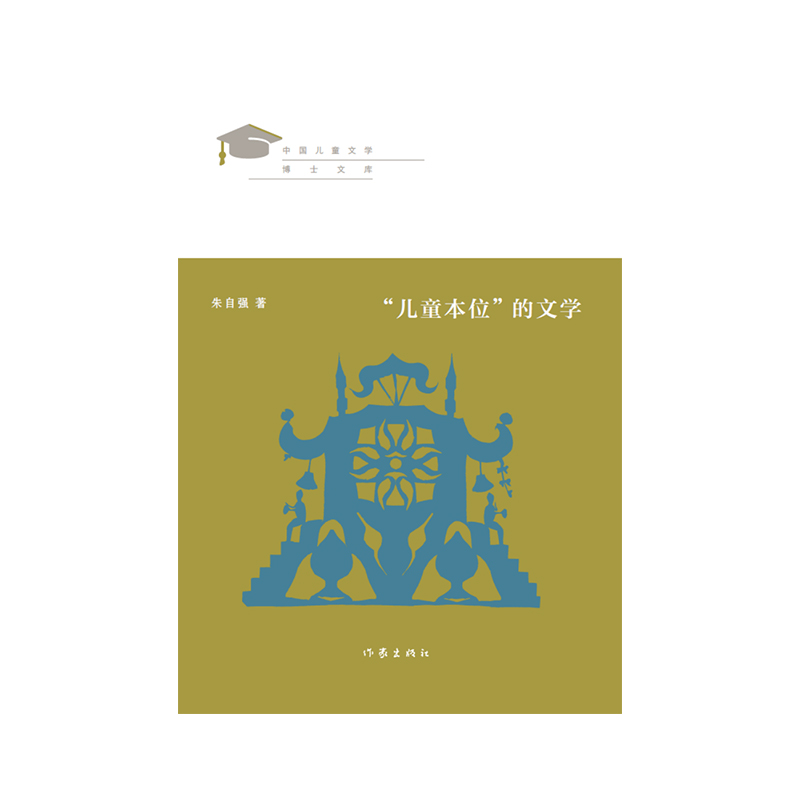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60.00
折扣价: 36.00
折扣购买: “儿童本位”的文学
ISBN: 97875212128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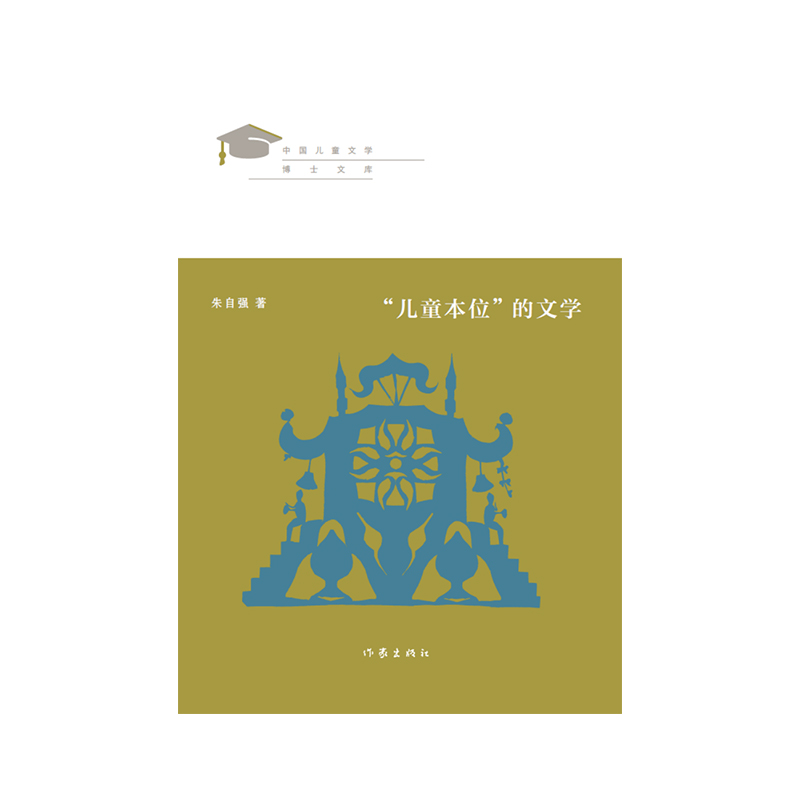
朱自强,学者、翻译家、作家。中国海洋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行远书院院长,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第十八届国际格林奖获得者。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主要学术领域为儿童文学、语文教育、儿童教育研究。出版《朱自强学术文集》(10卷),著有个人学术著作20种,代表作有《儿童文学的本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儿童文学概论》《日本儿童文学论》《中外儿童文学比较论稿》《儿童文学:学科与建构》《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法》等。
“儿童本位”的文学 ——我的儿童文学观 2021年,是我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第四十个年头。在那一年,又恰好是我六十四岁生日的那一天,国际格林奖评奖委员会通知我获得第十八届国际格林奖。“国际格林奖”与“国际安徒生奖”一起被誉为两大世界性儿童文学的最高奖项。与奖励儿童文学创作的国际安徒生奖不同,国际格林奖奖励儿童文学学术研究。这一奖项每两年评选一届,每届全世界范围内只评选出一位学者予以奖励。在我从事儿童文学研究整整四十年之际,获得国际格林奖,是对自己儿童文学研究的莫大的肯定和鼓励。 检验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的品质,主要不是看其文字数量有多大,论文发表的刊物级别有多高,获得的项目有多少,获得的奖项有多高,而是看其有没有独到而重要的学术发现,有没有系统性的理论建构,有没有广泛而持久的学术影响。对于儿童文学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建构出明晰的、系统的、具有实践有效性的儿童文学观。 在国际格林奖评奖委员会的颁奖词中,对我的儿童文学学术研究作了这样的概括——“践行以儿童为本位的思想理念和研究方法,是他的学术研究的特质。”读这句话,我有如遇知音、如逢甘霖之感。四十年来,“儿童本位”的思想和方法,不仅成为我的学术根基,而且弥散到我的每一篇文章,浸润进我的每一句言辞,甚至是潜意识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儿童本位”的文学》,是我至今为止出版的十余种文集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因为它系统地、全方位地呈现了我在四十年里殚精竭虑地建构起来的儿童文学观——“‘儿童本位’的文学”。 早在1997年,我就在《儿童文学的本质》一书中说:“‘儿童本位的文学’是我所选择的理想地表述了儿童文学本质的简洁用语。”研究科学方法论的科学家修·高奇归纳说:“一般的方法论原理涉及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概率论、简约性和对假设的检验。”他特别指出:“简约的模型经常能够得出更高的准确性……”作为一个想在方法论上努力会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者,我认为,“‘儿童本位’的文学”就是一个具有更高准确性的“简约模型”。能否简约表述,是思想是否清晰的表征,也是更可能具有科学性的一个验证。虽然我经常在自己的著述中论述儿童文学是“‘儿童本位’的文学”这一观念,甚至有论文的题目就是“儿童文学:儿童本位的文学”,但是,想到以“‘儿童本位’的文学”作为本文集书名的那一刻,还是有一种思想被透彻照亮的感觉。“‘儿童本位’的文学”,它不仅是对迄今为止自己最看重的一本文集的命名,而且也是对作为儿童文学学者的我自己的一次身份命名。 “儿童本位”论是贯穿于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历史的最重要的本土儿童文学理论,它源自于五四时期的周作人等人的阐发,经过当代一批学者的理论诠释和作家的创作实践,已经成为儿童文学研究和创作中最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思想。当然,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对“儿童本位”论有不尽相同的阐释。在儿童文学学术领域,我本人可以说是当代“儿童本位”论的大声疾呼者、全力建构者。学者眉睫就有这样的评价:“朱自强等理论家重提‘儿童本位论’,并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和内涵。……尤其可贵的是,朱先生将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注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新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儿童本位论’。” “儿童本位”论不仅是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理论,而且在国际儿童文学学术领域,“儿童本位”论也应该具有非常有效的阐释力。以我个人为例,《佩里·诺德曼的误区——与〈儿童文学的乐趣〉商榷》《儿童文学的人生观及其方法论》这两篇与西方知名学者对话、辩驳的论文,就都用了“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 在这部文集中,开篇的《引言》是10卷本《朱自强学术文集》的自序,构成我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形成和发展的整体背景;第一辑是对中国儿童文学历史上的“儿童本位”论的钩沉和梳理;第二辑呈现的是我本人建构的当代“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第三辑是我运用“儿童本位”理论进行的儿童文学批评,可以证明“儿童本位”理论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史论、理论、批评这三大领域几乎涵盖了儿童文学的全部学术版图。我希望读者能够感受到,我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已经全面而深入地渗透到了我的史论、理论、批评的字里行间。如果抽去“儿童本位”的思想和方法,我的儿童文学学术研究将不复成立。 下面,我想从“政治”、历史、哲学这三个维度来阐述我的“儿童本位”论的学理依据。 儿童文学的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要处理好作为儿童文学创作者、研究者、给予者的成人与作为儿童文学接受者的儿童之间的权力关系。在这一“政治”维度上,我主张儿童文学是“儿童本位”的文学。 在中国,有学者认为,强调“儿童本位”,容易造成单方面的对儿童的顺应,也有学者认为,“本位”总是以排除“对象”的存在价值为前提和标志。但是,在我所阐释的“儿童本位”论中,成人并不是单方面地顺应儿童,成人与儿童并不是相互对立和“排除”的关系,而是融合的关系和相互馈赠的关系。归根到底,我以“儿童文学”来实现人生的理想,对成人与儿童可以形成和谐互赠的关系持有信心。因此,我也不能同意杰奎琳·罗丝的“儿童文学是一种殖民(或破坏)儿童的方式”、佩里·诺德曼的“儿童文学代表了成人对儿童进行殖民统治的努力”这两个内涵一致的全称式判断。在这样的判断里,成人彻头彻尾地成了儿童的压迫者。 儿童文学为什么要以儿童为本位?因为“儿童是最为弱小的存在,他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大人的手里。儿童无法像妇女发动一场女权运动那样,为自己发动一场童权运动。也就是说,儿童与成人之间,有着其他任何人际关系都没有的特殊关系。因为生命的不同存在形式,儿童的解放并不能由儿童自己,而要由成人来帮助其完成。成人社会要完成这一解放儿童的事业,唯有以儿童为本位,这是由迄今为止的历史所充分证明了的”。 从历史的维度来探讨儿童文学观,我主张任何国家的儿童文学都是“现代”文学,而不是“古已有之”。探究儿童文学的发生,可以看清儿童文学的本质。在中国,儿童文学是在从古代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代孕育、出生、成长起来的,其发生的标志,就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出现。 “现代性”是至今为止的儿童文学的重要属性,在中国,其最为重要的思想就是“儿童本位”的儿童观。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兴起,“现代性”成了这种理论企图超越的对象。但是,“我对于哈贝马斯将‘现代性’视为‘一项未竟的事业’,抱有深切同感。现代性思想的相当大部分,依然适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这个正在建构‘现代’的具体的历史语境里,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的时代里,我们只能、只有先成为现代性的实践者。不论在现在,还是在将来,这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合法性。至少,我们也得在自己的内部,使‘现代’已经成为一种个人传统之后,才可能对其进行超越,才有可能与‘后现代’对话、融合”。 从哲学维度来探讨儿童文学观,我认为,儿童文学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观念。儿童文学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个实体(一个个作品构成的实体)。作为观念的儿童文学就是一种世界观,是关于人生的价值观的言说。儿童文学言说的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谬误,关键取决于论者主张的是何种形态的儿童文学观。 实体论儿童文学观是一种具有本质主义色彩的思维方式。我反对本质主义,主张的是建构主义的本质论。在建构主义的本质论看来,没有绝对的、固定不变的真理,只有历史的真理。“‘儿童本位’论就是历史的真理。‘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依然拥有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性和力量’。 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对于以成人为本位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都是端正的、具有实践效用的儿童文学理论。它虽然深受西方现代思想,尤其是儿童文学思想的影响,但却是中国本土实践产生的本土化儿童文学理论。它不仅从前解决了,而且目前还在解决着儿童文学在中国语境中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作为一种理论,只有当‘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已经失去了效用,才可能被‘超越’,反之,如果它在实践中能够继续发挥效用,就不该被超越,也不可能被超越。至少在今天的现实语境里,‘儿童本位’论依然是一种真理性理论,依然值得我们以此为工具去进行儿童文学以及儿童教育的实践。” 总而言之,从“政治”维度、历史维度以及哲学维度对儿童文学的本质进行学理上的思考之后,我必然会怀着自信,走向“儿童本位”论这一儿童文学观。 朱自强 2023年2月16日 于中国海洋大学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中心 “儿童文学博士文库”的出版,既是对儿童文学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的有力支持,同时也是促进新时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有力举措。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世纪以来我国自主培养的这一大批儿童文学博士生,正在成长为新一代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他们中的拔尖人才,已成为当今知名的理论批评家、作家、出版家与阅读教学专家,是中国儿童文学新一代的理论批评、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的接力者、领跑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儿童文学理论家 王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