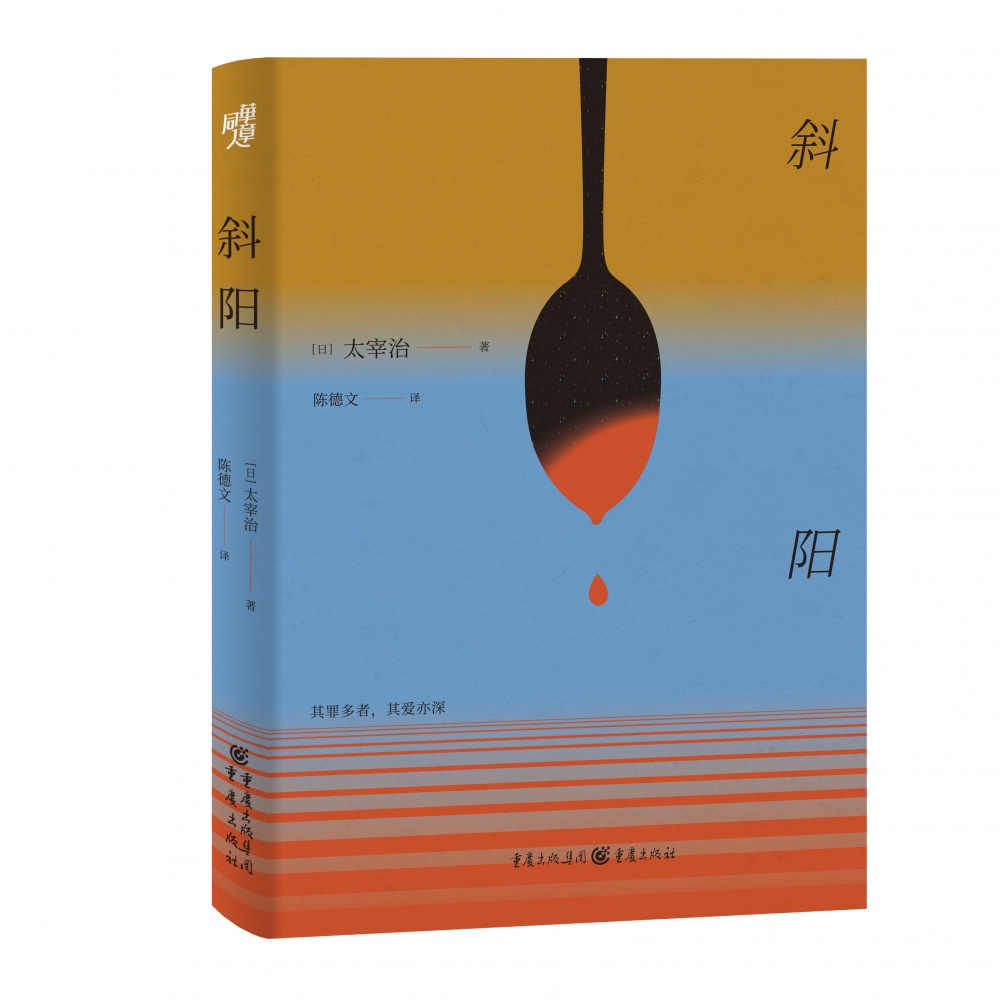
出版社: 重庆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7.90
折扣购买: 太宰治名家经典系列:斜阳
ISBN: 9787229156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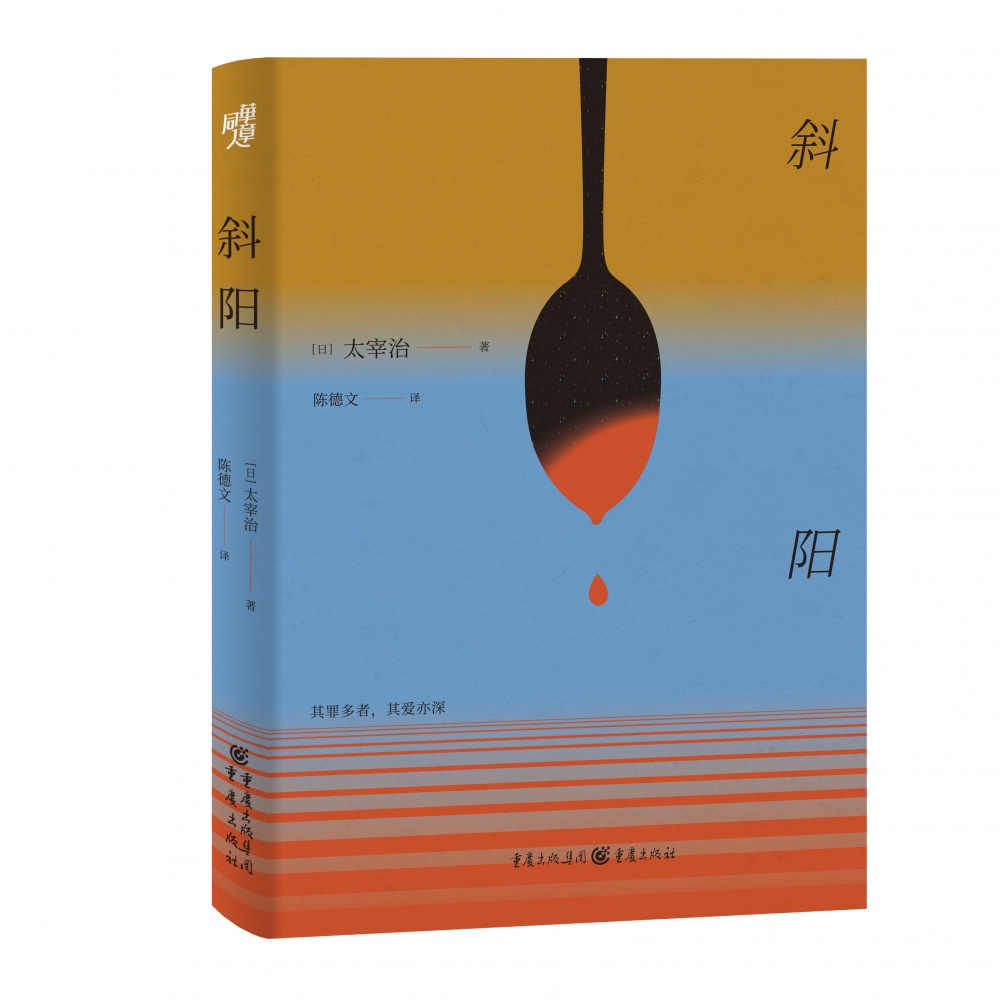
太宰治(1909—1948),户籍原名津岛修治,日本无赖派代表作家,青年时期的太宰治,思想支离破碎,精神极不安宁,这期间的作品以作品集《晚年》为首,还有《逆行》《小丑之花》《玩具》《猿岛》《创世纪》《二十世纪旗手》和《HUMAN LOST》等,内容多属于描写个人生活的私小说范畴。 太宰同石原美知子结婚后,在亲友和社会的救援下,不安的灵魂渐趋稳定,立志做一名“市井的小说家”。这个时期的作品,个性鲜明,笔墨多彩,文字细腻,佳作叠出。举其要者有《富岳百景》《奔跑吧,梅勒斯》《女生徒》《新哈姆莱特》《正义和微笑》《归去来》《右大臣实朝》《故乡》和《潘多拉的盒子》等。该系列作品内容多触及严肃的社会问题,但格调明朗而不沉郁,行文轻捷而不浮华,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战后三年,战争的创伤再度引起作家精神的不安定,这是太宰文学走向成熟和个体毁灭的悲壮时期。留下《维庸之妻》《斜阳》《樱桃》和《人间失格》等作品后,猝然陨落。 在日本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太宰治以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腻敏感,表达了对社会以及人生的思考,因此被称为“日本昭和时代不灭的金字塔”。 译者陈德文,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译有日本文学名家名著多种,包括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夏目漱石、岛崎藤村等人的小说十余部,以及松尾芭蕉、幸田露伴、岛崎藤村、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散文集,如《春雪》《金阁寺》《斜阳》《草枕》等,著有《岛崎藤村研究》《我在樱花之国》《花吹雪》《樱花雪月》《岛国走笔》等。
一 早晨,母亲在餐厅里舀了一勺汤,“嘶”地啜了进去。 “啊!”她低低地惊叫了一声。 “是头发吗?” 汤里想必混进什么不洁的东西了吧,我想。 “不是。” 母亲若无其事地又舀了一勺汤,动作灵巧地送进嘴里,然后转头望着厨房窗外盛开的山樱花,就那么侧着脸,又动作灵巧地舀一勺汤,从小小的嘴唇缝里灌了进去。“动作灵巧”这种形容,对母亲来说一点儿也不夸张。母亲的进食方法,和妇女杂志上介绍的完全不一样。弟弟直治有一次一边喝酒一边对我这个姐姐说过这样的话: “有了爵位[ 贵族的种别。《明治宪法》下编(明治—昭和二十二年,1868—1947)“日本”条记有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等级。 ],不等于就是贵族。没有爵位的人,也有的自然具有贵族高雅的品德。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有的光有爵位,根本谈不上贵族,仅仅接近于贱民。像岩岛(直治举出同学伯爵家的名字)那种人,给人的感觉甚至比新宿的游廓[ 即妓院。游廓作为甲州街道的宿场,自古有之,当时集中于新宿二丁目一带闹市。 ]拉客的鸡头还要下贱,不是吗?最近,柳井(弟弟又举出同学子爵家次子的姓名)的哥哥结婚,婚礼上瞧他那副德性,穿着简易的夜礼服,有必要穿那种衣服吗?这还不算,在致辞的时候,那家伙一个劲儿运用敬语表达法,实在令人作呕。摆阔和高雅根本沾不上边儿,他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本乡[ 东京文京区地名,东京大学所在地。 ]一带有很多挂着高级宅第的牌子,实际上,大部分华族[ 《明治宪法》下编身份制度的名称。初指江户时代的公卿、诸侯。明治十七(1884)年华族令规定,除授予爵位者外,为国立功的政治家、军人、官吏、实业家等也包括在内。位于皇族下、士族上,享有种种特权。1947年废止。 ]可以说都是高等乞丐。真正的贵族,是不会像岩岛那般摆臭架子的。就拿我们家来说,真正的贵族,喏,就像妈妈这样,那才是真的,有些地方谁也比不上。” 就说喝汤的方式,要是我们,总是稍微俯身在盘子上,横拿着汤匙舀起汤,就那么横着送到嘴边。而母亲却是用左手手指轻轻扶着餐桌的边缘,不必弯着上身,俨然仰着脸,也不看一下汤盘,横着撮起汤匙,然后再将汤匙转过来同嘴唇构成直角,用汤匙的尖端把汤汁从双唇之间灌进去,简直就像飞燕展翅,鲜明地轻轻一闪。就这样,她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之中,轻巧地地操纵汤匙,就像小鸟翻动着羽翼,既不会洒下一滴汤水,也听不到一点儿吮吸汤汁和盘子碰撞的声音。这种进食方式也许并不符合正规礼法,但在我眼里,显得非常可爱,使人感到这才是真正的贵族做派。而且事实上,比起俯伏身子横着汤匙喝汤,还是微微仰起上半身,使汤汁顺着匙尖儿流进嘴里为好。而且,奇妙的是这种进食法使得汤汁更加香醇。然而,我属于直治所说的那种高等乞丐,不能像母亲那样动作轻巧地操纵汤匙,没办法,只好照老样子俯伏在盘子上,运用所谓合乎正式礼法的那种死气沉沉的进食方法。 不只是喝汤,母亲的进食方法大都不合乎礼法。上肉菜时,她先用刀叉全部分切成小块,然后扔下刀子,将叉子换在右手拿着,一块一块地用叉子刺着,慢条斯理地享用。遇到带骨的鸡肉,我们为了不使盘子发出响声,煞费苦心地从鸡骨上切肉时,母亲却用指尖儿倏地撮起鸡骨头,用嘴将骨头和肉分离开来。那副野蛮的动作,一旦出自母亲的手,不仅显得可爱,而且看上去很性感。到底是真贵族,就是与众不同啊!不光是带骨的鸡肉,午餐时对于火腿和香肠等菜肴,母亲有时也用手指尖儿灵巧地撮着吃。 “饭团子为什么那么好吃,知道吗?因为是用人的手指尖儿捏成的缘故啊。”她曾经这样说。 用手拿着吃的确很香,我也这么想过。可是像我这样的高等乞丐,学也学不像,只能是越学越觉得像个真正的乞丐,所以还是坚忍住了。 弟弟也说他比不上母亲,我也切实觉得学母亲太难,有时甚至感到很绝望。有一次在西片町住宅的后院,初秋时节月光皎洁的夜晚,我和母亲坐在池畔的亭子里赏月,娘儿俩说说笑笑,谈论着狐狸出嫁和老鼠出嫁时,配备的嫁妆有什么不同。说着说着,母亲突然起身,钻进亭子旁边浓密的胡枝子花草丛里,透过粉白的花朵,伸出一张更加白净的脸孔,笑着说: “和子呀,你猜猜看,妈妈在干什么?” “在折花。”我回答。 “在撒尿呢。”她小声地笑着说。 她一点儿也未蹲下身子,我感到很惊奇。不过我们是学不来的。我打心底里感到母亲很可爱。 正说着早晨喝汤的事,话题扯远了。不过,我从最近阅读的一本书上,知道路易王朝时代的贵妇人也在宫殿的庭院或走廊的角落里小便,她们根本不当回事儿。这种毫不在乎的行为实在很好玩,我想我的母亲不就是这种贵妇人中的最后一个吗? 再回到早晨喝汤的事儿上吧,母亲“啊”了一声,我问:“是头发吗?”她回答:“不是。” “是不是太咸了?” 早晨的汤是用美国配给的罐装青豌豆做底料,由我一手熬煮的potage。我本来对做菜没把握,听到母亲说“不是”,心中依然犯着嘀咕,所以又叮问了一句。 “味道挺好的。”母亲认真地说。 喝完汤,母亲接着伸手撮起一个紫菜包饭团儿吃了。 我打小时候起就对早饭不感兴趣,不到十点钟肚子一点儿不饿,那时候有点汤水就好歹对付过去了。我吃起东西来很犯愁,先把饭团子盛在盘子里,然后用筷子戳碎,再用筷子尖儿夹起一小块儿,照着母亲喝汤的样子,使筷子和嘴巴成为直角,像喂小鸡一般塞进嘴里。在我慢慢腾腾吃着的当儿,母亲早已全都吃好了,她悄悄站起身子,背倚着朝阳辉映的墙壁,默默看着我吃饭的样子。 “和子呀,这样还是不行,早饭一定要吃得香甜才是。”她说。 “妈妈呢?您吃饭很香吗?” “那当然,我已经不是病人啦。” “和子我也不是病人啊。” “不行,不行。” 母亲凄凉地笑了,摇摇头。 我五年前害过肺病,卧床不起。不过,我明白那是娇生惯养造成的。但是母亲最近的病症却使我甚为担心,这是一种很可怜的病。然而,母亲只是为我操心。 “啊。” 我不由“啊”了一声。 “怎么啦?”母亲问道。 两人互相望着,似乎都心照不宣。我吃吃地笑了,母亲也笑了起来。 每当心里有什么难为情的事儿,又忍耐不住的时候,我就会悄悄地“啊”一声。眼下我心里突然清晰地浮现出六年前离婚的事儿,实在忍不住了,才不由“啊”地叫出声来。母亲又是怎么回事呢?母亲不会像我一样有着难以启齿的过去吧?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事情呢? “妈妈刚才也想起什么了吗?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忘啦。” “我的事吗?” “不是。” “直治的事?” “对。” 说到这里,她又歪着头,说道:“也许是吧。” 弟弟直治大学中途应征入伍,去了南方的海岛,从此杳无音信,终战后依然下落不明,母亲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她说再也见不到直治了。可是我从来不需要这个“心理准备”,我想肯定还能见到弟弟。 “我虽然死心了,但喝到这么好的汤,就想起直治,心里受不住。要是对直治多疼爱些就好了。” 直治读高中时就一味迷上了文学,开始过着不良少年的生活,真不知给母亲招来多少辛苦。虽说这样,母亲依然一喝上一勺汤就想起直治,“啊”地惊叫一声。我将一口饭塞进嘴里,眼睛热辣辣的。 “没事儿,直治不会出事的。像直治这样的恶汉子是不会死的。死的都是老实、漂亮、性情温和的人。直治是用棍子打也打不死的。” “看来,和子也许会早死的吧。” 母亲笑着逗弄我。 “哎呀,为什么?我是个淘气包,活到八十岁看来没问题。” “是吗?这么说,妈妈可以活到九十岁啦。” “嗯。” 说到这里,心里有点儿难过。恶汉长寿,漂亮的人早夭。妈妈很漂亮,不过我希望她长寿。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快别捉弄人啦!” 说着,我的下唇不住颤动,眼泪扑簌扑簌涌流出来。 说说蛇的事情吧。四五天前的午后,附近的孩子们在院墙边的竹丛里发现了十几个蛇蛋。 “是毒蛇蛋!” 孩子们嚷嚷着,我想,要是那竹丛里生了十多条毒蛇,就不能轻易到院子里玩了。 “烧了吧。” 我一说完,孩子们就欢呼跳跃,跟着我走来。 大家在竹丛一旁堆起树叶和柴草,点着了火,将蛇蛋一个个投进火堆。蛇蛋不易着火,孩子们添加了不少树叶、树枝,增强了火势,蛇蛋还是着不起来。 下面的农家姑娘在墙根外边笑着问道: “你们在干什么?” “烧毒蛇蛋呢。一旦生了毒蛇,该多可怕呀。” “多大个儿呢?” “像鹌鹑蛋一样,一抹白。” “那么说是普通的蛇蛋,不是毒蛇蛋。生蛇蛋是不会着火的。” 姑娘感到奇怪,笑着走开了。 火着了三十分钟,蛇蛋就是不燃烧。我叫孩子们从火里捡出蛇蛋,埋在梅花树下,垒上小石子作为墓标。 “来,大家一起拜一拜吧。” 我蹲下身子,双手合十,孩子们也都顺从地蹲在我身后合掌拜祭。然后,我告别孩子们,一个人独自缓缓登上石阶,只见石阶上头,母亲站在藤架荫里。 “你干了件可悲的事啊。”她说。 “以为是毒蛇,谁知竟是普通的蛇蛋。不过,都掩埋好了,没问题的。” 我虽然这么说,但觉得被母亲看见总是不太好。 母亲并不迷信,可是十年前父亲在西片町家中去世后,她非常害怕蛇。据说父亲临终前,母亲发现父亲的枕畔掉落一根又细又黑的线绳儿,她毫不经意地拾起来一看,是蛇!眼见着那蛇很快地逃走了,顺着走廊不知钻到哪里去了。看到这条蛇的只有母亲与和田舅舅两个人,姐弟二人面面相觑,但为了不惊扰前来送终的客人,将这事隐瞒了,没有声张出去。我们虽说也都在场,可关于蛇的事一点儿也不知道。 但是,父亲死去那天晚上,水池边的树木全都爬满了蛇,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我已经是二十九岁的老大妈了,十年前父亲去世时我十九岁,早已不是小孩子了,现在又过了十年,当时的记忆依然十分清晰,一点儿都不会错的。我为了剪花上供,来到池畔,站在岸边杜鹃花丛中。突然,我发现杜鹃花的枝子上盘着一条小蛇。我不由一惊,又想攀折一枝棠棣花,谁知那枝条上也盘着一条蛇。相邻的木樨、小枫树、金雀花、紫藤、樱树,不论哪种树木上都一律盘着蛇。可我并不怎么害怕,我只是认为,蛇也和我一样,对于父亲的辞世感到悲伤,一齐爬出洞来祭拜父亲的亡灵吧?于是,我把院子中出现蛇的事悄悄告诉了母亲,她听罢有些担心,歪着头思考了一阵子,可也没再说些什么。 不过自从出现这两件有关蛇的事之后,母亲就非常讨厌蛇,这倒是事实。说是讨厌,其实是更加崇拜蛇,害怕蛇,对蛇抱着满心的畏怖之情。 母亲看到烧蛇蛋,肯定会感到很不吉利,我也觉得烧蛇蛋这种事儿太可怕了。这件事会不会给母亲带来厄运呢?我担心又担心,第二天,第三天,都忘不掉。今天早晨在餐厅里又随便扯到美人早夭这类荒唐的事,真不知如何补救。早饭后一边拾掇碗筷,一边感到自己身子里钻进了一条可怕的小蛇,它将缩短母亲的寿命,我一个劲儿哭泣,打心眼儿里腻歪得不得了。 而且,那天我又在院子里看到了蛇。那天天气特别和暖,我做完厨房的事儿,打算搬一张藤椅放在院中的草坪上,坐在那里织毛衣。我搬着藤椅刚走下院子,就发现院中石头旁的竹丛中有蛇。哎呀,真讨厌,我只是这么想着,没有进一步深思下去,又搬着藤椅回到廊缘上,坐在上头织毛衣。午后,我想到庭院一角佛堂里的藏书中找一本罗兰桑画集,刚走下庭院,便看到草坪上有条蛇在缓缓爬动,和早晨那条蛇一样。这是一条纤细的、高雅的蛇。我猜是条女蛇。她静静地穿越草地,爬到野玫瑰花荫里,停住了,抬起头来,抖动着细细的火焰般的信子。看她那姿态,仿佛在打量着四周,过了一会儿,又垂下头,忧戚地盘绕在一起。当时,我只认为这是一条美丽的蛇,过了一会儿,我把画集拿回佛堂,回来时瞥了一眼刚才蛇盘桓的地方,已经不见蛇的踪影了。 黄昏将近,我和母亲坐在中式房间里饮茶,朝院子里看时,石阶第三级的石头缝里,早晨那条蛇又慢腾腾地爬出来了。 “那蛇怎么啦?” 母亲看到蛇,站起来走到我身旁,拉着我的手呆立不动。母亲这么一说,我猛然想到:“该不是蛇蛋的母亲吧?”一句话随即脱口而出。 “是的,没错啊!” 母亲的声音有些嘶哑。 我们手拉着手,屏住呼吸,默默注视着那条蛇。蛇忧郁地蹲踞在石阶上,开始颤颤巍巍地爬行了,她吃力地越过石阶,钻入一簇燕子花丛里。 “这条蛇一大早就在院子里转悠了。” 我小声地说。母亲叹了口气,一下子坐到椅子上,语调沉重地说道: “是吧?是在寻找蛇蛋呢,好可怜啊。” 我只能嘿嘿地笑了笑。 夕阳映照着母亲的面孔。看起来,母亲的眼睛闪着蓝色的光芒,似乎含着几分嗔怒,神情十分美丽,引人恨不得扑过去紧紧抱住她。我觉得母亲的那张脸孔,同刚才那条悲伤的蛇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且,我的胸中盘踞着一条毒蛇,这条丑陋的蛇,总有一天要把那条万分悲悯而又无比美丽的母蛇一口吞掉,不是吗?为什么,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我把手搭在母亲柔软而温润的肩膀上,心中泛起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 我们舍弃东京西片町的宅第,搬来伊豆的这座稍带中国风格的山庄,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年的十二月初。父亲死后,我们家中的经济都由母亲的弟弟,同时也是母亲唯一的亲人——和田舅舅一手包揽下来。战争结束,时局变化,和田舅舅实在支撑不下去了,看样子曾经同母亲商量过,他规劝母亲,不如将旧家卖掉,将女佣全部辞退,母女二人到乡下买一套漂亮的小住宅,享享清福为好。母亲对于金钱的事,比孩子更一窍不通,经舅舅这么一说,就把这些事都托付给他了。 十一月末,舅舅发来快信,说骏豆铁道沿线河田子爵的别墅正在出售,这座宅第位于高台之上,视野开阔,有一百多坪农田,周围又是观赏梅花的好地方。那里冬暖夏凉,住下去一定会满意的。因为必须同卖主当面商谈,明天请务必来银座他的办事处一趟。——信的内容就是这些。 “妈妈您去吗?” “我本来都交付给他的呀。” 母亲忍不住凄凉地笑着说。 第二天,母亲在先前那位司松山大师的陪伴下过午就出发了,晚上八时,松山大师又把她送回家来。 “决定啦。” 她一走进我的房间,双手便扶住我的书桌瘫坐下来,只说了这么一句。 “决定了什么?” “全部买下。” “可是,”我有些吃惊,“房子怎么样,还没有看就……” 母亲胳膊肘儿支着桌面,手轻轻按着额头,稍稍叹了口气。 “和田舅舅说了,是座好住宅,我就这么闭着眼搬过去,也会感到舒心的。” 说罢她扬起脸微微笑起来。那张面孔略显憔悴,但很美丽。 “说的也是。” 母亲对和田舅舅的无比信赖使我很佩服,于是我表示赞同。 “那么,和子我也闭着眼。” 娘儿俩齐声笑了,笑完之后,又觉得好不凄凉。 其后,每天家里都有民工来打点行李准备搬家。和田舅舅也每天大老远地赶来,将变卖的东西分别打包。我和女佣阿君两个忙里忙外地整理衣物,将一些破烂堆到院子里烧掉。可母亲呢,既不帮助整理东西,也不发号指令,每天关在屋子里,慢慢悠悠,不知在倒腾些什么。 “您怎么啦?不想去伊豆了吗?” 我实在憋不住,稍显严厉地问。 “不。” 她只是一脸茫然地回答。 花了十天光景整理完了。晚上,我同阿君两人在院子里焚烧碎纸和草秆儿。母亲走出屋子,站在廊缘上,默默望着我们点燃的火堆。灰暗而寒冷的西风刮来,黑烟低低地在地面爬行。我蓦然抬头看向母亲,发现她面色惨白,这是从未有过的,不由惊讶地喊道: “妈妈,您的脸色很不妙啊!” “没什么。”母亲淡然地笑了,说罢又悄悄走回屋子。 当晚,被褥已经打点完毕,阿君睡在二楼西式房间的沙发上,我和母亲从邻居家借了一套被褥,娘儿俩一起睡在母亲的卧房里。 母亲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叫了一声,嗓音显得有些衰老。 “有和子在,只要和子陪我,我就去伊豆。因为有和子做伴儿。” 她的话很使我意外。我不由心里一震,问道: “要是和子不在了呢?” 母亲立即哭起来,她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哭得越发厉害了。 “那还是死了好,这个家没了父亲,母亲也不想再活下去啦。” 母亲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说过这般丧气的话,我也从未见她如此激烈地痛哭过。哪怕是父亲去世,我出嫁,不久怀着大肚子跑回娘家来,不久孩子死在医院,以及我生病起不来床,还有直治闯祸那些日月,母亲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心灰意冷。父亲死后的十年间,母亲和父亲在世时毫无两样,依旧那般娴静、优雅。而且,我们也都心情愉快,在母亲的娇惯下成长。但是,母亲没有钱了,为了我们,为了我和直治,毫不吝惜地花光了,一个子儿也没剩下,而且,离开这座长年居住的宅第,只和我搬到伊豆的小村庄,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假如母亲是个冷酷、悭吝的人,经常责骂我们,而且只顾偷偷生法子攒钱肥己,那么,不管世道如何改变,她都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一心想死。啊,没有钱是多么可怕、可怜、求救无门的地狱啊!有生第一次切实感到这一点,我心头郁闷,痛苦地一心想哭。所谓人生的严峻就是这种感觉吗?我只好纹丝不动,仰面躺卧,像一块石头凝固在一起了。 贵族的仪礼如同黄昏,终将淹没在黑夜之中,是不可挽回的没落。《斜阳》是献给没落贵族的一曲寂寞挽歌,堪称日本战后社会的夕阳图、国民精神变异的告白书,被誉为“日本的《樱桃园》”。 人有生的权利,同样也有死的权利。他说自己只是一棵小草,在人世的空气和阳光里难于生长。要生长,还不充分,还缺少一样东西。以往活过来,已是竭尽全力了。 太宰治作为一位“弱者”,其伟大之处在于他把自己的脆弱剥开来,彻头彻尾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其实在脆弱面前,我们都是同类。 太宰治名家经典系列,涵括太宰治不同创作时期的经典篇目,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文洁若、豆瓣高分资深译者陈德文等翻译大家匠心打造名家气质译本,裹挟物哀与孤寂美学的全新装帧震撼来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