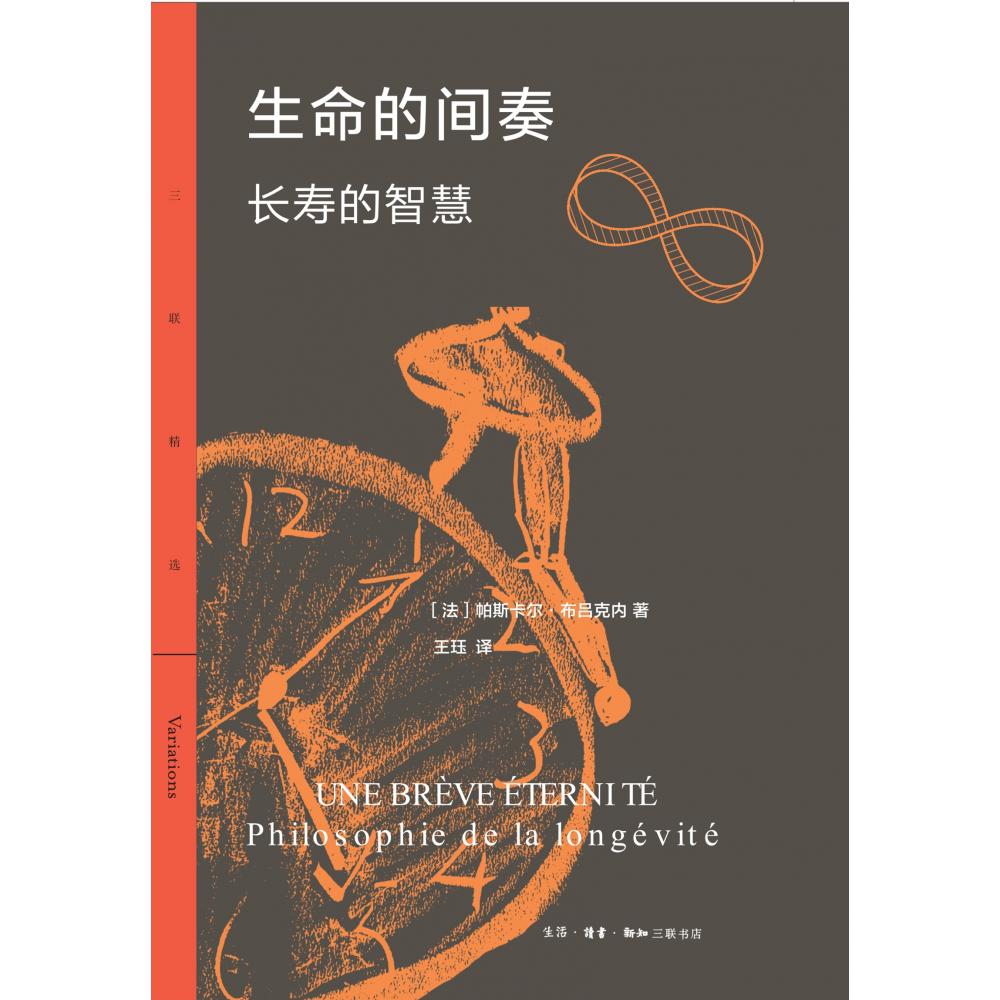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39.00
折扣价: 26.60
折扣购买: 生命的间奏:长寿的智慧
ISBN: 9787108069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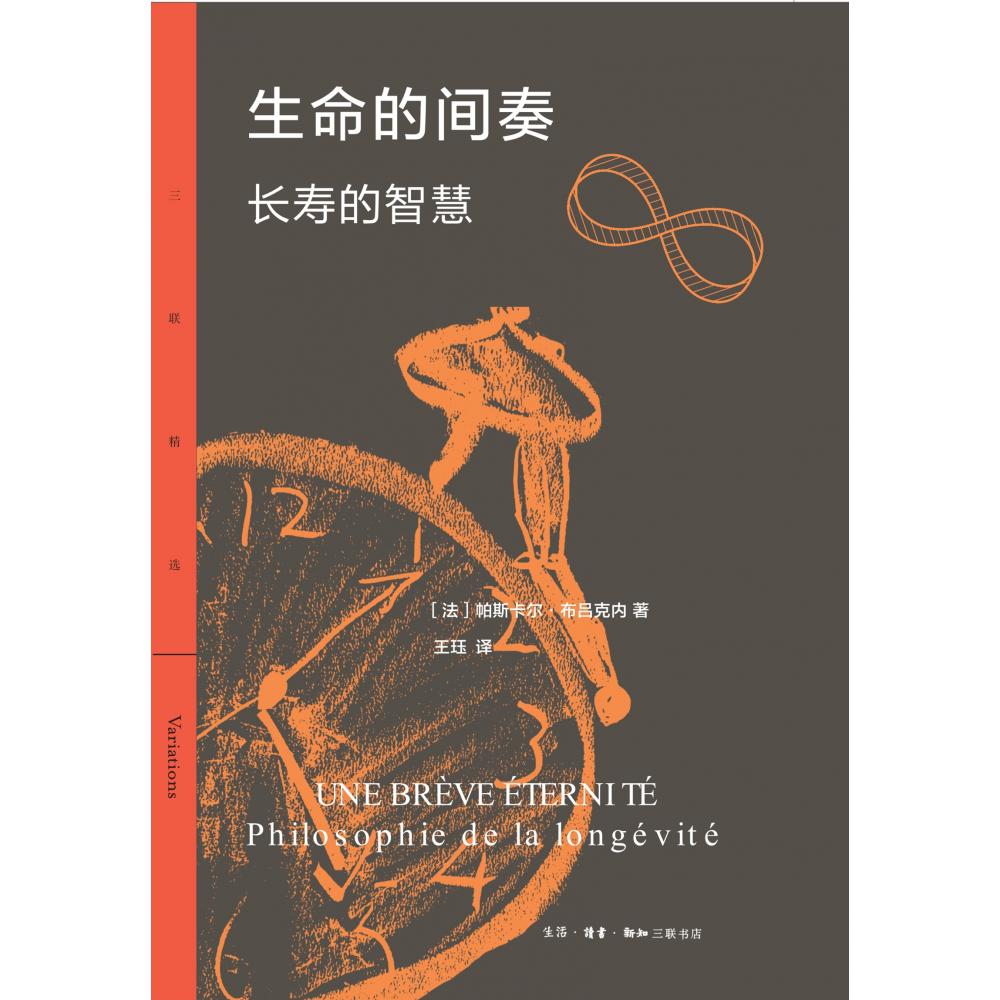
帕斯卡尔·布吕克内(Pascal Bruckner),著名小说家、哲学家。其主要作品为:《无辜的意图》(La Tentation de l’innocence,格拉塞出版社,1995,美第奇奖获奖作品)、《盗美贼》(Les voleurs de beauté,格拉塞出版社,1997,雷诺多文学奖获奖作品)、《悔罪之暴政:试论西方受虐癖》(La tyrannie de la pénitence,格拉塞出版社,2006,蒙田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儿子》(Un bon fils,格拉塞出版社,2014,马塞巴纽尔奖获奖作品)、《虚构的种族主义,反伊斯兰教及罪恶感》(Un racisme imaginaire,格拉塞出版社,2017,反种族主义奖获奖作品)。
第一章? 拒绝遁世(节选) “慢慢老去是目前已知通达长寿的唯一途径。” ——圣伯夫 自 1945 年以来,人类社会中出现了哪些改变?最本质的变化:生命不再短暂易逝。若借用莫泊桑的比喻,生命不再 “如飞驰的列车”一般呼啸而过了。更确切地说,由于生命始终在烦忧的重压和突发事件的闪现中反复横跳,因此它变得既过于短暂又过于漫长:既可“诸事不顺,度日如年”,也可“佳期如梦,似水流年”。事实上,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的寿命一直在延长,在相对富庶的国家中,人类寿命甚至增加了二十到三十年。每个人依据自己的命数都拿到了一张时效因人而异(受性别、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的继续生存“许可证”。米 歇尔·福柯将医学称作“被人类有限性武装的形式”。医学的进步让当代人相较祖先得以多见一辈子孙。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渴望“尽兴而活”实则对应着推迟进入衰老。要知道,在两百年以前,三十多岁就可算步入老年了。1800 年时,人类寿命仅有三十至三十五岁,1900 年这个数字已增长到四十五至五十岁。之后每年人类都可将自己的寿命延长三个月。也就是说,今天出生的小姑娘里有一半可以活过一百岁。“长寿”不只与行将就木的老人有关,它对每个人的影响从孩提时代便已经开始,并且会影响各年龄段的人。比如如今的“千禧一代”,他们十八岁时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寿命很可能会持续一个世纪,这将影响他们对学习、事业、家庭和爱情的看法:路漫漫其修远兮,有的是时间徘徊、流浪,有的是机会犯错再重来。既然余生漫长,为什么要在二十岁的时候“英年早婚”甚至早育,为什么要早早结束求学之路呢?多的是时间去学习更多的知识,体验更多的行业,甚至经历更多段婚姻。大家对于完成社会职责的最终期限都心知肚明,只是都心照不宣地选择巧妙规避。此时,人类发扬了一项崇高的美德—对自己踟蹰不决的宽容,同时也在面临一个挑战—面对选择的恐慌。 自动门 五十岁,人生从此时起开始显得短暂。人类在这个年岁开始经历一种介于两种状态间的“悬而未决”。 五十岁之前的时间是有方向性的,它一直朝着人生的终了—精神的至臻之地、万事皆休的圆满状态—前进。而进入五十岁后,在两段时期之间,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插入性时刻。所以,五十岁到底是什么?它好似一段缓刑期,让人生变得开放,犹如一扇自动门。年过五十,人生中出现了一些可影响一切的质变:收入的提升、夫妻问题、社保投入、独立生活的巨大开销等。在“壮年”和“老年”之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年龄概念,该概念指向的人口群体健康状况良好,且通常比其他年龄层享有更多资源。在拉丁语中该年龄层被称为“seniors”(“中老年”)。进入中老年阶段,大部分人已经将子女抚养成人,因此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应尽的夫妻义务,故而很多人在此时离婚甚至再婚。该现象不只局限于西方社会,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无论其物质条件如何,许多国家都出现了人口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的问题。全球各地的政府都在考虑让中老年重回工作岗位,为此将退休年龄推迟到六十五至七十岁已被提上议程。高龄如今不再是少数人才能有幸抽中的“大乐透”,它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面临的板上钉钉的未来,当然,死亡率持续攀升的美国白人工人阶层除外。到 2050 年,全球老龄化人口预计将为四岁以下婴幼儿人口的两倍。换句话说,“暮年”或“年迈”涵盖的年龄范围越来越大,但最符合这一概念的,还应是无限接近死亡的那段人生。因此,年龄段划分的精细化势在必行。 余生短暂也许会促使生活变得更加浓艳热烈,这是很多人热烈地盼望充分享受余生,使之极尽精彩的原因。他们渴望弥补曾经的遗憾,渴望延长已经体味过的生命的美好。这也是倒数计时的好处:它让我们更加珍视飞驰而过的时光。五十岁以后的人生应该被贪婪、迫切地利用,应被无穷无尽的欲念与渴望填满。毕竟不知哪天我们便会在一场重疾或一次事故中殒命。勒内·笛卡尔曾说:“基于我现在的人生状态推算,经年之后它也势必精彩。”纵使医学已取得飞跃式进步,但今日与17 世纪也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明日的吉凶祸福今日依旧不可知。“长寿”不过是基于统计学计算得出的结果,而并非命运与每个个体签订的保证书。好比立足于山脊之上的人,落入眼中的既有峰峦也有险谷。 值得注意的是,语法概念中的“将来”与人生道路上的“未来”不可被混作一谈。“将来”是被迫忍受,“未来”是主动创造;“将来”源于混沌消极,而“未来”源于人类的自主行为,它绝非偶发事件,而是人们诚心追逐、热烈盼望的明天。明天降温下雨(“将来”),但无论如何,我心已决,我将启程远行(“未来”)。海德格尔将关于自身的“存在”与反映过去的“存在者”加以区分。长寿不难,但时至晚年,我们是否依旧“存在”呢?维克多·雨果曾说过:“人生最沉重的负担是只能生存而无法存在。”到底应如何利用这意外得来的二三十年的额外生命?“50+”的我们,就好像一群等待被遣散但马上又会因其他战争而被招入伍的士兵。人生的主体部分已然上演,进行总结的时刻似乎也已近在眼前,然而一切都没有要停止的意思。有些人其实对长寿充满畏惧,他们觉得在冗长的生命之路的尽头应是终于得以休憩的“应许之地”,在那儿他们可以卸下所有重负彻底放松。对这些人来说,暮年算是 一个善意的谎言吧。作为生命中的“小阳春”,这段时光被史无前例地拉长,彻底放松的期许渐渐化为泡影。他们以为马上得以进入“应许之地”尽享安宁,却不得不在人世间继续坚守不知多少个春秋。 这段“缓刑期”真可谓让人欢喜让人忧。从本质上说,它是极尽虚空的,我们应努力将这段额外的时光填满。“我的进步在于我发现自己已无法再进步了。”萨特于 1964 年在 《文字生涯》中如是写道。当时他五十九岁,在书中毫无保留地承认了自己对“登山者充满青春气息的狂热”的怀恋。半个世纪后的我们亦是如此吗?余生渐短,机遇变得罕见,但仍有可能偶遇美好、惊喜甚至令人神魂颠倒的爱情。时间不再是置你我于死地的杀手,它作为同盟,与我们并肩前行,承载着你我的忧虑与欢愉,(借用勒内·夏尔的比喻可谓)“半是果园,半是沙漠”。生命时限逐渐被拉长好似那些白日渐长的夏日傍晚,空气芬芳、菜肴味美、友人情浓,谁不期待这种曼妙时刻的延续,谁又舍得在此佳期面前让睡意肆意萌生。 长寿并非简单的年岁叠加,它彻底改变了你我与生命的关系。首先,长寿使得各种经历不同、回忆不同在地球上历时存在的人共存。一位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柏林墙倒塌的世纪老人和一个诞生于网络时代、高科技时代的婴孩能有什么共同点?曾经的我和现在的我又有何相似之处?不过是都使用一张身份证罢了。时间线上的各个节点毫无逻辑地相互碰撞,生活经历的不同使前后辈间使用的语言都不甚相同,交流问题日益凸显。长寿打破了很多所谓“不可共存”的概念:如今,一个人可以身兼多重身份—父亲、祖父、曾祖父;一位长者也可以是某项运动的达人;一位普通母亲甚至可以是她女儿、女婿的代孕妈妈。当代社会中,代代人都是玛士撒拉,而且是异常活跃的玛士撒拉:一位男士在七十五岁高龄时仍可诞育后代,同年,他的长子完全有可能为他添一位孙子。如此一来,伯父或姑母比侄辈小四十岁并非奇闻,幼子与长子有半世纪的年龄差也绝非天方夜谭。科学使时间线上的节点对调成为可能,家族繁衍的支脉从整齐的线性传递变成像通信基站的电缆般错综盘桓的杂乱发展,家族谱系的层级关系被彻底打乱,变成一个缺乏任何参照物的巨大旋涡。将来某天,若百岁老人成了社会人口构成的主体,他们定会将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看作没教养的孩子,然后大声训斥道:哎,这些小年轻儿可真没规矩啊! “缓刑”即“暂”不执行最终判决,其中蕴含的巨大不确定性无须赘言。生命不再是从出生指向死亡的箭头,而是一段“旋律性绵延”(伯格森),一块时间性相互叠加而成的千层饼。无须对岁月停滞望眼欲穿(拉马丁曾经苦苦哀求:“时光啊,请收起你飞翔的翅膀”,阿兰却反驳说:“(您想)让它停多久呢?”),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享受这份天赐之礼。面对这段增补而来的生命,好比为丧事提前哀悼,又如在临死前通过三药疗法治疗拯救的艾滋病人。总之,刽子手的铡刀迟迟不落。人生的推进与侦探小说的情节发展正好相反:结局人人心知肚明,谁是凶手也毫无悬念,但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保护其身份不被暴露。当他行事稍有破绽时,我们甚至会苦苦哀求:请你藏好,还得等好多年才能揭露真相呢。书中的最后一章即便是总结概括,也不妨碍其和前序章节一样引人入胜。 青春的珍贵之处在于它的不确定性,谁也无法预知将来会发生什么;生命中的“小阳春”的优势则类似考试时“答案在手,万事无忧”。这个年岁既可以是“天恩赐福”也可以是“万劫不复”。五十岁以后,“无忧无虑”算是一去不复返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变成了他曾经期待自己成为的样子。从此时开始,我们好像可以自由选择是想永恒地留存于即时的“存在”中还是重塑自我。阅历的不断累积将千差万别的要素一股脑儿糅进一个人的生命,并像粒子加速器一样促使其在之后的人生中渐渐发酵。前所未有的“暮年青春期”、黄昏恋等现 象已经揭示:暮年的主题并非选择人生,而是使之不朽、使之转向、使之丰富充实。到底应如何利用这段光阴呢?借用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话:“每一天都是余生中的第一天。”万事万物缘起于一,因此“余生的第一天”给人一种由缓至急的感觉:初看时光尚早,之后越过越紧张。时间就像柏拉图口中的爱情一样,是“匮乏”与“丰盈”的共同产物。它代表必然的成熟、无尽的期许,它必会孕育、开花结果,然而也有衰败、残破、油尽灯枯的那一日。随着年岁的增加,人们理应变得“锱铢必较”:万物皆有数,每过一日留给我们的选择便少一分,因此,我们必须拥有十足的辨识力。 然而,在五十多岁时迟来的“青春期”却并非理智选择的结果。克洛德·罗阿〔1〕曾将其解释为“生命之诗迟迟不愿曲终的拖延方式”。不愿让一生盖棺定论,想让它像一扇半开的窗一样留白是非常合乎情理的。这扇窗应由他人来关,这首诗应由他人来画上句点。他人也可对我们的命运评头论足。克尔凯郭尔在其著作中曾经将人生分为三个阶段:感性阶段,即追求直接性的阶段;理性阶段,即满足道德要求的阶段;宗教阶段,即追求宗教大能的阶段。该观点确实振奋人心,但谁能像构建一篇逻辑清晰、结构分明的学术论文一样为自己的人生划分段落呢?生命本身应像论文的简介,直至终了,也不会有什么层次递进。我们进入时光洪流的一瞬其实也是被它驱逐的瞬间,因为我们始终只能立足于那个被称作“此时此刻”的位置。对于时间的长河来说,我们不过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可怜人罢了。 这本看似自传独白的小书只有一个核心议题——生命的漫长。本书立足生命的中段,即年过五十后既非年轻也不算年迈,内心仍充满无限渴望的时光。岁已至此,很多有关人生的尖锐问题接踵而至:应该追求长寿还是应努力活得充实热烈?应推翻一切重新来过还是应在人生之路上略做转向?再婚怎么样?转行怎么样?如何排解生活的重压?如何扫除暮年的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