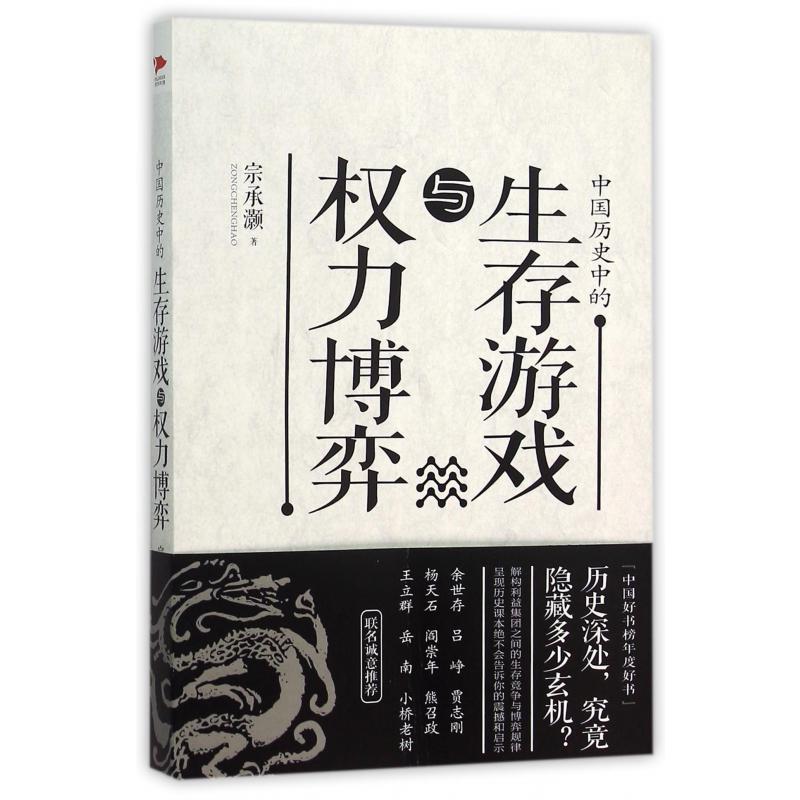
出版社: 群言
原售价: 39.80
折扣价: 23.50
折扣购买: 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与权力博弈
ISBN: 97878025678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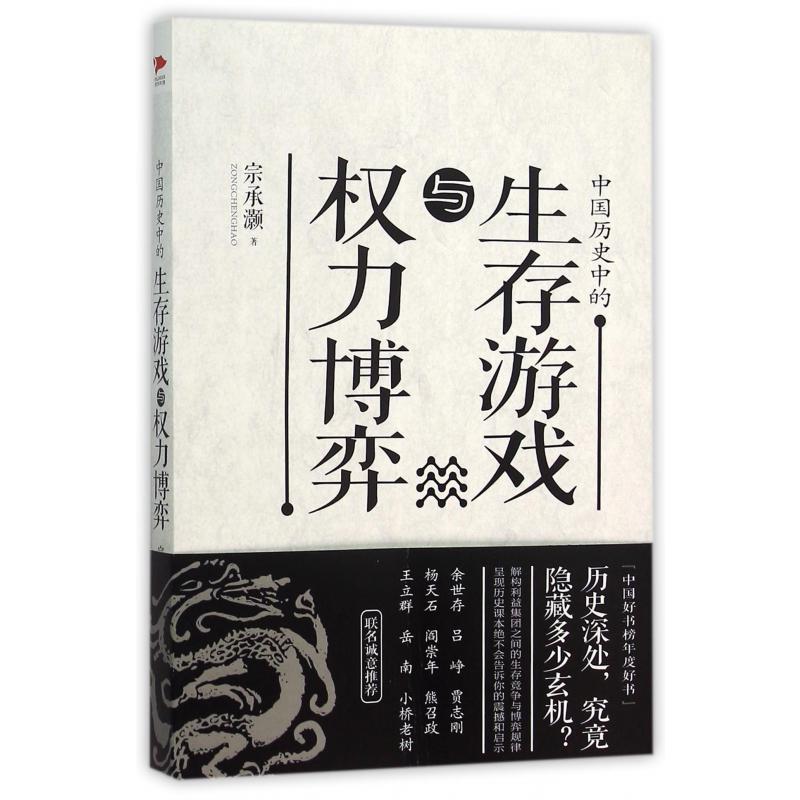
宗承灏,新一代非虚构历史作品领军人物;专栏作家。文笔如刀,抽丝剥茧;行文轻松,说史透彻,力图从历史深处找出被人有意无意埋没的玄机和真相。 已出版《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与权力博弈》《权力的智慧——冰与火的中国历史定律》《出轨的盛唐》系列等多部畅销作品。“中国好书榜年度好书”获奖作家。
小胥吏大买卖 按照清朝时期的权力结构设计,京城六部衙门里 的胥吏只是一些普通的办事人员,他们的工作无非就 是干一些抄抄写写的活,类似于今天政府部门的办公 室文员。 在权力的等级制度中,这些文员的上面还有很多 人——被称为“司官”的主事(处长)、员外郎(副 司长)、郎中(司长),被称为“堂官”的侍郎(副 部长)、尚书(正部长)管着他们。可问题是,管归 管,那些处长、司长、部长却没有几个懂得财务方面 的专业知识。即使有人知道一点皮毛,可谁也不愿意 把时间和精力花在那些枯燥乏味的账目上,他们更愿 意把时间、精力花在喝花酒、听京戏等娱乐性活动上 。其中高雅一点的是去读书、收藏书画、写诗、吟风 颂月。将时间花在那些琐碎而无聊的数字游戏上,他 们觉得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更何况他们也看不起没 完没了琐碎而无聊的工作,觉得没有必要去弄懂。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把审计的职责推给了胥吏 ,通常就是在胥吏把审计报告送上来的时候,自己在 上面签个大名,对于具体内容并不去核实。这样以来 ,审计和批驳的权力实际上就在不知不觉中转移到了 胥吏手上:胥吏说行,他们就在同意报销的审核报告 上签字;胥吏说不行,他们就在批驳的意见单上签字 。 摆在福康安面前的一个很现实问题就是,户部胥 吏才是决定报销成否的关键。 虽然说胥吏在帝国的权力结构中是一些没有地位 的人,类似于政府聘用的不在编人员,按规定是五年 一续聘,而且不能连任。他们不仅连正式的工资都没 有,甚至连一点伙食费(饭银)都未必能够如数领到 手。更不合理的是,胥吏的办公费用——比如纸张、 墨水等经常还得自己掏钱买。即便是这样的工作,也 有严格的编制限制,户部主管全国的财政,需要处理 的事情很多,而胥吏的正式编制只有200多个。胥吏 自己办不完的事只能找助手,助手可能再找助手,这 就有许多编外人员,这些编外人员的工资福利都要由 找他们办事的正编书吏来负责。 当然对于胥吏们来说,他们工作的动力与领不领 政府的薪水关系并不大。他们占据了这个职位,也就 等于拥有了衍生权力,有了权力就可以生出灰色利益 。对于胥吏来说,他们更看中的是衍生权力为自己带 来的灰色利益。只要福康安按照潜规则出牌,他们就 可以顺利拿到自己应得的灰色利益。即使福康安的账 目不符合规定,漏洞百出,他们也可以做到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换句话说,如果福康安坚持自己那套“老 子天下第一”的理论,那就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情景 :即使申报的款项完全符合规定,账目做得天衣无缝 ,他们也能找到一个说不的理由,让你核查清楚了再 来报。 正因为户部胥吏手中有了这种权力,才有了福康 安不交“部费”就无法报销的现实问题。其实他们也 不是针对福康安一个人,那些能够跑到户部来报销账 目的,哪一个部门或者官员是吃素的?不是封疆大吏 就是重要部门的王爷。如果今天他们能对福康安开这 个口子,那么明天就会对其他人也开这个口子。这样 的话,他们自己就破坏了游戏规则,最后伤害到的只 能是自己的利益。 最后双方博弈的结果当然是福康安做出了让步。 在与地方大员的交锋中,户部的小胥吏成功地维持了 户部灰色收入的程序“正当性”。 这些胥吏也并不是拿福康安不当盘菜,福康安所 遭遇的一切也算不得什么新鲜事。福康安之后,权倾 朝野的肃顺,作为咸丰皇帝的托孤大臣,由于办案风 格太过酷烈,又加上他上奏要求削减旗人的俸禄,影 响了朝廷官员的“灰色收入”,最终也落得身首异处 。福康安之前,明朝万历年间的权相张居正也是一个 大案例。作为首辅大臣,张居正可以说是红极一时, 他所推行的“一条鞭法”就触及到了大明官场的潜规 则,损害了官员的“灰色收入”,最终落得死后被权 力集团清算的下场。 灰色收入在传统中国自古有之,并不是明清时期 的特有产物。 秦汉以来,灰色收入的存在始终保持在一定的限 度,始终没有出现井喷式地增长,更没有动摇国家财 富的根本,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灰色收入有其合理 性,甚至是必要性。例如明朝官员的俸禄极低,以至 于像海瑞这样的二品大员如果不贪污竟然养不活一家 人。海瑞并不屑于像其他官员那样搞点“灰色收入” ,也就只能在自家菜园里搞点“副业”以贴补家用。 另一方面,历代中央各部的低级官吏往往事多钱少, 如果不能够确立“外快”的合法性,那么庞大而繁杂 的官僚机器根本无法正常运转。 所以,对于这种无伤大雅的“灰色钱道”,各级 官员和百姓也都是持默许态度,毕竟官僚体系内部也 有自己的约定俗成,出现狮子大开口的几率相对较低 。 民生不能承受之重 这些敢找朝廷大员吃拿卡要的胥吏们到底能够捞 到了多少好处?最后装进自己腰包的“灰色收入”又 是多少呢?按照晚清的学者兼官员冯桂芬在他所著的 《校邠庐抗议》政论书籍里所记载的:那些胥吏们在 做事的时候手法是极其隐蔽的,圈外人士一般是很难 摸清确切的底数。 冯桂芬曾经和一个绍兴籍的胥吏算过一笔账:吏 部四个司的胥吏每年大概能够得到三百万两银子的好 处费,加上兵部、户部、工部,四部书吏每年所得应 该不少于一千万两银子。外省衙门的人数更多,因此 “灰色收入”也就不止一千万两银子。从这些灰色收 入的来源渠道可以分析得出:其中十分之三是来自于 国家财政,十分之七是从地方税收中获取,而地方税 收的来源又基本上是从老百姓的血汗钱里刮来的。 在冯桂芬生活的道光、咸丰年间,全国的胥吏每 年得到的灰色收入超过了两千万两银子,而当时全国 的财政收入是四千多万两。也就是说,胥吏的灰色收 入占去了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如果按照上面来源 渠道三七开的算法,属于国库的有三成,占到了600 万两;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到的财富高达1400余万两。 如果以4000万两的国家财政收入作为比较对象,那就 意味着地方在收税时要加收35%才能持平。 那么我们再来算一算这些“灰色”总收入,最终 摊派到每个胥吏的头上,也就是落到个人腰包里的会 有多少? 当时一个衙门有十几个胥吏,而州县衙门至少分 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房(类似于县政府下面 的科室),每房平均下来有二三个人,事多人手少, 通常都是一个正役带几个帮役都忙活不过来。 雍正年间,田文镜在河南巡抚任上的时候,巡抚 衙门的经制书吏分为两班,每班10人,共为20人。但 田文镜说衙门事务太多,实际上每班有100人,所以 河南巡抚衙门的胥吏实际人数是200多人。由此可以 得出,各级衙门的胥吏实际人数可能是正式编制的十 倍以上。清初的散文大家侯方域做过统计,他统计出 来的数字是全国州县衙门的胥吏大约有30万人。其实 他算的只是州县衙门,并没有把所有的官府衙门都算 进去。如果从上到下都计算在内,全国的胥吏有40万 人左右。 如果按照40万的胥吏来算,灰色收入总额达到 2000万两银子,平均下来每个人也不过就是50两银子 。要知道书吏们在当时都没有国家派发的死工资,为 了能够谋得书吏的职位,他们还得花一笔活动经费( 称之为“顶首银”)。由此看来,每年50两的银子应 该是不会高估的。当时老百姓家庭一家五口一年花费 需要30多两银子,50两银子也只能让他们过上比一般 人家好一点的日子,而不太可能有更多的财产积蓄。 按照全国胥吏的灰色收入总量2000万两银子来计 算,如果将其分摊至民间,那也是“民生不能承受之 重”。全国40万胥吏“灰色生存”所产生的“灰色收 入”,使得老百姓的实际负担要比法定负担增加了三 分之一。当然在这里还不包括官员和衙役阶层在运行 正式权力时所需要的成本,如果统统计算在内,那么 又将是一笔骇人的天文数字。 经济学上有一个“租金”的概念,就是指由权力 管制所造成的,由官员与官商特殊利益集团来分配的 社会公共财富。其实官员的灰色收入就是一种经过权 力异化而来的“租金”,通常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 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与否的收入部分; 另一种情况是实际为非法收入但又缺乏足够的证据来 认定其为非法的收入。 灰色收入的形成,就是权力滋生的腐败行为,它 与官员贪污、渎职、寻租等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其 实官场上的利益分配往往与一个官员的权力大小成正 比,但是权力的大小与官职的大小却难成正比。利益 分配,除了合法收入,就是有着灰色和黑色成分的隐 形收入。很多时候,后者并不比前者得到实惠少。就 像那些能够占据肥缺的胥吏,官家制度虽然不承认他 们具有合法的权力名分,但是他们照样能够发自己的 财,让老百姓痛恨去。既然得不到权力的名分,那就 借助权力的光来照亮自己的“钱程”,毕竟他们手里 掌握着含金量可观的衍生权力。 有的官员虽然有品级有名分却得不到太多的实惠 ,在这一点上,最明显的比较是京官与地方官,四品 的京官往往不如一七品的知县。原因是京官能够闪 转腾挪的权力空间与地方官员是无法相比的,天高皇 帝远,一个知县俨然就是一方小诸侯。即使不同的官 员所处的职位有肥瘦之分,他们所获取的收入还是能 够反映出个人的实际权力值。 那些占据肥缺的官员,权力的衍生力就越强大, 他们能够将权力的枝节伸展得无孔不入,他们拥有广 泛的人脉资源和强有力的后台支撑。反之,那些清水 衙门的官员,权力的衍生力也相对弱化。 所以说,最后为“灰色生存”埋单的还是那些手 无寸权的老百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共谋者。而那些 利用职业之便尽享“灰色收入”之利且安之若素者, 可以说是权力集团内部最大的蛀虫。 P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