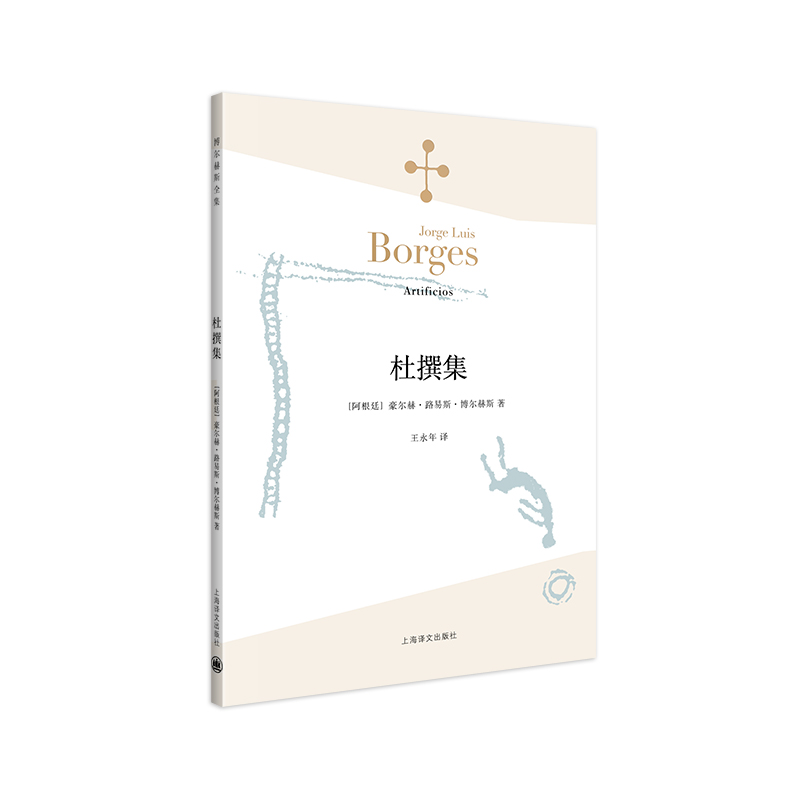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售价: 35.00
折扣价: 22.80
折扣购买: 杜撰集(博尔赫斯全集)
ISBN: 97875327629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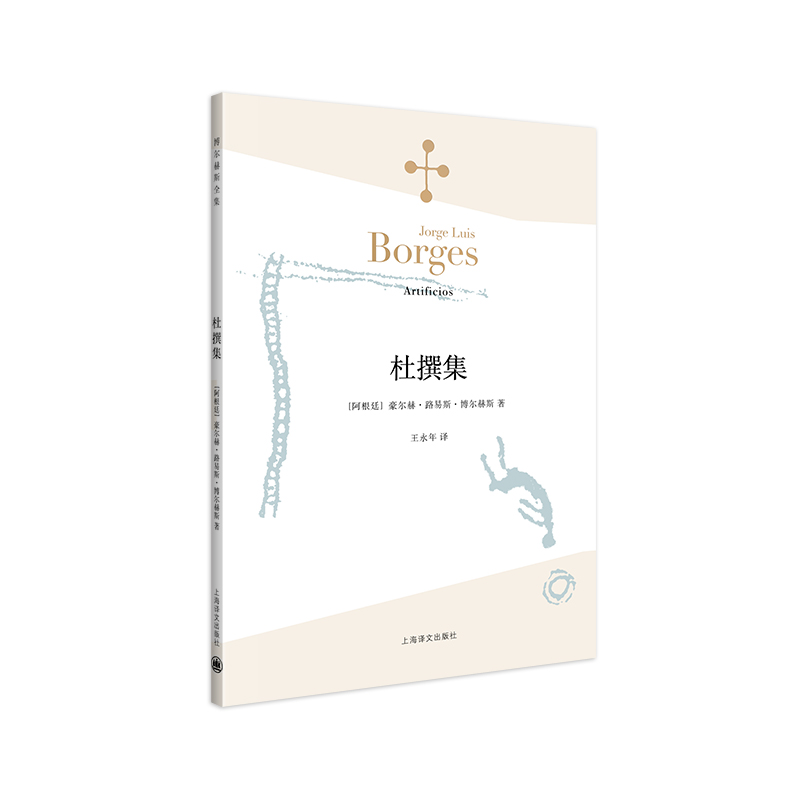
博闻强记的富内斯 我记得(其实我没有权 利讲出那个神圣的动词,世 界上只有一个人有权利,但 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他手里 拿着一枝深色的西番莲,仿 佛从未见过似的瞅着它,尽 管他从黎明到黄昏一直看着 ,看了整整一辈子。我记得 他衔着香烟,沉默寡言,那 张有印第安特征的脸庞的神 情显得出奇地遥远。我认为 我记得他细长灵活的手指的 模样。我记得他手边那个有 东岸地带纹章的马黛茶罐; 我记得他家窗外一张黄色的 席子,隐约可以望到湖边的 景色。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声 音,旧时城郊居民那种缓慢 、阴郁的鼻音,没有如今那 些意大利移民的咝咝声。我 只见过他三次,最后一次是 一八八七年……我觉得凡是 同他有过接触的人写一些回 忆他的文章将是很有意义的 事;我的文章也许会是你们 汇编的集子中最简短,肯定 最贫乏,但不是最不公正的 一篇。当主题涉及一个乌拉 圭人时,我身为阿根廷人的 可悲情况有碍于我参与乌拉 圭的必不可少的赞颂体裁。 有文化的、风度翩翩的布宜 诺斯艾利斯人,富内斯虽然 没有用过那种损人的字眼, 但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他 心目中我就是那种人物。佩 德罗·莱安德罗·伊普切说过 ,富内斯是超人的先驱者, “一个土生土长、未加斧凿 的查拉图斯特拉”;我对这 一点并无异议,但不能忘记 ,他也是弗赖本托斯的一般 居民,有某些无法弥补的局 限性。 我第一次见到富内斯的 印象十分清晰。那是一八八 四年三月或二月的一个傍晚 。当时我父亲带我去弗赖本 托斯度夏。我同表哥贝尔纳 多·阿埃多从圣弗朗西斯科 庄园回来。我们骑着马,唱 着歌,心情舒畅。更使我高 兴的是,闷热了一天,天空 突然乌云密布,南风又推波 助澜,树枝乱舞;我担心( 或者不如说盼望)在旷野淋 到倾盆大雨。我们策马飞奔 ,仿佛同暴风雨赛跑。我们 进入一条小巷,两旁是极高 的砖砌的人行道。天色突然 黑了下来;我听到上面传来 迅速的、几乎隐秘的脚步声 ,我抬眼一看,只见狭窄破 败的人行道上有个小伙子像 在狭窄破败的墙头奔跑。我 记得他穿的灯笼裤和草鞋, 铺天盖地的乌云衬托着他衔 着香烟的阴暗的脸。贝尔纳 多出乎意料地朝他嚷道:“ 几点钟啦,伊雷内奥?”小 伙子既不看天色,也不站停 ,脱口回答说:“八点差四 分,贝尔纳多·胡安·弗朗西 斯科少爷。”他的声音很尖 ,有点嘲弄的意味。 我当时心不在焉,如果 我表哥没有强调,他们两人 的一问一答根本不会引起我 注意。我想表哥之所以强调 ,大概是出于乡土的自豪, 并且想表明他并不计较那种 连名带姓的称呼。 表哥告诉我,巷子里的 那个小伙子名叫伊雷内奥· 富内斯,有点怪,比如说, 他跟谁都不往来,并且像钟 表一样随时能报出时间。他 母亲是镇上一个熨衣工,玛 丽亚·克莱门蒂娜·富内斯, 有人说他父亲是屠宰场的医 生,一个名叫奥康纳的英国 人,也有人说他父亲是萨尔 托省的一个驯马人或者向导 。他同母亲一起住在月桂庄 园拐角的地方。 一八八五和一八八六年 ,我们在蒙得维的亚市度夏 。一八八七年,我们又去弗 赖本托斯。我很自然地问起 所有认识的人,最后也问到 那个“活钟表富内斯”。人们 告诉我,他在圣弗朗西斯科 庄园从一匹没有驯化的马背 上摔下来,就此瘫痪,没有 康复的希望。我记得那消息 在我心中勾起的不舒适的魔 幻似的印象:我只见过他一 次,当时我们从圣弗朗西斯 科庄园骑马归来,他在高处 行走;我表哥贝尔纳多介绍 的情况很像一个似曾相识的 梦。他们说他躺在小床上动 弹不得,眼睛盯着远处一株 仙人掌或者一张蜘蛛网。傍 晚时,他让人把他抬到窗口 。他非常高傲,甚至假装认 为这次要命的打击是因祸得 福……我隔着栅栏见过他两 次,栅栏粗鲁地使人联想到 他作为永恒囚徒的处境:一 次见他一动不动,闭着眼睛 ;另一次也是一动不动,出 神地瞅着一枝气味浓烈的山 道年枝条。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