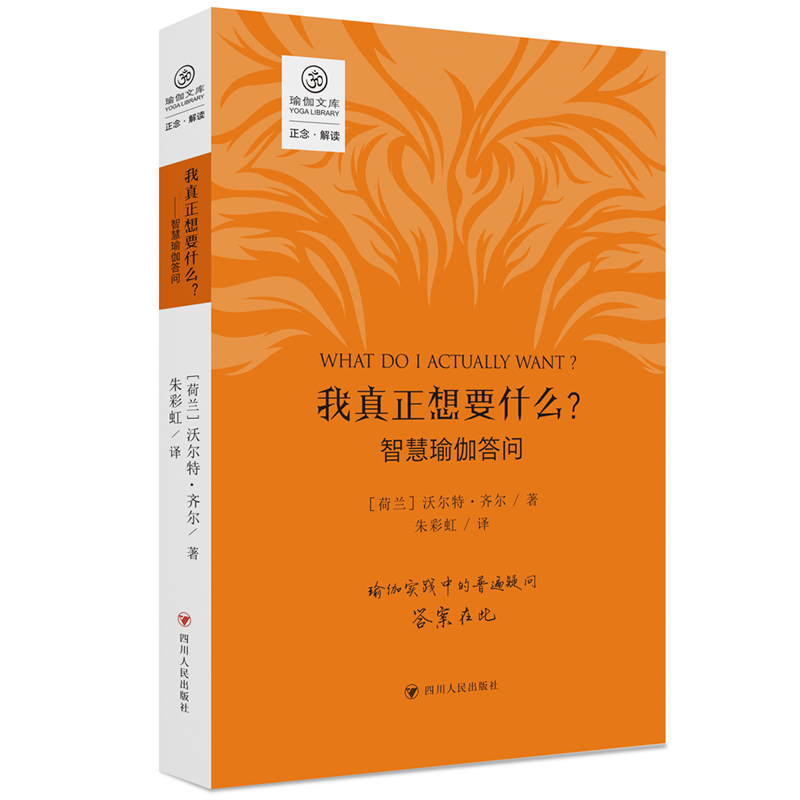
出版社: 四川人民
原售价: 52.00
折扣价: 29.70
折扣购买: 正念系列-我真正想要什么?:智慧瑜伽答问
ISBN: 9787220138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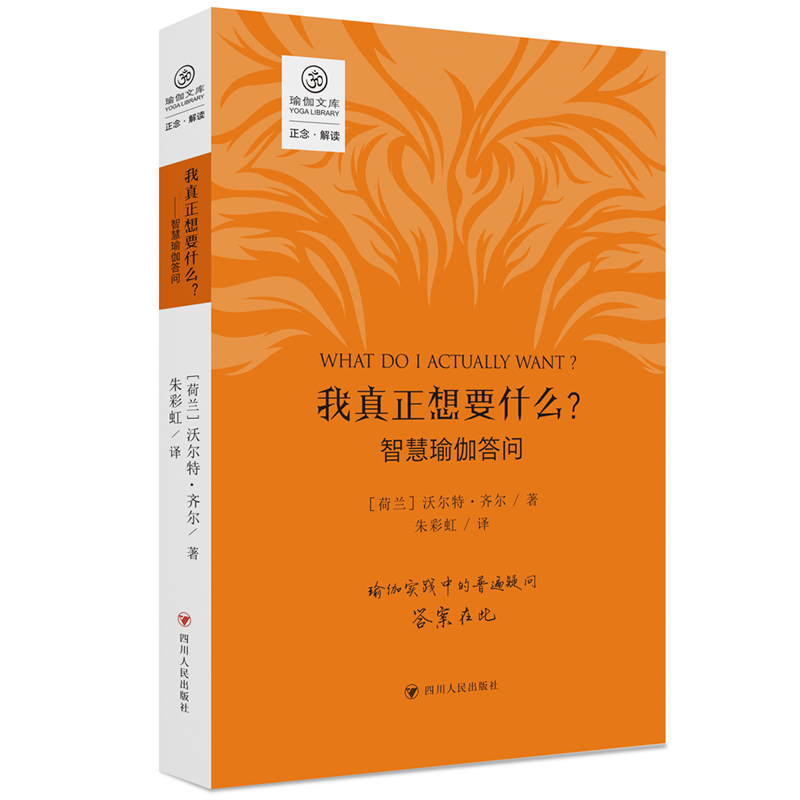
沃尔特?齐尔(Wolter Keers,1923—1985)出生于荷兰,成年后成为拉玛那?马哈希的弟子。马哈希仙逝之后,他师从阿特曼南达若干年,其间还拜访过尼萨格达塔?马哈拉吉。这三位导师是公认的20世纪吠檀多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学成之后,齐尔返回欧洲,主编《瑜伽与吠檀多》杂志。
我真正想要什么? 阅读古代经典,我们反复读到,人类的伟大领袖们关注生活的基本面,而于生活的细枝末节则不甚挂心。我也认为,如果我们想要过上快乐的生活,就必须不断回到基本问题,并习惯于自我追问——不是追问我想要什么,而是追问我真正想要什么。留心当下正在发生什么,胜过迷失于种种复杂的理论。 如果我们想要变得快乐,就必须再三留心当下正在发生什么——我们身在某处的当下、回家后的当下、工作时的当下、度假时的当下等等。如果我们密切关注,就会浮现出一幅越来越清晰的图像,它描述了我们在自己周围建造的“监狱”之规模。某件让我们愉悦的事情发生,我们便立刻朝那个方向奔去,投入巨大的能量获取让我们愉悦之物。某件让我们不悦的事情发生,或者出现了那样的征兆,我们便生起抗拒,立刻用全部的能量放大原本的非人格化反应,使之成为“我”害怕、“我”愤怒等等。就这样,我们成了我们过去植入的各种反应的奴隶、仆人、提线木偶。我们被锁在了过去,而只要我们继续喂养这些反应,我们就继续不快乐。 总的来说,我们拒绝看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快乐,那是父母的错、伴侣的错、孩子的错、老板的错,而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怀有的是善意。我们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让我们受伤的正是我们自己。这种忽略是因为我们把能量耗费在了身体反应和心理自动作用上,它们在很久以前,也许在我们幼年时,起到过这种或那种良好的作用,但现在,它们就像孩提时的旧衣服,不再适合我们。 我真正想要什么? 也许我会活到70岁、80岁或90岁,到那时,回首往事,我能说些什么?我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在恐惧、抱怨和追逐实际上并不重要的东西中度过了一生。最近,我读了一本书,讲的是美国开发的一种新的疗法,书中有个接受了这种疗法的人说:“神经症就是尽你所能地死死抓住某种你真的不想要的东西不放。”我们为了实际上不想要的东西——我执、人格——而斗争,有时斗得头破血流,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真正想要什么? 我真正想要的是快乐,我真正想要的是爱,我真正想要的始终是回到这样一种已知的状态:我是温暖本身,各种限制消失不见,世界是个生活的好地方。但我们已经改变,回到了旧的我执。当我们为了爱而放下一切,世界是个天堂。但我们已经出于习惯回到囚笼、回到监狱、回到德国人所称的“绝对命令”:你必须这样,你不可以那样。我们已经回到“我想要这个,不想要那个”。但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我们不可能既是爱又是私我,而必须做出选择。自私的爱就像干的水、方的圆,不可能存在。 我真正想要什么? 自由是毫无限制。当有了爱,当我放下了一切,当一切消融于那唯一的经验本身,就有了自由。为什么我不留在那里?为什么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恐惧、我对处境的执着、作为个体的我、我的银行账户、我的工作、我的这个或那个?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因为我疯狂。我们必须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我们的疯狂。我们必须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只要我们在以一种明知百分之百会失败的方式寻找快乐,我们就是疯狂的。我们必须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如果我们试图在囚笼中找到自由,我们就是疯狂的。疯狂并不太糟糕,但保持疯狂就是愚蠢。这种疯狂产生于我们被养大的方式,它告诉我们:你是这,你是“那”,你是无数的事物。而这样告诉我们的人明明知道自己是“一”。他们的目光同样远离他们自身,他们看的是监狱的栏杆、安全的假象。他们忽略自身,死死抓住各种虚假的“我”不放。这种我们从小就过的生活常常由职责组成,而职责不能代替爱。我们满眼都是责任:上帝要求履行一大堆责任,祖国要求履行一大堆责任,还有更多的责任——对学校的责任、对家庭的责我真正想要的是自由本身。自由不是摆脱依附,任、对邻居的责任等等。这是一个慢性死亡的好办法。有人会说:“你说得对,你总不能一直抄着手坐在椅子上吧。”我倒不会,可如果你还这么生活,这椅子就是你的归宿!如果你还这么生活,这椅子上的生活就将是你为你的孩子们一手打造的生活。因为没有爱的生活足以致残。 被好好养大的孩子,即常常被带往内心最深处的温暖中的孩子,发现在他们的存在之根基处,有着唯一的、真正的、绝不能被夺走的安全;他们乐意走出“监狱”,卸下防备。于是,他们获得自在。快乐之人不会懒惰地抄着手坐在椅子上,而是充满能量,愉快地工作,愉快地享受他人的陪伴,闪闪发光。 爱与快乐是离心的、发散的属性;恐惧、自私、贪婪、防御、执着则是向心的属性,它们是我们内在的束缚之源头。只有当我们乐意以某种方式卸下防备(无论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借助的是哲学还是心灵),内在的束缚才会消失。于是,向心的属性——束缚和挂碍——变成了离心的属性,我们感到自己不再笨重,而是变成了光。“他在街上快乐地跳舞”,这样的句子出现在很多书本中。他跳舞,他是光。但为了每天都能享受这种快乐(我们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它),我们用尽了办法却让这种快乐变得不可能——这一点就像昼夜交替那样确定无疑。我执显然让我们永远错失目标。但为了明白这一点,你不得不学会看清。 也许你和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而你们两个都是对的,这是争吵中常见的情况;或者,也许你们两个都是错的,但你是强势的一方,压倒了对方,自我感觉良好。当争吵结束,你觉得自己像个恶棍,这时你知道,如果你看向内心深处,就会发现胜利是空洞的。如果你原原本本地向人诉说实情,这时,你会感到挫败,你内心最美好的部分包裹着一层硬壳。换言之,这时,你背叛了你内心最深的部分。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人人都能在自己的生活中体会。如果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用能量喂养冲突,如果我们紧紧抓住外物、提出要求,我们就在自己和他人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凡是重新深刻地经验到无限温暖(我们称之为“爱”)的人,都知道不可能有任何高墙。爱的经验(也可以说成“状态”)在所有高墙消失的时刻显现出来。一个人能够去爱的强度取决于其高墙的厚度——墙越厚,防御越强,爱就越少。如果我们真的看透并自问“我真正想要什么”,那么我认为我们内心深处唯一的渴望就是:毫无保留地给出我们拥有的全部。只有给出全部——我拥有的全部和我所是的全部,快乐才是圆满的。 《新约》中有个经典比喻:种子如果不死,就不会结出果实。如果我真正诚实地看进内心深处,就知道我想要的是“死亡”——给出我所是的全部。在给予中,甚至会发现更多可给予的,于是你说:把那也带走吧,我连那也不要了。这的确是一种死亡。爱是一种自杀,而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像蝴蝶一样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的人很少获得爱的经验。 初到印度,我就见到了拉玛那·马哈希。生平第一次,我看见爱本身坐在椅子上,几乎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这毫不夸张。由于他的在场,在好几天的时间里,对于使我不能忍受的一切,我只能说:拿走吧,拿走我的一切。他的爱就像一束激光,将我穿透,与之不和谐的每一事物都显得突兀。于是,我的内心说,请把这也拿走吧。 我记得让·克莱因做过一个比喻:大多数人到古鲁那里是为了获取什么。他们以为自己是要去一家三星级餐馆,吃一顿真正美味的灵性大餐,然而,让他们吃惊的是,不是他们吃到了一顿美味大餐,而是主厨拿着一把大刀过来,切掉了他们的胃,掏空了他们的口袋,脱掉了他们的衣服,直到他们一无所有。这就是与古鲁相处的情形。究竟应该是我给予,我放下,我把一切融入了爱中;还是我正站在收银台前收款,我正在算计,我正把囚笼关着呢?你无须是个伟大的心理学家或哲学家,在我十四五岁时,我们家在战前雇的一个仅仅受过小学教育的保姆就为我解答了这个问题。你无须学习,你也无须是个老人或智者,孩童都能回答这个问题。这是选择,是选这种方式还是那种方式的问题。要么筑起高墙,要么推倒高墙——这个选择非常简单。 “你说得对,但是……”只要我们这么说,就在筑起高墙,这些话透露出恐惧。每天晚上,你都应该至少数到十,然后自问:我今天有没有减轻至少一克?有没有放下什么?有没有直面什么恐惧?有没有丢掉什么?或者我今天是否更沉重了?口袋是否更满了?有没有喂养我的反应?有没有保卫我的人格?我到底是远离了我的恐惧、要求和渴望,还是滋养了我的恐惧、要求和渴望? 我真正想要什么? 这是问题之一,它归结为如下问题:我真正是谁?我真正知道什么? 爱也许是最美的路。我没有说爱是最容易的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最容易的路,但在如下范围内,爱是最美的路:你无须经历危机,因为如果你再度容许爱,那么你的心灵会迸发出爱,爱会渗透你的头脑、你的整个存在,接着渗透你的家庭、你的工作场所。这种爱的释放是一场庆典,它是一条以平稳的加速度通往自由的路。如果你让事物消融于你真正所是的爱中,消融于你的存在深处,第一次虽然很难,因为你尚未习惯,但第二次就要简单得多。 我真正想要什么?我想要留在囚笼里,还是想要活在蓝天下?仿佛自由太艰难、太危险,或者认为自由在社会上行不通——“邻居会怎么想?”那是不明智的。不敢正视问题仅仅是因为缺乏理解力。假如我活得仿佛不是我的真正所是,使得我绝不能成为自己,那我就是在以最可怕的方式惩罚自己。我究竟做了什么,该受那样的惩罚?当你和密友在一起,你会说:在这里我能做自己,我爱自己,我就是自己。 如果我想要做自己,那么我只能接受自己。我要接受在我心中(就像在每一个人心中)有着无数的可能性,包括善与恶、美与丑。只要不接受这一点,就不可能快乐。只要我只想看到让私我高兴的东西,而拒绝看到让私我丢脸的东西,我就不会自由。只要我们像傻瓜一样地做事,我们就在显示自己缺乏理解力。也许我们需要一些勇气,但何者需要更多的勇气——是偶尔勇敢几个小时,还是在几十年里像干重活的马一样拖拖拉拉? 《圣经》里还说,真理将使你自由。只要我们活得仿佛不是自己,而是别人,我们就戴着沉重的镣铐。只要我表现得仿佛我是一幅漂亮的画,有着这个或那个优点,我就受到了束缚。于是,我会保卫这幅画:我对不迎合这幅画的一切变得愤怒,我只接受迎合这幅画的东西。换言之,我完全依赖于我的环境,我是周围环境的提线木偶,是我过去植入自身并已扎根的各种反应的奴隶。 我真正想要什么?我认为,做别人的奴隶也是一条路,但那样的话,你必须是个完完全全的奴隶。如果你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奴隶,以至于说“这个身体是你的,一切都是你的,我一无所有”,你就达到了和身在爱中相同的境地——在爱中,你也一无所有。但做完美的奴隶并不简单,我认为走爱的路更为简单。然而,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心中生起的各种感受的奴隶,一定不能被那些感受胁迫。如果我们敏锐地看,就会看到,在让私我不悦或愉悦的事情发生时,一种反应也随之生起。这种反应本身还不是一种束缚,但在它被视为“我”的时刻——“我”害怕,“我”要求、渴望或追逐某物——我们就置身囚笼中。相反,如果我们仅仅承认那是一种反应,那么我们甚至不需要心理学意义上的归因,比如,“我的这种反应归因于一个事实:小的时候,祖母把我弄倒过”。不,那是反应,而我不是一种反应。反应来来去去,而我是始终如一。所以,我不是一种反应,“我害怕”纯属谎言,“我愤怒”也纯属谎言。我是恐惧、愤怒、渴望、愉悦等反应的接收者。只是因为依附、执着于“我之感”,我才变得依赖于偶然出现之物。假如我的邻居有点心机,他就能确切地知道如何与我搭讪来引出我的特定反应,从而随心所欲地对待我。可见,我们喊的各种口号(比如支持或反对越南)不是因为我们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是因为我们已被操纵,或者可被操纵,原因在于我们害怕。 只要我们害怕,社会就能按照它想要的样子对待我们,环境就能按照它喜欢的样子对待我们。所以,我们不仅是自己的反应的傀儡,而且是环境和社会的傀儡。这显然和我们所知的自由状态相反,那是毫无限制的光明、温暖状态,使我们真正能够拥抱森林里的每一棵树。获得自由只不过是一再地放下,是明白我的安全不在于我的银行账户,也不在于我的力量或别的什么。世上没有什么是真正安全的。唯一真正安全的是最终无法从我这里拿走的东西——我自己。自由当然是因摆脱人格而来的自由。我已经说过,自由不同于目无法纪。自由不是出于一切皆有可能而去追逐你想要的任何东西——那正是我所说的囚笼。自由是独立于一切事物。此外,自由不是实现我执和人格,而是摆脱它们——我认为,每天留出片刻时间观看自己的最深处,看一看我真正是什么、真正想要什么,是绝对有必要的。因为我真正想要的就是我真正所是的。你最爱的是你的自我,还是爱本身?深入观看自我,就会发现这似乎是个不可 能的选择,因为我最深的自我就是爱本身;只有在爱中,我才是自己。在生命的源头,“爱”和“自我”指向同一事物——它只活在源头,而不活在各种防御工事或对补偿的寻求中。当然,“源头”这个词说明了一切。如果我抛弃源头,转而依赖人格、形象、感受、恐惧、挫折,那么我绝不能抵达自由。有个英文习语,译为“永远还有更多”,放在这里就是说,每一次得到补偿之后,“我”便立刻开始寻求别的什么。然而,当我让自己的最深处变得温暖,当我想方设法在深处再次觉醒(通过回忆爱在场时的情形;通过看清“我”不是我所保卫的一切;通过领悟防御让高墙耸立,而不是让温暖自由流动),筑起的高墙必定开始摇晃。 印度神话中有个巨人,每当他砍下敌人的脑袋,敌人的力量就成了他的力量。最后,他变得非常强大,没人能够打败他,渐渐地,他胆敢挑战诸神。这个故事的象征含义是,每一次胜利、每一个洞见、每一回放下恐惧或贪婪,都能巩固源头,把原先用于抗拒的能量加到源头上。这样,源头不断变强,而抗拒不断变弱,直到某个时刻,整面高墙轰然倒塌。于是,我们进入人人都经验过的那种状态,并立刻宣告:是的,这就是我真正想要的。 我真正想要什么? 如果我们稍稍深入自我,答案就会彻底显明。每一次我们放弃深入自我——我们筑起高墙、伸出爪子、追逐某种补偿、赢得空洞的胜利——也许我们背叛了别人,但最糟糕的是,我们背叛了最深的真我,而真我乃是我们真正想要、真正所是的。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说:“最重要的是忠于自我,这样你就不会愧对他人,二者如同昼夜相随。”这个顺序是对的。如果我们活在爱中,如果我们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只做自己、活在源头,那么,剩下的一切自然而然是该有的样子。每一次我们背叛自我,就是把刀子插进了自己的胸膛,即使我们认为插进的是别人的胸膛。 在寻找最深的自我时,不能接受权威给予的任何东西,必须亲证一切——是真是假?这类似于吃饭,没人能替你吃。如果你学的只是理论,动用的只是智力,则完全没用,还不如学习下棋、拉小提琴或做点别的什么。单纯学习理论对你没有帮助,自己看清、自己明白的,才能给你自由,理论只是额外的包袱。 (在谈话间歇,听众问了几个问题,其中有个问题是回应《瑜伽与吠檀多》中的一句话:“因为乙出自甲,所以乙不可能异于甲。”) 齐尔:我想,你们在听我讲的过程中已经明白这句话,不是吗? 提问者:是的。 齐尔那么幻觉呢? 幻觉是个念头! 如果你能把幻觉视为被错看了的真理,被错会了的光明,但仍是真理和光明,那么幻觉会消失。有时,人们发现恨是被扭曲了的爱:“我是如此想要爱你,但不知怎的出了错,现在我恨你。”然而,这种恨实际上是被扭曲的爱——发现这一点能让恨消失,让爱回来。同样,如果你把幻觉看作光明本身,幻觉就会消失。这是《瑜伽与吠檀多》一书的内容。 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切事物终究会爱一切事物。那时,碰到的是一个人、一只动物,还是自然,就没什么不同;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但也有些人觉得那样很烦人。 有些人认为如果你爱他们,你就是想要滥用他们。有时,孩子们被灌输了严格的性禁忌。这种女孩会认为所有男人都是禽兽,因为她们在男人和禽兽般的性行为之间建立了联结。男孩常常有着同样的畸形心理。即使一个正常的男孩爱上了一个女孩,女孩也会感到男孩想要占她便宜。如此一来,爱就被当成了某种与爱毫不相干的东西。人总是立足于自己所处的层面看待问题,而看不到真正在发生什么。借用刚才的例子,那个女孩看不到有人在爱她,她把爱理解成了兽性。所以,如果有人因为你拥有宽广的胸怀而烦恼,那么此人是有问题的!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就是向此人解释我们真的爱她,可是爱她并不意味着我们想要占有她、控制她或给她下套,恰恰相反,我们什么也不想要。然而,我们必须懂得爱是什么。 产生严重混乱的原因是,人们用“爱”一词意指更多的东西。我们用这个词指某些感觉,比如我们在和某个人、某种境遇或某段音乐发生关联时的温暖感:我爱舒伯特,我爱我的兄弟,我爱恋爱关系、性关系中的某人,等等。在这些例子中,我们谈论的主要是一种感觉,但爱是全然的自由,无关任何感觉。例如,在婚姻中,对伴侣的忘我的爱起初是一种感觉,但它超越自身,变成了空、变成了温暖,于是,伴侣消失了,一切消融了,唯有爱本身留存。这时,没有甲爱乙、乙爱甲,因为甲和乙已然消失,唯有无限者。这种爱带来一种洞察:这(这具身体)和那(另一具身体)都是我自己的所是之显现。在这一意义上,没有任何偏私;在这一意义上,没有谁比谁更接近你。 最终,爱是绝不会离你而去的东西,爱是“知晓”和“永恒的在场”的另一种表述。爱没有起始和结束。“爱的感觉”是通往爱本身的门户之一。所以,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无限的爱绝不会占有或想要占有任何东西、任何人。怎么可能占有?那就像我的右手想要占有我的左手一样没有意义。在爱中,没有占有者。如果爱能够占有什么,那就是宇宙本身;要么是全体,要么是无,你可以说是任何一者,但不是一个碎片,你无法将自己分割成碎片。你是他人眼中的爱。把你带进真理、自由、爱中的古鲁是爱本身,他对你所是的爱本身说话。你原先把古鲁视为个人是因为你把自己视为个人。 你发现,如果你不再对他人的攻击做出反应,他很可能会认为你傲慢、冷漠,甚至疯狂。 他会认为你这个人已经变得冷漠,但他完全错了,冷漠是封闭、抗拒,而情况恰恰相反。然而,他是如此习惯于为了他的利益、为了他的高墙和牢笼而斗争,以至于当有人快乐,他就生气,并说那人自私。可这样说的人自己在做什么?他也在寻找快乐,只是不知如何才能找到,他误以为可以通过加固囚笼获得自由。在他发现私我绝不能快乐的时刻,他就停止了斗争,于是,他也被周围人当成了冷漠之人。我想,我们都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其间,别人对我们说:“丢掉私我是非常自私的,你只会孤立无援。”但在某个时刻,他们定会发现,出现了某种新的东西,某种他们无法准确地指出的东西,这种东西比以前拥有的更珍贵,比以前出现的更吸引人。有时,你会看到他们开始理解。 我们害怕自由,我们被培养成了奴隶。首先是父母的培养。我们不得不成为父母认为我们必须成为的样子,他们对于一个乖孩子应有的样子抱有某种想象,而我们必须成为那样。由此,我们学会了扮演一个角色,而不是成为我们的所是。那就是日常神经症的起始,那就是我们如何长成了一层盔甲套着另一层盔甲的样子。现在,自由突然被给予我们,这把我们吓坏了,我们害怕自己不得不面对未知的彻底的孤独。 因为恐惧自由,我们必须拥有一个父亲。弗洛姆(Fromm)写过一本相当有趣的书,就叫《恐惧自由》,你可以读一读。该书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选择了独裁统治者。一个人想要拥有一个父亲,并根据父亲主宰的家庭来思考:父亲为你着想,为你做决定,并保护你。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不想要自由,害怕自由。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发现自由是恐怖的。如果我们有点神经质,甚至会发现失去问题是恐怖的——没有了问题我该怎么办?在荷兰,有个关于精神病人的笑话:“我很高兴自己不喜欢菠菜,因为如果我喜欢菠菜,就不得不吃菠菜,而我不喜欢菠菜。” 这个精神病人的主要症结在于恐惧康复:假如我康复了,我就必须做各种不喜欢的事。病人不明白,如果他康复了,他会发现那些事根本没有那么糟糕,它们实际上会自行完成,它们根本不是高山,而是小土堆。我们都熟悉病人的心理,因为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这种心理。在有的时刻,你变得害怕康复,害怕推倒你的高墙,因为你感到躲在高墙后面是如此安全。但感到安全的是谁呢?是高墙感到安全。事实上,高墙后面没有人。反过来才是自然的,即高墙代表不安全。你为什么感到不安全?因为你筑起了高墙去对抗环境。如果你与环境融合,就不存在不安全。 让我们举个确切的例子吧。什么是恐惧?恐惧是一个机制,人们期望用它来阻止不幸。当一个小孩靠近暖气机,你会说:当心受伤!由此,你植入了一种恐惧,用来阻止小孩触摸暖气机。这是一种有益的恐惧。但现在,让我们把恐惧移植一下:我恐惧你,我恐惧某物会被夺走,我恐惧必须做什么,等等。原是用来防止不幸、防止小孩烫伤手指的恐惧,现在被当成了一服药。但这比疾病更糟糕。恐惧本身是疾病,可以变得很离谱。有人试图向我解释他的问题:他不仅害怕恐惧,而且害怕恐惧恐惧!不要试图去理解他,让我们止步于恐惧的存在。如果我一再地承认恐惧感的存在,恐惧就会消失。我们想要的是让恐惧消失,而不是培养对恐惧的恐惧。我相信,如果你今晚认真听了我的话,那么你已经完全明白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那么,就让我们把全部的樊篱扔进爱的火里。爱乃是我们的所是,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提问者:我认为“当下”的念头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把它视为一个认识者。 齐尔:是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避免把一个“认识者”投射在思考上。你认为你的头脑中有个“思考者”,如果它消失了,你的头脑中还有一个“认识者”,但那不是真正的认识者。你不应该把人格投射在认识者上,而要试着明白,念头只不过是意识本身,因为念头没有人格味,你要把念头视为意识本身、认识本身。 提问者:真的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但仍然生活在幻中,那是怎样的? 齐尔:在我看来,那是我们常常谈到的“空”的开端。人人皆知“我是一”,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重要直觉。围绕着这个中心,从童年到老年,我被植入了各种小小的“我”——我是这,我是那,它们都是抗拒的高墙。我不是作为真正的中心(“我是我所是”)而活,而是作为短暂地投射出来的一个角色而活。有一天,我会明白,这些“我”不是真正的我,它们全都是角色,出现又消失,其中有些角色出现在醒态,还有些出现在梦态;但我不是一个出现又消失的“我”,我始终是在场。 渐渐地,这些小小的“我之感”趋于消失。随后,有段时间,你几乎没有问题,没有大的困难。你活在一种等待的状态中,那是“不知之空”在彰显自身。只要还有一丝“我是一个……的人”,空就不是完完全全的。但在某个时刻,我们会达到彻底的“不知”:人格就像一把椅子,一无所知。 提问者:这是不是让·克莱因所说的“我不知道”的意思? 齐尔:是的,就是这样。作为人格的“我”不比这张桌子知道得更多;作为人格的“我”是认识客体,就像这张桌子一样。当空在各个方面变得完完全全的时刻,光明自显。但这样表述相当粗略。我说的完全是真的,从这一刻到下一刻,空变成了圆满。但如果我说空一点点地变成圆满,那也是真的。无知、误解、错会一点点地消失,我的恐惧也必定一天天地消失,而我则会变得愈发光明。我比以前更加敏锐,我的身体更加敏感,我不再堵塞,等等。如此这般逐渐推进,直到一切变得透明,空变得完完全全。 1. quan书由23篇独立的文章组成,旨在回应人们在瑜伽实践中的普遍困惑。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23篇文章几乎涵盖了一个人内在探求的所有重要方面。一书在手,无须他求。 2. 除了瑜伽大师的身份,作者沃尔特?齐尔生还是一名专业文字工作者,他的文字严谨且富有张力,常能在将复杂而近乎难以言传的思想和盘托出的同时,不失其可读性。quan书23篇文章,篇篇精彩。 3. 此书作者生也逢时,得一并亲炙印度近代三贤,是一位当世罕见的解脱者。 他以“过来人”的视角,扫视来时路,将修行之路上的岔口与坑洼详为标记,而成此书。无有古鲁者,可奉此书为古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