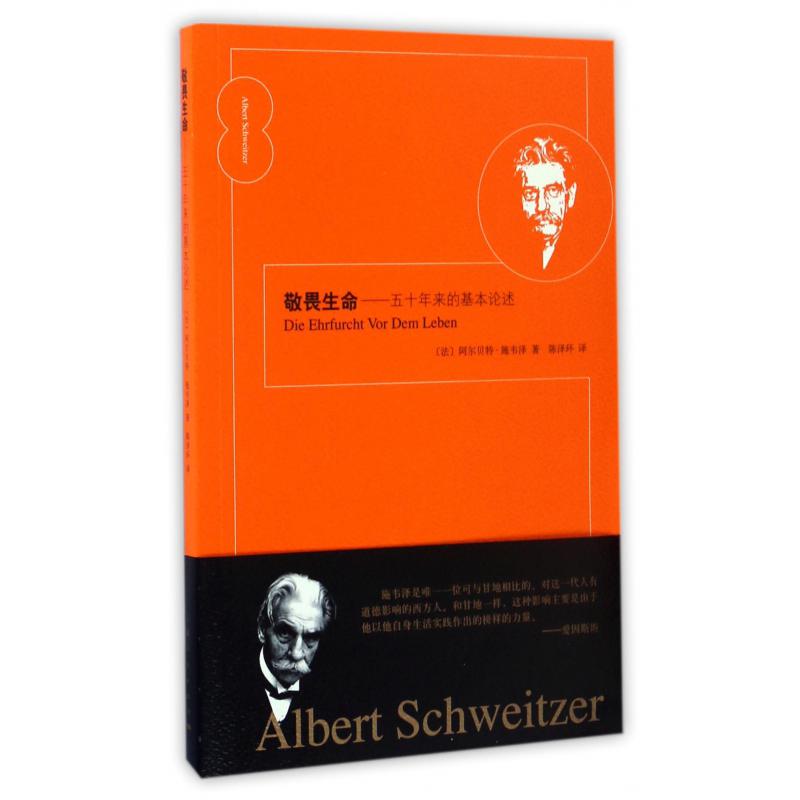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人民
原售价: 36.00
折扣价: 23.80
折扣购买: 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
ISBN: 97872081405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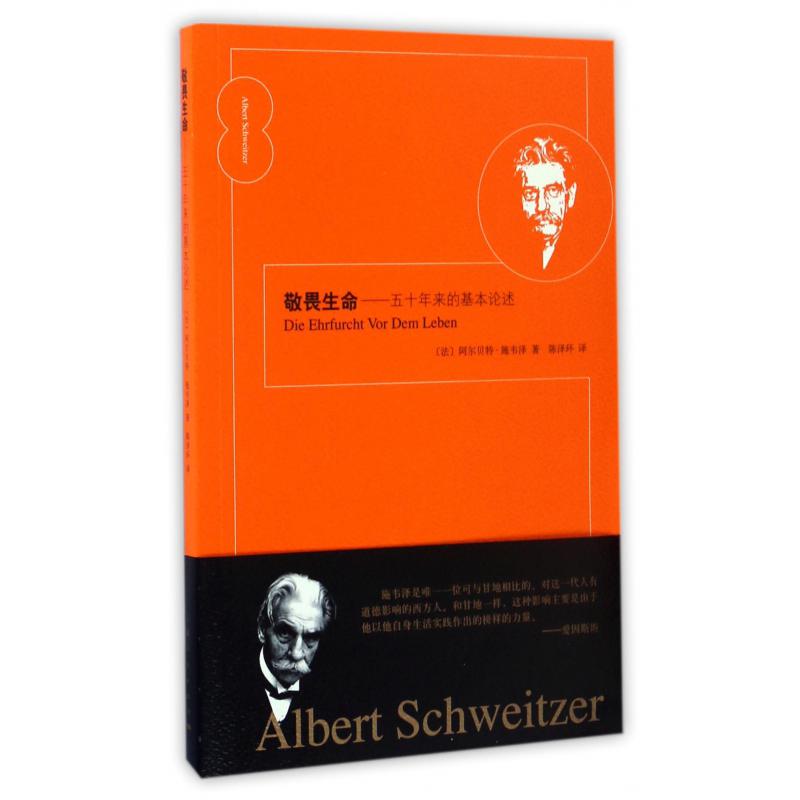
阿尔**·施韦泽1875年出生于法国上阿尔萨斯,青年时代多才多艺,不仅是神学博士和哲学博士,而且还是一位享有盛名的管风琴演奏家和巴赫音乐的研究家。38岁时获医学博士,取得医生执照,1913年携妻子一起前往非洲的兰巴雷内(现在属于加蓬),在那里创建了自己的诊所,义务为当地居民治病,六十年如一日,历尽艰辛,直到1965年逝世。195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陈泽环,1954年生于浙江宁波,1971年上海市第二中学毕业后进上海重型机器厂工作。1979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3年获哲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哲学硕士学位。1986年至2003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89年至1991年、1995年至1996年、2000年、2002年、2005年先后在德国的柏林洪堡大学、卡尔斯鲁厄大学、汉诺成哲学研究所、慕尼黑大学、卡尔斯鲁厄师范学院访学。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伦理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包括道德理论、德国伦理学、道德建设、经济伦理学等方向。自1983年起至今,先后出版《敬畏生命——阿尔**·施韦泽的哲学和伦理思想研究》、《道德结构与伦理学——当代实践哲学的思考》、《个人自由和社会义务——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研究》、《功利·奉献·生态·文化——经济伦理引论》等专著7部;出版《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敬畏生命——50年来的基本论述》、《对生命的敬畏——阿尔**·施韦泽自述》、《文化哲学》等译著10部;发表《论西方伦理学的道德论证》、《梁启超论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施韦泽的中国思想研究》、《儒学创新与人权》、《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自主性与根基性》等论文160余篇。
1.敬畏生命理论的产生及 对我们文化的意义。 小时候,我就感到有同情动物的必要。当时,我 们的晚祷只为人类祈祷,这使尚未就学的我迷惑不解 。为此,在母亲与我结束祈祷并互道晚安之后,我暗 地里还用自己编的祷词为所有生命祈祷:“亲爱的上 帝,请保护和赐福于所有生灵,使它们免遭灾祸并安 宁地休息。” 发生在七八岁时的一件事使我难以忘怀。我的同 学海因里希·布雷希和我用橡皮筋做了弹弓,它能用 来弹小石块。当时是春天,正值耶稣受难期。在一个 晴朗的礼拜天早晨,他对我说:“来,现在我们到雷 帕山打鸟去!” 这一建议使我吃惊,但由于害怕他会嘲笑我,就 没敢反对。 我们走到一棵缺枝少叶的树附近,树上的鸟儿正 在晨曦中动听地歌唱,毫不畏惧我们。我的同学像狩 猎的印第安人那样弯着腰,给弹弓装上小石块并拉紧 了它。顺从着他命令式的眼光,我也照着他的样子做 了。但由于受到**的良心谴责,我发誓把小石块射 向旁边。 正在这一瞬间,教堂的钟声响了,并回荡在朝霞 和鸟儿的歌唱声中。这是教堂大钟召唤信徒的“主鸣 ”之前半小时的“初鸣”。 对我来说,这是来自天国的声音。我扔下弹弓, 惊走了鸟儿。鸟儿因此免受我同学的弹弓之击,飞回 了自己的窝巢。 从此,每当耶稣受难期的钟声在春天的朝霞和树 林中回荡时,我总是激动地想到,它曾怎样在我心中 宣告了“你不应杀生”的命令。 在我青年时代就存在的动物保护运动的复兴,也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终于敢在公众中坚持并 宣告:同情动物是真正人道的天然要素,人们对此不 能不加理睬。我认为,这是在思想的昏暗中亮起的一 盏新的明灯,并且越来越亮。 自1893年起,我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哲学和神 学。在这世纪末的日子里,我们大学生共同经历了一 些值得注意的事件:尼采和托尔斯泰各种著作的传播 。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他的学业几乎 还未结束,就被聘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学教授。 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只研究古希腊文化及精神,而且 也从事一般文化问题及精神的研究。从1880年起,尼 采表示反对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传统的欧洲文化。他谴 责这种欧洲文化,认为在其中占**地位的是人之软 弱和畏缩的精神,它产生了要求爱他人的伦理。为了 保护这种伦理,它还创立了天国希望的理论。 根据尼采的想法,真正文化的伦理只能是对生活 的自豪和勇敢的肯定,“超人”并不受爱的“奴隶道 德”的约束。他坚持“强力意志”的主人道德。 尼采以极大的**阐发了这种关于文化和伦理之 本质的新观点,对当时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 但就在那时,即那个世纪末的时刻,托尔斯泰 (1828_1910)的著作也在公众中流行。在他的长篇和 短篇小说中,这位俄罗斯作家和思想家代表了一种不 同于日耳曼的世界观。托尔斯泰肯定伦理的文化,他 认为伦理的文化是他在自己的经历和思考中获得的深 刻真理。通过他的短篇小说,托尔斯泰使我们了解到 :他是如何认识真正人道和质朴虔诚的。 我们19世纪末的年轻人,就这样与两种不同的世 界观打交道。 在这种状况中,我曾经产生过极大的失望。我期 望宗教和哲学能够共同有力地反对和驳斥尼采,但这 种情况没有出现。也许,它们已经表示过对尼采的反 对。但是我认为,宗教和哲学没有能够也没有尝试在 尼采对它们挑战的深度上阐明伦理的文化。 作为一个大学生,我本人在世纪末期就开始思考 这个问题:我们的文化是否真正具有不可缺少的伦理 动能?这促使我研究文化和伦理问题。在19世纪后半 叶,这个问题受到哲学界的普遍重视。我发现,当时 欧洲*重要的哲学文献根本就不认为文化和伦理是一 个问题;相反,它们把文化和伦理作为既成的精神成 就而接受下来。 我自己则不能摆脱这种印象:人们认为永恒的伦 理并没有向人类和社会提出重大的要求,它是“处于 休息状态”的伦理。 从而,19世纪末,当人们为了确认和评价这一世 纪的成就而回顾和考察各个领域时,流行的是一种我 无法理解的乐观主义。人们似乎普遍相信,我们不仅 在发明和知识方面取得了进展,而且在精神和伦理领 域也达到了一个***和再也不会失去的高度。但 我认为,我们的精神生活似乎不仅没有超过过去的时 代,而且还依赖着前人的某些成就;*有甚者,其中 有些遗产经过我们的手而逐渐消失了。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