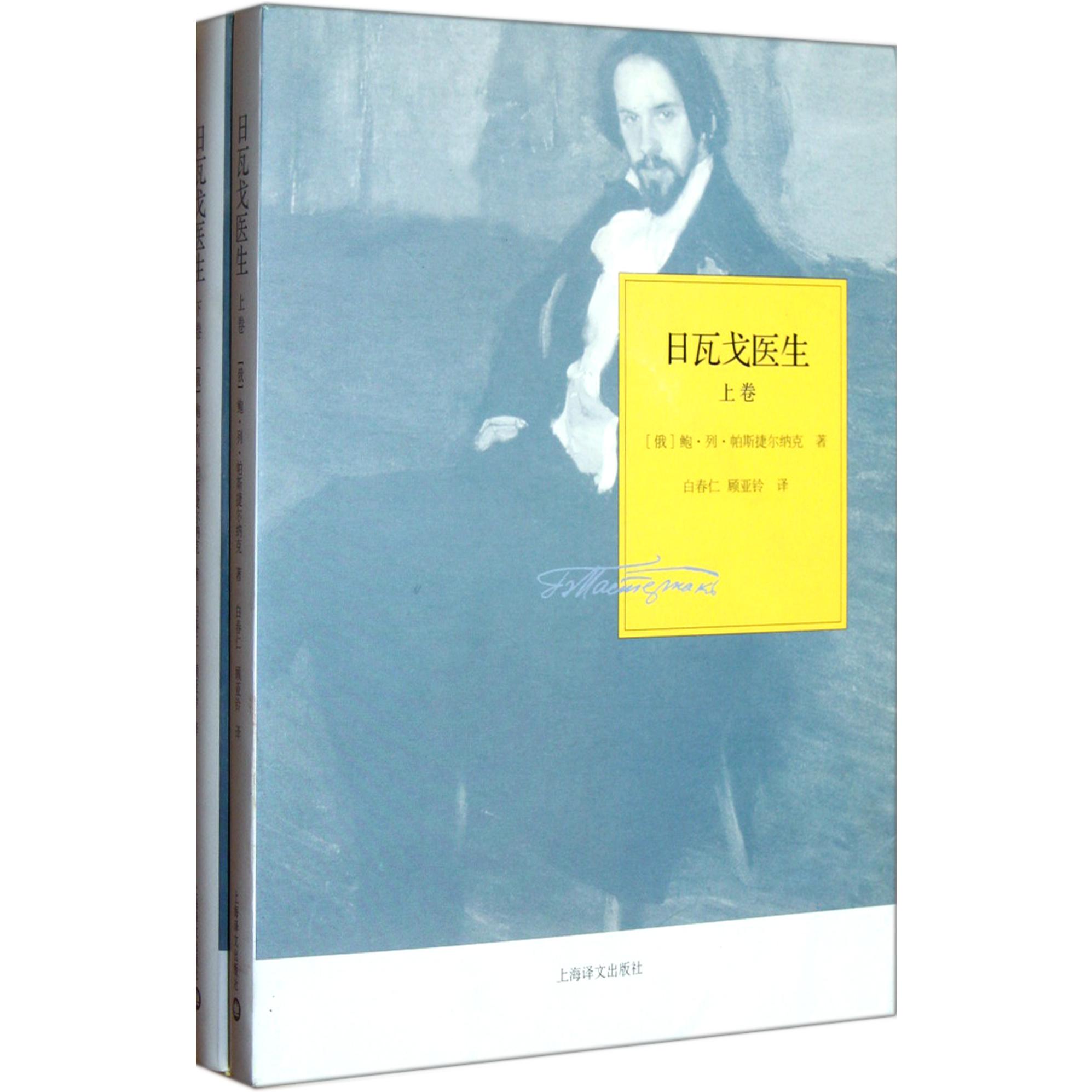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译文
原售价: 54.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日瓦戈医生(上下)
ISBN: 9787532756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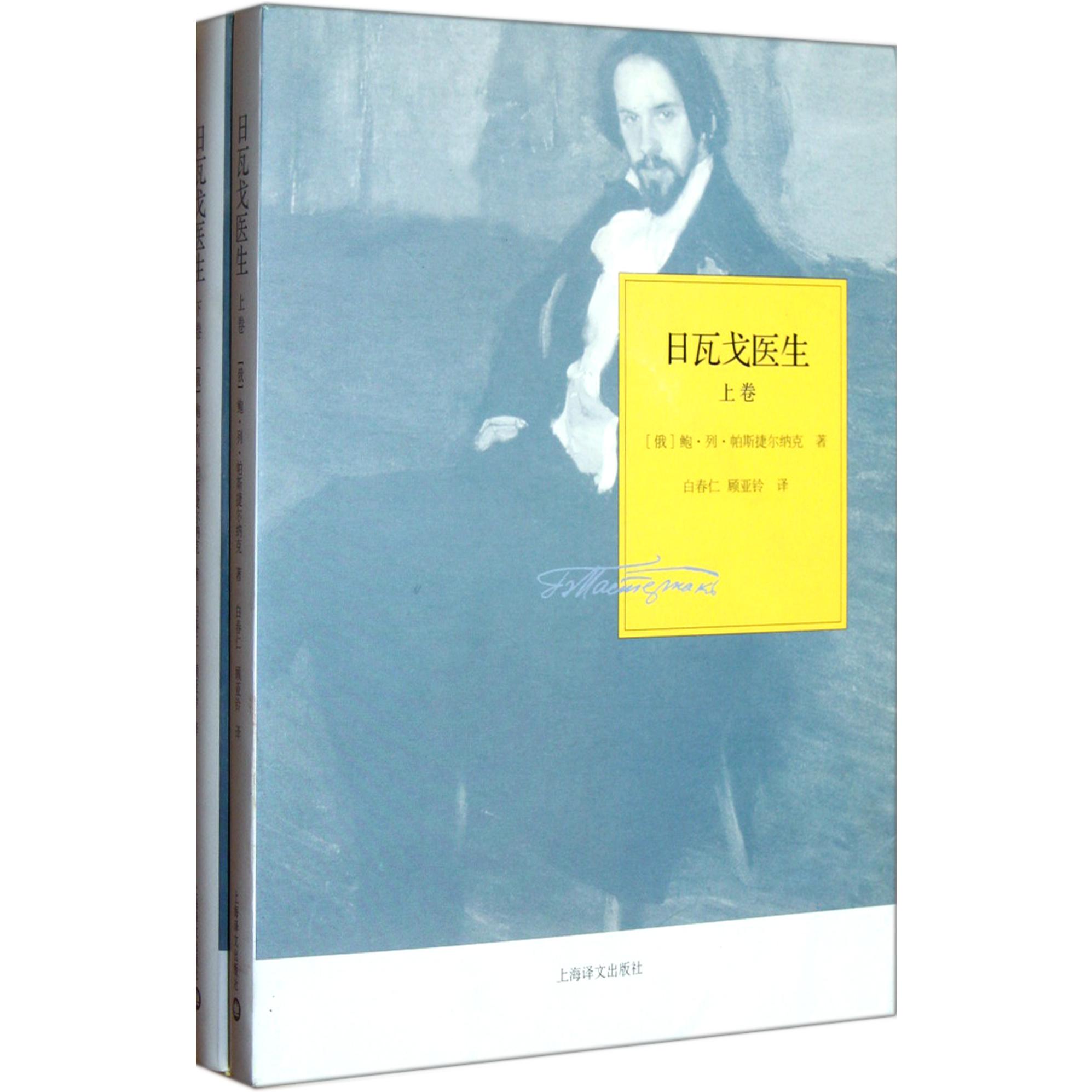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俄国诗人,作家。代表作有诗集《我的姐妹——生活》、自传体随笔《安全保护证》和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一九五八年诺贝尔文学奖。
在盛大葬礼完毕之后,人们通常会变得迟钝麻木。只有在这种状态下, 大家才可能觉着这孩子站在母亲的坟茔上似乎想说些什么。 男孩抬起头,在坟头上茫然环视四周荒凉的秋野和修道院上的圆顶。长 着翘鼻子的脸上,神色异常。脖颈伸得长长的。如果一只小狼崽这样仰起头 来,不用说它就要哀嗥了。这时孩子双手掩面,失声恸哭起来。迎面刮来的 乌云泼下冷雨,仿佛用湿鞭抽打他的脸和手。坟前来了一个男人,穿着窄袖 皱边紧口的黑色丧服,这是死者的兄弟,那哭泣的孩子的舅舅——尼古拉 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他原是个神甫,自愿还了俗。他走到男孩跟前 ,领着他离开了墓地。 他们在修道院里一间单身修士房中过夜,因为舅舅是这里的老熟人,才 让借住的。这天正是圣母节的前夕。第二天,舅孩将和舅舅一起去南方伏尔 加地区的一个省城。舅舅在一家发行地方进步报纸的出版社工倌。车票已经 买好,行季也已打捆放在屋里。火车站离得很近,寒风拂过,传来不远处机 车调头时发出的凄厉的汽笛声。 傍晚,天气骤然变冷。从屋里两扇落地的窗子向外望去,可以看到,败 落的菜园一角,菜园四周丛丛刺槐;凭窗还可以看到大路上冻冰的水洼,墓 地中白天安葬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的那个角落。菜园里除了几畦冻青了的 卷心莱外,周围一片荒芜。劲风吹来,叶落,枝疏的刺槐,便狂摇乱舞,伏 倒在大路上。 深夜,尤拉被窗子的响声惊醒。黑暗的小屋闪烁着一种神奇的、飘忽不 定的白光。尤拉只穿着衬衣跑到窗前,把脸紧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窗外既看不见道路,也看不见鏖地和菜园,只有暴风雪在肆虐,雪花纷 纷扬扬,漫天飞旋。也许是暴风雪发现了尤拉。暴风雪意识到自己有无限的 威力,洋洋得意地显示自己如何震慑住了孩子。它呼啸着,狂吼着,千方百 计想吸引尤拉韵注意。白茫茫的风雪巨浪,一层又一层从天空不停地倾泻到 地面上,、仿佛是一块块白色的裹尸布,笼罩在大地上。此刻世界上唯有暴 风雪在大施淫威,没有什么堪与它相匹敌。 尤拉爬下窗台,第一个念头就是穿上衣服,跑到院子里去做点什么。他 一会儿担心修道院的白菜被风雪埋住,再也挖不出来了,一会儿又害怕母亲 被埋在雪里,无力反抗,会越陷越深,离他越来越远。 结果他又哭了一场。舅舅从梦中惊醒,给他讲基督对人们的保佑,安慰 了他一番。然后舅舅打个哈欠,走到窗前沉思起来。他们开始穿衣。天光渐 渐发亮。 母亲在世的时候,尤拉并不知道父亲早已遗弃了他们母子俩。父亲浪迹 于西伯利亚和国外形形色色的城市,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并且早把万贯家 财挥霍一空。人们总是告诉尤拉说,他父亲有时在彼得堡,有时去参加商品 交易会,最常去的是伊尔比特。 后来,一向多病的母亲发现得了肺结核。她开始常去法国南部和意大利 北部治疗,尤拉陪她去过两次。他常被托付给别人照料,这些人又常常更换 。就在这种动荡和不断的猜测中,尤拉度过了童年。他已经习惯了这类变化 ;在长期不安定的生活环境里,父亲不在家,对他来说也不足为奇。 他小时候还赶上了日瓦戈家族的好时光,那时他家的姓,常被人们用去 给许多极为不同的事物命名。 当时曾有过日瓦戈纺织厂、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公寓、系领带和别领 带用的日瓦戈佩针,甚至有一种浸糖酒的圆形蛋糕也叫日瓦戈;有一个时期 ,在莫斯科对马车夫说一声“去日瓦戈家”简直就像说了句“去爪哇国”, 车夫就会拉着雪橇把你送到一个遥远的“国度”,你会进入一座宁静的花园 。低垂的云杉枝,挂着白霜,乌鸦飞落枝头,霜花簌簌而下。乌鸦的呱呱声 传到远处,仿佛是树枝折断的声音。几只纯种猎狗,从林中通道后边的新房 子那里,穿过大路跑来。那里已时近傍晚,灯火通明。 然而,转眼间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他们的家业衰败了。 一九○三年夏季,尤拉和舅舅坐着四轮马车去乡下的杜普良卡庄园,探 望教师兼科普作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波伊尼科夫。这庄园是丝绸厂 老板科洛格里沃夫的产业,他同时又是热心的艺术赞助人。 那时正值喀山圣母节,收割大忙的日子。他们到时,田里一个人也没有 ,也许去吃午饭,也许过节去了。呔阳热辣辣地晒着没割完的麦地,仿佛是 给犯人剃的阴阳头一般。鸟儿在麦地上空旋舞。田野上没有一丝风,麦秆笔 直地挺立着,坠着沉甸甸的麦穗;割下的麦子一垛垛高高地摞在路那头很远 的地方。久久细望过去,它们仿佛成了一个个走动羞的人,正在地平线上测 量,一边记录着什么;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向侧身坐在赶车座上的帕维尔说:“这里的地是 谁家的?”帕维尔是出版社的听差和看门人。他坐在那里:弓着背i跷着腿 ,表示他并非马车夫,驾车不是他的本分。 “这片地是地主老爷的,”帕维尔答道,一边点着烟,“前边那些地, ”他点着了烟深吸一口,过了半晌才用鞭梢指着另一边,说道,“那些地是 农民自己的。驾!怎么睡着了?”他不时对马吆喝着,眼睛总瞟着马尾和后 臀,就像火车司机盯着压力表一样。P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