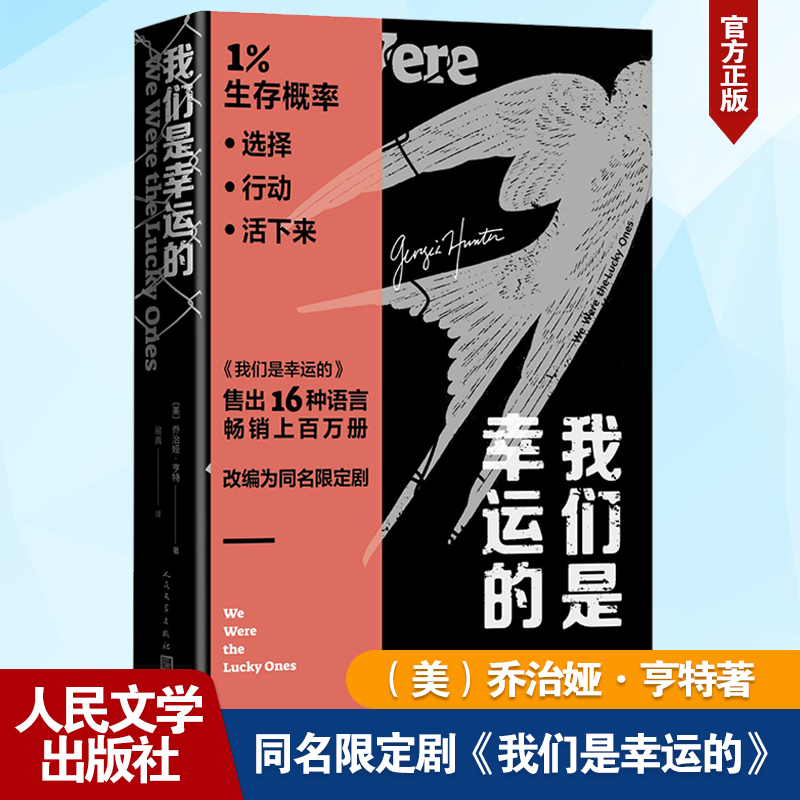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89.00
折扣价: 58.80
折扣购买: 我们是幸运的
ISBN: 9787020184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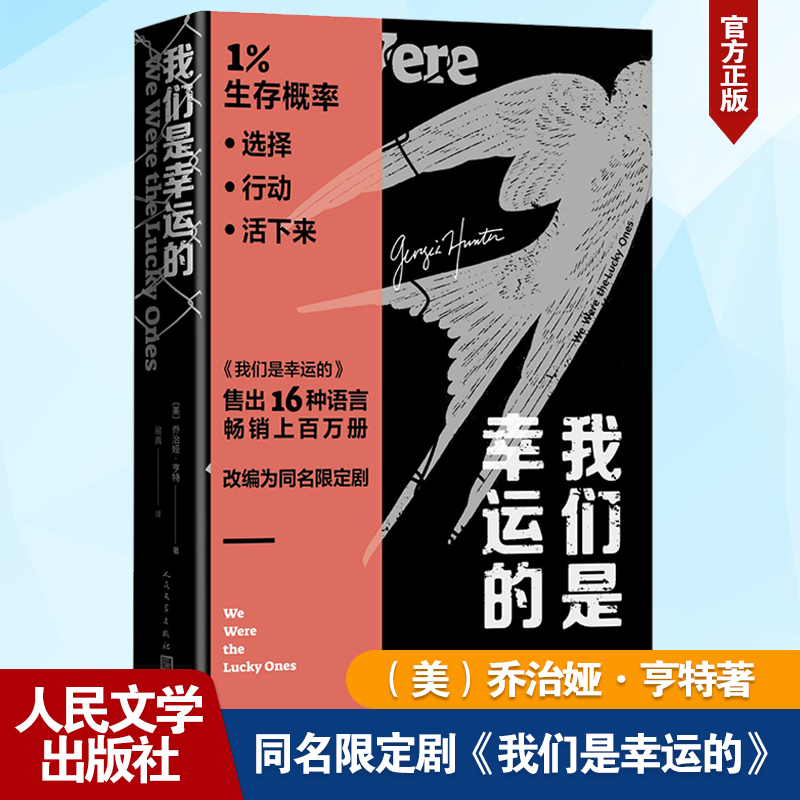
作者简介: 乔治娅·亨特(Georgia Hunter, 1978— ) 美国作家,出自一个在“二战”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家庭。自幼热爱写作,1994年,高中生的她得知外祖父那一代在“二战”中的经历,2000年与库尔茨大家族聚会,2008年开始深入研究和挖掘家族故事,历经十数年写成《我们是幸运的》。这是作者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目前她与丈夫、儿子生活在康涅狄格州。 译者简介: 易真 自由译者,译有《心灵之歌》《天外来客》《我们是幸运的》、《归来记》(即将出版)等。
后记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以为外祖父埃迪(故事中阿迪·库尔茨的原型)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是位成功的商人。他的英语在我听来十分纯正。外祖父住在一幢很大的现代化宅子里,顺着我们家所在的街道往前走便是,家中的落地窗从天花板直通地面,门廊很大,适合进行各种娱乐活动,私人车道上还停着一辆福特车。他唯一教过我的儿歌是用法语唱的,食品储藏室里绝对不能放番茄酱(外祖父管番茄酱叫化学物质),家里大半东西都是他亲手制作的(比如他设计过一个奇妙的装置,利用磁铁把香皂挂在洗手间水槽上以保持干燥;还有摆放在楼梯井的黏土半身像,原型是外祖父的孩子;他把地下室改造成雪松木桑拿房;客厅的窗帘也是用外祖父手工制作的织布机编织而成),虽然有这么多奇怪的地方,但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太多。外祖父有时会在餐桌上说 “不要降落在你的豌豆上”这样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有些古怪罢了,而且一旦我用“哦”或者“嗯嗯”来回答,他就会假装没有听见,“是的”是唯一正确的回答,因为这才符合他的语法标准,这些事有时让我抓狂。现在回想起来,若是换作其他人,应该会给外祖父这些习惯贴上“不同寻常”的标签。但当时的我还是个孩子,只有和外祖父一起生活的经验,对其他的事情一窍不通。即使母亲现在告诉我外祖父在说英语时语调会有轻微变化,我也会假装听不出来,对于外祖父的那些怪癖,我也会装作视而不见。我深爱着外公;他就是简简单单地在做自己。 当然,外祖父身上有许多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要提的就是他的音乐。我从未见过有谁像他那样醉心于艺术。他的书架上堆满33转唱片,按照作曲家姓氏排序,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关于钢琴曲的书籍。外祖父家里永远在播放音乐——爵士、蓝调、古典,有时还会播放自己的专辑。去外祖父家时我总能看见他坐在施坦威钢琴前,耳朵后面塞着二号铅笔,他正在构思新作品的旋律,对着琴键反复推敲练习直到满意为止。外祖父偶尔会让我坐在旁边看他弹琴,每次近距离观摩都会让我心跳加速,我会等他轻轻点头,这是给乐谱翻页的信号。“谢谢,乔吉。”外祖父会在演奏结束时向我道谢,我会满脸笑容地抬头看着他,为能帮上忙而骄傲。大部分时候,等外祖父结束手头工作,他就会问我要不要上一课,而我每次都会说好——倒不是因为我和他一样喜欢钢琴(我从来就不擅长弹钢琴),而是因为我知道他在教我时有多开心。他会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入门书籍,我会把手指试探性地放在琴键上,感受身旁外祖父大腿传来的温度,我会尽可能地不犯错,外祖父会耐心地教导我,从只有几小节的主旋律到海顿的《惊愕交响曲》。我特别希望自己能给外祖父留下一个好印象。 除了精湛的钢琴演奏技巧,外祖父还精通七国语言,我对他十分敬畏。我想这种熟练驾驭语言的能力应该归功于他设立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还有他的亲人定居在巴西和法国,不过外祖父那辈我知道名字的只有哈利娜,她是外祖父的妹妹,两个人关系尤其亲近。她住在圣保罗,之前来家中拜访过几回,除了她之外,还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表亲偶尔会在夏天时从巴黎过来和我们待上几周,说是为了学习英语。看来外祖父家族里每个人都至少能说两门语言。 小时候的我并不知道外祖父原来出生在一个波兰城镇,那里曾经居住着三万多名犹太人;他出生时不叫埃迪(后来他给自己改了名字),而叫阿道夫,不过从小到大每个人都喊他阿迪。我不知道他是五个孩子中的老三,也不知道他有将近十年时间都在担心家人的下落,他不知道亲人是活过了战争,还是死在了集中营,抑或是和数千名犹太人一起在波兰隔都被杀害。 外祖母并不是有意对我隐瞒——这些只是外祖父选择抛下的过去生活片段。来到美国以后,他重塑自我,把大部分精力和创造力都放在了现在和未来。他不是会沉湎于过去的人,而我也从未想过要问他那些往事。 1993年,外祖父因帕金森病去世,那年我十四岁。一年后,高中英语老师给我们班布置了“寻找自我”的作业,旨在教会我们如何运用调查研究的技巧来挖掘祖先的过去。趁着亲人对外祖父的记忆仍然清晰,我决定坐下来采访我的外祖母卡罗琳,她是外祖父携手相伴近五十年的妻子,我想通过她来了解外祖父的故事。 正是通过这次采访,我第一次知道了拉多姆,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地方对曾经的外祖父来说有多重要,更不知道这个地方对后来的我又有多重要——以至于二十年后,我会亲自拜访这座城市,走在铺满鹅卵石的大街上,想象在这里成长会是什么模样。外祖母在地图上点出拉多姆的位置,而我则说出了内心的疑惑,我想知道外祖父有没有在战争结束后回去过。没有,这是外祖母的回答,埃迪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去。她接着解释道,1939年纳粹入侵波兰时埃迪刚好在法国,因此他是家族里唯一一位在战争开始时就逃离欧洲的人。外祖母告诉我外祖父曾经和一个在“阿尔西纳号”客轮上认识的捷克女人订过婚;外祖母与外祖父第一次见面是在里约热内卢伊帕内马的聚会上;两个人第一个孩子凯瑟琳也出生在里约,时间就在外祖父和家人团聚的几天前——他已经和父母、兄弟姐妹、姑伯姨舅还有堂表亲分开了近十年。超过九成的波兰犹太人死于战争,而生活在拉多姆的三万名犹太人,生还者只有三百来人(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外祖父的亲人竟然都以某种方式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外祖父的家人在巴西安顿下来之后,外祖母继续说,她和外祖父一起搬去了美国,我的母亲伊莎贝尔和舅舅蒂姆相继出生。外祖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名字从阿道夫·库尔茨改为埃迪·考茨,并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他翻开了人生的崭新一页,外祖母说。当我问到外祖父有没有保留从旧世界带来的习惯时,外祖母点了点头。他几乎从来不提自己的犹太人背景,也没人知道他出生在波兰——但他总会在不经意间暴露这些特点。就像钢琴是他成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祖父坚持让自己的孩子每天练习乐器。吃饭时必须用法语对话。在邻居还没听过意式浓缩咖啡时,外祖父老早就开始喝了,而且他很喜欢在波士顿赫马基特广场和那些露天商贩讨价还价(他经常会在那里买上一包牛舌,并且坚称这是美味佳肴)。他唯一允许家里人食用的糖果就是他出差去瑞士后带回来的黑巧克力。 外祖母的采访结束后,我感到有些晕头转向。就像掀起了一层面纱,我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外祖父的人生。现在的我终于意识到,他身上的那些奇怪之处,还有我之前认为是怪癖的那些特点,其实都源于他的欧洲血统。这次采访反而勾起了我更多的疑问。外祖父的父母经历过什么?他的兄弟姐妹呢?他们是怎样在战争中活下来的?我缠着外祖母告诉我更多细节,但关于那些姻亲的事情,外祖母知之甚少,她只能告诉我一些细枝末节。我是在战争结束后才第一次见到他的家人,外祖母说,他们几乎从不谈论自己的经历。回到家中,我问母亲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外祖父有没有跟您说过他在拉多姆长大?他有没有跟您提过战争的事情?这些问题的答案总是没有。 时间来到2000年的夏天,大学毕业几周后,母亲提议在我家位于马撒葡萄园岛的宅子里举办库尔茨家族聚会。她的堂表亲纷纷赞同——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而下一代更是有许多人连见都没见过。是时候来一次久别重逢了。主意敲定后,这些堂表亲(一共十人)开始安排各自的行程,七月就这样过去,库尔茨家的人从迈阿密、奥克兰、西雅图、芝加哥,还有更远的里约热内卢、巴黎、特拉维夫等地赶来。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和配偶,我们数了数,一共有三十二人。 重聚的每天晚上,吃罢晚餐,母亲那一辈人便和外祖母聚在屋后门廊聊天。我晚上一般都和堂表亲待在一起,我们慵懒地坐在客厅沙发上,互相交流音乐和电影方面的爱好与品位(为什么那些巴西和法国来的堂表亲竟然比我还了解美国流行文化)。但最后一天晚上,我来到外面散步,坐在凯思大姨身边的长椅上,听她们讲故事。 虽然母亲的堂表亲分别来自不同地方,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成长经历,说着不同的语言,有些人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但大家聊天时却很轻松自然。整个过程充满欢声笑语,有人唱起了歌(一首波兰摇篮曲,这是里卡多舅舅和他妹妹安娜的童年回忆,兄妹俩说这是外公外婆教给他们的),有人讲了一个笑话,大家笑得更开心了,众人举杯祝福外祖母,她是外祖父这辈唯一健在的老人。他们说话时会在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之间来回切换;我能做的就是尽全力跟上大家的节奏。还好我做到了,长辈围绕着外祖父展开话题,后来又聊到了战争,我凑到大人近前,竖起耳朵听着。 说起在里约和外祖父第一次相遇的情景,外祖母的眼睛都亮了。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学会葡萄牙语,她说,但埃迪只花了几周就掌握了英语。她说外祖父非常痴迷美国习语,即使他用得一团糟,外祖母也不忍心纠正他。凯思大姨想起外祖父有穿着内衣洗澡的习惯,她摇了摇头——据说这样能在沐浴的同时洗好内衣,这是外祖父在长期奔波中养成的习惯;只要打着高效的旗号,大姨说,什么事他都干得出来。蒂姆舅舅想起自己小时候,外祖父会跟所有人搭话,从服务员到街上的路人,舅舅总是被弄得很尴尬。他能跟任何人聊天,舅舅说,其他人笑着点了点头,从长辈发光的眼神中,我能感觉到他们非常尊敬外祖父。 我跟着长辈一起笑起来,要是自己能认识年轻时的外祖父该多好,过了一会儿,大家安静下来,从巴西过来的约泽夫堂舅讲起他父亲(也就是外祖父的大哥)的故事。我了解到,盖内克与妻子赫塔在战争期间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的劳改营。约泽夫堂舅告诉大家他是在营房里出生的,当时正值深冬时节,一到晚上,堂舅的眼睛就会被冻得睁不开,而他的母亲就会在转天早晨用温暖的乳汁将他的眼皮轻轻揉开,听到这些故事,我立刻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听到这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控制自己不要喊出那句你刚才说她干了什么。尽管这件事已经出乎了我的预料,其他人还是立刻打开了话匣子,每个故事都令人震惊:有哈利娜徒步穿越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壮举(而且还怀着孕);有在漆黑房间里举行的秘密婚礼;有伪造的身份证和为了掩饰割礼而进行的孤注一掷;有胆大包天的隔都越狱行动;还有逃出死亡草地的恐怖经历。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我现在才知道这些事情。然后我接下来的反应是:这些故事需要被记录下来。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后来记录这些故事的人就是我自己。晚上睡觉时我也没有把这段家族历史写成书的想法。当时我只有二十一岁,刚刚取得学位,全部精力都放在找工作和找房子上,我面对的是“现实生活”。过了将近十年时间我才踏上欧洲的土地,拿着一支录音笔和一个空白笔记本,开始采访亲朋好友,记录战争期间整个家族的经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怀着澎湃的心情渐渐睡去。我深受启发。被这些故事迷住。我有许多疑问,渴望找到答案。 我已经记不得那天离开门廊回房休息是什么时候——但我想起最后发言的是费利西娅,她是母亲的堂表亲里年纪最长的。我发现和其他人相比,她有些寡言内向。当长辈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时,费利西娅一脸严肃,态度谨慎。当她开口讲话时,她的眼神透出一丝哀伤。我了解到战争刚开始时她只有一岁,等战争结束时她已经长到八岁。战争的记忆依旧让她刻骨铭心,但分享那段经历让她不安。当然,好几年后,我才慢慢了解她背后的故事,不过当时的我就在想,无论她心中藏着怎样的回忆,那段往事一定十分痛苦。 “我们这一家人,”费利西娅的法国口音很重,她语气严肃,“本来不应该活下来。或者说不应该有那么多人活下来。”她停顿片刻,微风拂过房屋两旁的矮栎树,树叶沙沙作响。其他人都安静下来。我屏住呼吸,等待她接下来的解释。费利西娅叹了一口气,一只手捂住脖子,周围的皮肤仍然留有许多痘痕,我后来才知道,她在战争期间患上了坏血病,几乎因此丧命。“从许多方面来讲,我们能活下来就是个奇迹,”最后,她望着远方的树林说,“我们是幸运的。” 这句话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某一天,我迫切想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如何排除万难,我不禁想要寻找一切的答案。《我们是幸运的》这本书所描绘的,就是我的家族的生存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