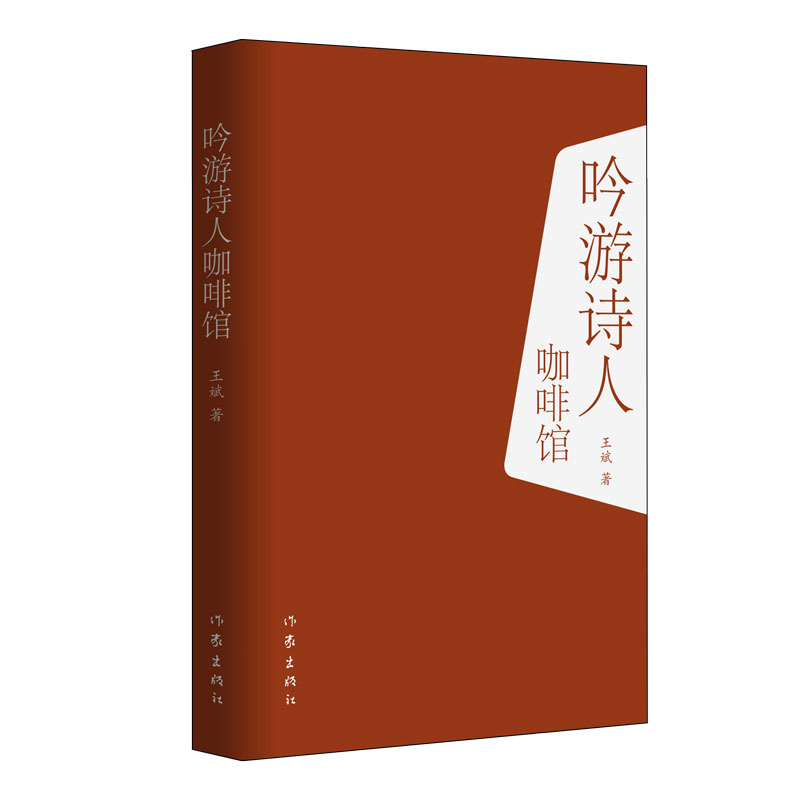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3.60
折扣购买: 吟游诗人咖啡馆(精)
ISBN: 9787521203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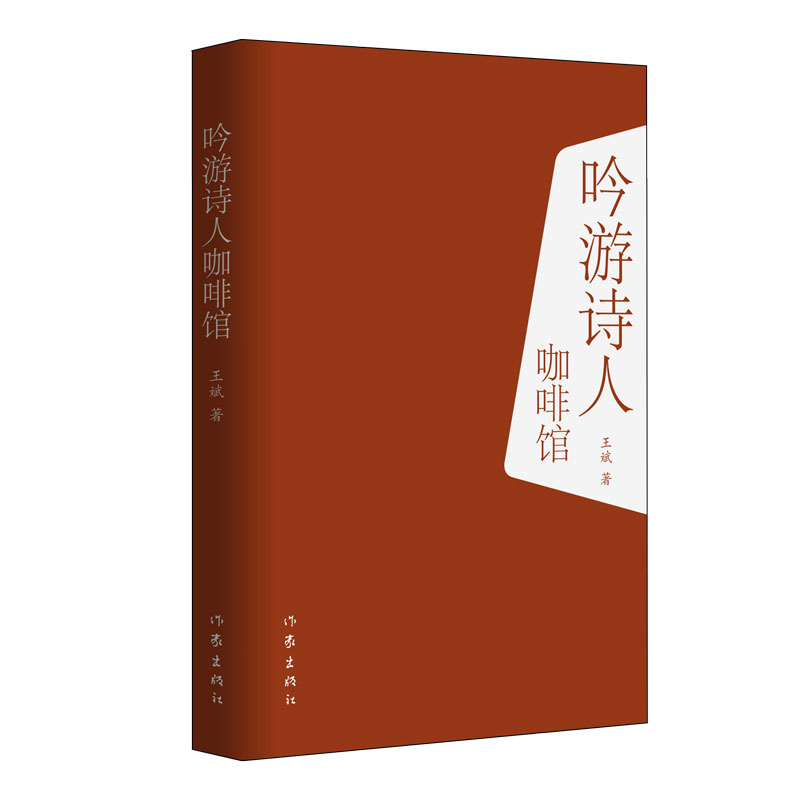
王斌,**作家、文学批评家、编剧。出版有长篇小说《六六年》《相遇的别离》《味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等,文化随笔集《城市符号》,散文集《逆风的逍遥》《思想的钟摆》《我的孤独与我无关》,纪实文学《活着·张艺谋》。策划与编剧的电影有《活着》《英雄》《霍元甲》《满城尽带黄金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漂亮妈妈》《千里走单骑》《十面埋伏》《青春爱人事件》《美人依旧》等。
一 又起霾了。 就像一个阴险的隐形人,肆无忌惮地向天空喷吐毒雾,而人们只能无奈而沉默地被迫吸纳。就这样,渐渐地它也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只能隐忍。 **前,还是澄澈碧蓝的天空,白云悠闲地飘浮着,空气清新如洗,转眼又见风息霾起了。铅灰色的雾霾,无边无涯地笼罩着这座庞然大物般的城市,浑浊、沉闷、压抑,让人感到窒息。彼时的萧朗,还没意识到这将又是一个浓重的雾霾之天呢。 昨晚入睡前,狂风尖厉地呼啸而起,从楼层的高处听来,就如同声嘶力竭的鬼哭狼嚎,又像是憋急眼的婴儿,在发出刺耳的声声啼哭,滚雷一般从广袤的地平线上碾过,地动山摇,宛若要将沉睡的城市连根拔起。 风声,啸声四起的风声,总会不经意地唤起萧朗心灵深处的某个记忆。那仿佛是久远的记忆了。 曾几何时,风声让萧朗记忆尤深。彼时,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萧朗总会瞪大双眼,仰望着黑的天花板,心存忧伤,耳闻风声嘶吼,狂啸不已。萧朗犹感在这么一个时刻,思绪亦像在风中无根飘零。 这时的萧朗,常会莫名其妙地陷入失眠。 他只能半夜爬起,披衣步入书房,揿亮台灯,然后打开了电脑。待坐定后,稍一闭目沉思,萧朗便觉心中涌荡的思绪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了起来,思若泉涌了。他捕捉着激流般向他迎面扑来的感觉,以文字呈现的形式,将它们快速地输入他的实名博客。在萧朗看来,那一个个争先恐后蹦跳而出的文字,亦如在风中飞扬狂舞。 后来,北京的风渐少了,那呼啸的风声也像在记忆中渐次远去,而漫无边际的雾霾,则变得越来越浓厚了。萧朗感到了莫名的惆怅。 是因为少了呐喊般的风声吗?还是因了那裹挟在风中的记忆—— 他记忆中名唤月光的女孩儿?萧朗当然知道,他在失眠之夜写下的那一篇篇随笔,其实是为了那个萦绕在他心中的,仿若悠长绵延的思念而写下的。那是他对遥不可及的月光的思念。虽然行文中萧朗似乎并没有这么明说,而*像是在追忆自己曾经以往的似水流年,但他心中其实是了然的,之所以陆续写下这些文字,皆是为了那个网名叫作月光的女孩儿。 彼时,萧朗心里知道,这个女孩儿一定会是他随笔的**个读者。她亦像是一位不会与他“失约”的知心挚友,总是奇迹般**个出现在他博客下的留言栏里。久而久之,便在无形中成了萧朗写下这些文字的潜在动力。萧朗有时甚至会觉得,他的这些随笔文字就像在以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向月光轻声倾诉着什么。那是什么呢—— 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是在这些经历中自己从中获得的某些人生感悟? 似是, 而又非是了! 萧朗以为,自己是在以这么一种方式向身在远方的月光,袒露着某种自己一时还梳理不清的心迹。而这个隐秘的心迹,萧朗从没向任何人提起过,自然也没对那个叫作月光的女孩儿说过。这就像是隐匿在他心间的不能向外人道及的秘密,而这份秘密,萧朗从不愿轻易地与别人一道分享。 只有自知了! 后来月光遽然消失了,如一阵风,在萧朗的记忆中留下了一道刻骨铭心的划痕。也就是从那时起,萧朗开始了他漫长且从未曾间断过的在博客上的随笔写作。在他的幻觉中,总觉得终究有那么**,月光又会突然出现在他的博客留言栏中。又是**个坐在“沙发”上的人,还像以往那般先跟他打个招呼。这一幻觉,竟然如此顽固地盘旋在萧朗的心头,以致像是成了他写作的灵感之泉。萧朗后来渐渐地觉察到了,原来他写下的这些文字,终归还是为了让遽然逝去身影的月光看的,虽然她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他仍在一如既往地向她诉说着心中的某种隐语。或者说,他在以一种别人所无法知晓的表达方式,在隐秘地告诉遥远的月光,目下的他,又在做些什么。 即使在月光消失后的那段日子里,萧朗的生活中也出现过一段男女间的小插曲,但萧朗依然觉得月光在他的心灵深处从未真正地消失过。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让萧朗不由得想起她来。萧朗想念她,也怀恋他们间曾共同拥有过的那一段美好的时光。这亦让萧朗感到了惊诧。毕竟他与她—— 月光,从未有过一次谋面之缘,甚至月光曾经示以的照片,亦是朦胧而又模糊的,也就是说,他甚至无法了然月光究竟长得什么样。可她就是犹如她的网名——月光那般,像在寂静夜晚的云雾中游弋的一钩明月,悬浮在他的心中,隐约照亮着他的生活。 哦,久违的北京的风,入夜后又骤然而起了。 就寝前,萧朗凝神聆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陷入冥想。那风声听上去一如往昔,让萧朗飘忽的记忆,以及裹挟在记忆中的那份隐而未显的感觉,再度被悄然地唤醒了。他为此又感到了一种无以言说的落寞和伤感! 深夜骤然而起的大风,还让萧朗误以为踯躅在城市上空的那层浓浓的阴霾,将会随着这骤然而至的狂风一扫而净呢,而明天,将迎来一个清朗的天空,云开雾散,蓝天白云,一轮艳阳高悬在天,普照大地。 萧朗多么希望能有这么一个怡人的阳光明媚的晴天,从而助他从一再陷入困境的思绪中走出,就如同有一道炫目的神光从天而降,**着他,步出晦暗的心境,走向澄明。但此刻笼罩着他的这份困顿之心境,就如同已将他笼罩在了烟雾弥漫的大海中,萧朗竟似看不见远去的飘洋过海的风帆了。 萧朗爱海,每每旅行到了海边时,他总会在天色破晓前,独自一人来到海边的沙滩上,盘脚坐下,静静地等候着海上日出,在霞光万丈的曙色中,远眺海平线上远去的风帆,心中涌动着一股永恒般的澄澈与辉煌。 目下的萧朗,好像深陷在了这重重的迷雾中,一时之间竟像是走不出来了。他为此在苦恼着。 清晨时分,萧朗从梦中兀自醒来了。睁开眼,脑袋一如往常地仍处在混沌的懵懂状态中。这一夜他显然是没睡好的。他习惯性地从枕边摸出了手表,仰脸躺着,迷迷糊糊地瞄了一眼:时间指向七点十分。他总在这样一个时辰自动醒来,渐成习惯了。 萧朗还是慵懒地赖在床上,浑身无力地又躺了一会儿,大瞪着呆呆的双眼,醒了醒神,这才起身穿好衣服,懒懒散散地来到窗前。他站住了,下意识地抬起了手臂,揉了揉惺忪迷离的双眼,然后拉开了厚厚的窗帘。 一道刺目的光线,就在这时激射了进来。萧朗这时见到了灰蒙蒙遮天蔽日的雾霾,远处的西山亦湮没在了帷幔般的雾霾之中。萧朗的心境,一下子如同这黏稠般的雾霾,暗沉了下来。萧朗预期中的**,应该是一个晴空万里的好天呢,因了昨晚睡前窗外刮起了大风。可期待还是落空了。已然泛青的树林在大地上纹丝不动,风止啸歇了。 难怪又起雾霾了呢,现在的北京,无风即霾呵!他不无沮丧地想。 鸡蛋、牛奶、面包和咖啡,这便是萧朗的早餐了。他日复一日以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打发着属于他的每一个清晨。然后呢?然后他会看一会儿闲书,品着咖啡,再听一会儿古典音乐。早晨适合听莫扎特或肖邦。这是他让自己的大脑放松的*好方式了。 这时的他,什么都不会去想,包括那篇让他深陷困境中的小说。萧朗的习惯是一旦陷入写作困境,就不让自己再去多想了,顺其自然地暂时将大脑放空,等待下一次重新进入写作状态时,再开始凝神思索,寻找新的突破点。奇迹有时就会如愿以偿地骤然降临。 这种写作方式让萧朗屡试不爽,有如天助。 二 远方的天边刚露出一抹曙色时,手机的闹钟就悦耳地响起了,发出一波波刺激耳鼓的声音。这是一首流行乐曲,悠扬而又激越,发出的声响亦是欢快的,仿佛在欣悦地应和着黎明的降临,但在昏睡中的远乔听来竟是那么的刺耳难受。她皱紧了小脸,倦怠地抬起了她纤细的手臂,从床头柜上摸索着找到手机,将闹钟止息了。 做下这一切时,远乔并没有睁开眼睛。 屋里又安静了下来。 远乔翻了一个身,脑袋斜倚在松软的枕头上。她想继续再眯瞪一会儿。昨晚睡得太晚了,她还是感到了难耐的困倦。尽管平时都是这个点儿准时被闹钟唤醒的,这已成了她生活中的一种按部就班的日常规律。但此刻,她还想再赖一会儿床,哪怕就只有那么一小会儿。 是的,就那么一会儿,远乔迷迷糊糊地想。 可没过多久,那个扰人的音乐声又再度响起了。远乔烦躁地又将身体翻转了过来,素面朝天,闭着眼愣了一会儿,然后不耐烦地抬起手来猛烈地拍了拍床,嘴里没好气地嘟囔了一句: “你讨厌!” 远乔睁开了眼睛。 这是一双红肿的眼睛,眼眶里布满了道道血丝,显然,她昨晚的确没睡好。难怪她那个不受控制的小脾气又犯了呢。 远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得不从床上坐了起来。这时她还是有点迷迷瞪瞪的,意识仍处在混沌状态。闹钟依然在不识趣地鸣响着。她不再去管它了,任由它一遍遍地催促着,就如同一人坐在她边上,自顾自地对着她固执地絮叨着,亦不管她愿不愿听。 远乔很不情愿地从床上爬了起来,然后将睡前摞着整整齐齐的衣物,一件件地抖开、套上身。远乔是一个爱整洁的人,甚至自认为还有点重复症式的洁癖。她喜欢生活在她的精心安置下,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秩序感,唯在此一“秩序”中,她才能获得一份惬意和释然,才能让远乔觉得她所在的这个世界的氛围,是由自己独自创作和编排的。这当然是远乔的一厢情愿,一种假想或曰幻觉。但远乔自己却并不这么看。远乔私下觉得,幻想与否其实并不重要,只有自己的感觉是真的便是好的。远乔就属于愿意生活在浪漫之幻觉中的那类人,仿佛眼见的一切都是经由她的刻意设计、修饰而调配好的,她在这其中可以自由自在地游刃有余。 三 八点半时,萧朗准点起身,离开了他居住的公寓。 他总是在这个时点背上双肩包(里面装着他心爱的苹果超薄十二寸笔记本电脑)离开家,奔向他选择且心仪的一家咖啡馆。 他不喜欢一人在家里闷头写作,喜欢在咖啡馆里写。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萧朗有时亦会下意识地扪心自问。哦,我可能是害怕孤独。他想。 孤独,一个人待在家里时的清冷、孤单,会让萧朗不由得萌生出一种茫然的寂寥之感。这种感觉时不时地会悄然地袭上心头,于无形中影响着他的情绪,以至潜在地又影响到了他的写作心境。 一个作家,孤独点不好吗? 每当莫名的孤独感向他袭来时,萧朗禁不住地会在内心深处追问自己一句。孤独?哦,他想,这个世界看上去色彩缤纷,包罗万象,仿佛无所不有,千奇百怪,马路上车水马龙,人流亦熙来攘往,在庞然大物般的都市里蠕动着,却予人以亦真亦幻的虚无感。 萧朗有时竟觉自己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讨厌待在众声喧哗的人群中,讨厌虚头巴脑的应酬和人际交往,那只会让他*加感到孤独。没事时他就喜欢一人待着,远离人群,远离市井的喧嚣,看书赏乐。他热爱哲学与文学,热爱古典音乐,其中他*爱的作曲家是马勒、肖斯塔科维奇、坎切利、古拜杜丽娜——毋庸置疑,他*喜欢的都是充满了苦难、悲伤的音乐,或者说他喜欢的都带有悲剧性的音乐类型,一如他喜欢的小说与戏剧乃是悲剧。他也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这是鲁迅先生对于悲剧的定义;还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论述,他认为悲剧是对人之灵魂的净化与陶冶。萧朗以为后者可能*符合他对悲剧的个人感受。是的,灵魂净化,他喜欢这个词汇,他亦知在那些悲伤哀婉乃至忧愤的文字与旋律中,他的灵魂得以升华,就像一场飓风暴雨荡涤着污浊的大地,洗尽铅华,把自己布满污垢的心灵濯洗了一遍似的。亦觉唯在这类作品中他方能感同身受,直击心灵。由此萧朗亦将这类作家、作曲家,视为自己的精神同类和知己。他对他们有一份深藏于心的感恩戴德。 萧朗还喜欢透过自家的玻璃幕墙,从高处俯瞰三环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真像是一只只失控的甲壳虫,在拥挤的大地上缓慢蠕动!萧朗有时会这么无边地遐想。他也喜欢看着楼下行色匆匆的行人像一波波忙着搬家的蝼蚁,以及小区院子里的孩子们欢快的嬉戏和玩耍。哦,我也有过如此天真烂漫的童年吗?可我时常会在人生旅途中将我的往昔岁月遗忘。遗忘了我天真无邪的童年。这时的萧朗,会不自觉地沉溺其间,触景生情,不无感慨地想起了自己曾有过的如诗如歌的童年往事,犹如他所见证的楼下的这群孩子的童年。每当此时,萧朗便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了油然而生的感伤。 萧朗时常这么出神地凝望着,渐渐地忘了自己,仿佛融化在了他所观望的人与景中。他就这么投入地远眺着,大脑竟是空荡荡的了。 他有些入迷了。 咖啡馆九时开门营业,他步行过去,正好要走上近半个小时。他喜欢清晨的闲散漫步,溜溜达达的,行走在喧嚣的大街上,一路上看着匆匆行走的路人和来来往往的车流。这是城市从睡梦中苏醒过来后*典型的景观了,萧朗想。他感到自己在那一刻,迅速地融入了这逐渐沸腾起来的生活激流之中。但他还是会感到一丝莫名的怅然。他有时亦喜悄然地观察擦肩而过的行人的表情,如同一个个移动的风向标,清晰地镌刻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征候。 咖啡馆的大门尚未打开。他看看表,还差四分钟到九点,显然是他抵达的时间提前了那么一丁点儿。隔着门框上镶嵌的透明玻璃,他能隐约见到咖啡馆内晃动的人影。那是早晨上班的服务生在提前打扫馆内的卫生呢。 他背过了身去,再次望向人来车往的大街。有不少人戴着口罩,神色木然僵硬地快步走过。他不紧不慢从兜里摸出一支烟,点上,悠悠地抽了起来。吐出的烟雾在空气中摇曳,又迅速地隐没了。 《吟游诗人咖啡馆》既是现实主义的经典叙事,又是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呈现。作品描述和塑造了这个时代隐身在喧嚣都市中的“吟游诗人”,宛若一曲诗意的咏叹调,探析当今生活中的人们所未知的某种情感之谜。 我始终是一名孤独而执着的写作者,一位试图探解人生无解乃至悖谬之谜的人。我只想像现下这样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因为写作之于我,不仅仅是人生的探索与解惑,*是一种自我的救赎,从而我认识了我自己。 ?????????????????????? ???——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