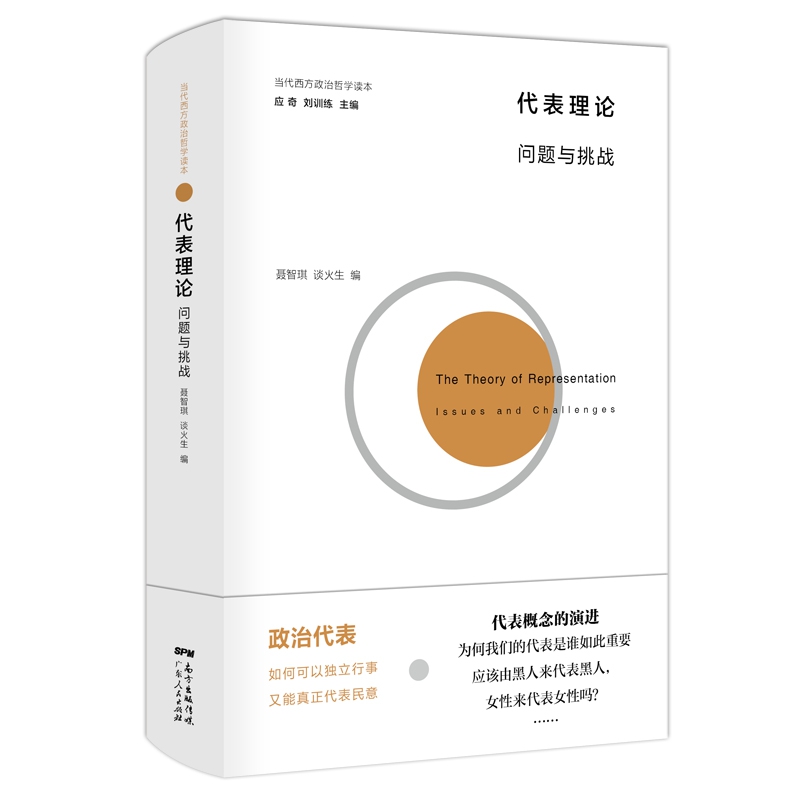
出版社: 广东人民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5.50
折扣购买: 代表理论(问题与挑战)(精)/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
ISBN: 97872181315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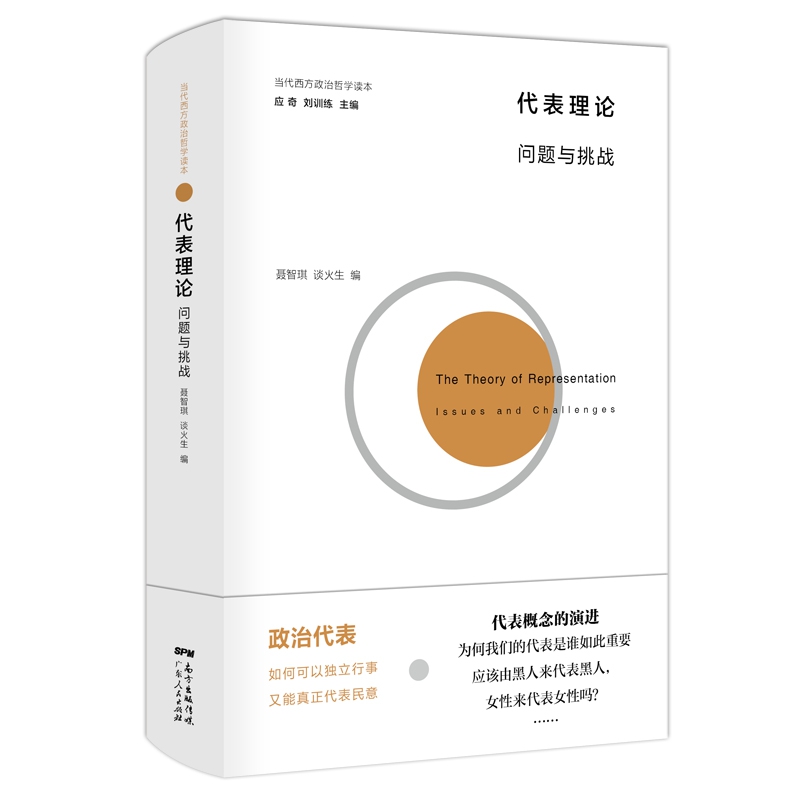
汉娜?费尼刀尔?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科学系名誉教授,在政治理论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学生,《代表的概念》是其代表作,刊行四十余年仍盛誉不减,此书使其获得了2003年度的有“政治学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斯凯特奖”。 娜迪亚?乌尔比娜提(Nadia Urbinati),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有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Principles and Genealogy、Mill on Democracy: From the Athenian Polis to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等著作。
在行动维度的代表理论中,有一个核心问题一直困扰着该理论:代表的角色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我们能希望代表干什么,代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理论家们“借用了大量的比拟性说法和状语性词语”,但并没有真正阐明代表的角色。理论家们会说,代表在行动之时是被代表者的代理人,站在被代表者的立场上,代替被代表者行动;他是以被代表者的名义,为了被代表者的利益,并与被代表者的愿望、意志或**保持一致;代表的行动是为了促进被代表者的福利,满足他们的需要,乃至于取悦被代表者,以使他们满意,感觉就像是他们自己在行动一样。理论家们还会说,代表就像是演员、代理人、大使、代理律师、特派员、副手、使者、外交特使、经销商、监护人、助理、诉讼代理人、管家、候补选手、*托人、代理主教……类似的说法太多了,而且每一个说法都有不同的内涵,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中进行选择时无从下手。 关于这些术语的理论讨论常常会使代表角色问题走向一种两极化模式,我将其称之为“指令与独立之争”(mandateindependence controversy)。这种模式可以用一种两分法的方式归纳如下:代表是应该(必须)按照选民的愿望来行动,还是应该(必须)按照他认为*佳的方式来行动?一方面,那些强调民众指令的理论家认为,代表的行动应该为了民众的利益,代表有义务按照选民的愿望行动,使其行动就像是选民自己在行动一样;另一方面,那些强调代表行动之独立性的理论家则认为,代表的行动应基于他自己的判断,他之所以被选为代表就是因为他具有特殊的能力,他的职责就是将通过他的转换,使选民们特殊而分散的需求凝聚成**的福利。 在某种意义上,“指令与独立之争”*令人吃惊之处在于,这一争论一直在持续,但却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双方的支持者们都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但各自的论证都是自说自话,缺乏真正的交锋,其结果就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有些学者将这一争论没有取得进展的原因归结为该问题的“规范性”特征,或者说,是由于它承载着“价值的负担”(valueladen)。根据这一判断,他们建议不要再在此问题上刨根问底了,应该满足于经验和历史的探究,看看代表们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即可。 但是,不幸的是,历史的和经验的证据同理论分析一样含混不清。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议员们*到授权的约束;但在另外一些时候,人们又期望他们能独立行动。在对当代的议员们进行调查时发现,有些议员支持指令的立场,有些议员则支持独立的立场;在对普通民众进行调查时,当他们被问到“您希望代表如何行动”时,同样出现了两极分化。 对代表进行概念分析的人认为,这种持续而似乎不可解的矛盾状态源于一个哲学悖论,源于“代表”概念本身含义的复杂性。将指令和独立这二者对立起来,这种方式本身就使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很难让人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研究和经验研究亦难以有所助益,因为它们会遭遇同样的困境,将概念本身的复杂性编织到欲探究的问题当中。很显然,指令与独立之争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混乱问题,它与现实政治行动和政治制度的一些重大议题关联在一起。但是,概念上的困难确实存在,而且,它还会影响我们明智地把握那些现实的议题。 我倒在行动维度的代表理论中,有一个核心问题一直困扰着该理论:代表的角色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我们能希望代表干什么,代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理论家们“借用了大量的比拟性说法和状语性词语”,但并没有真正阐明代表的角色。理论家们会说,代表在行动之时是被代表者的代理人,站在被代表者的立场上,代替被代表者行动;他是以被代表者的名义,为了被代表者的利益,并与被代表者的愿望、意志或**保持一致;代表的行动是为了促进被代表者的福利,满足他们的需要,乃至于取悦被代表者,以使他们满意,感觉就像是他们自己在行动一样。理论家们还会说,代表就像是演员、代理人、大使、代理律师、特派员、副手、使者、外交特使、经销商、监护人、助理、诉讼代理人、管家、候补选手、*托人、代理主教……类似的说法太多了,而且每一个说法都有不同的内涵,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中进行选择时无从下手。 关于这些术语的理论讨论常常会使代表角色问题走向一种两极化模式,我将其称之为“指令与独立之争”(mandateindependence controversy)。这种模式可以用一种两分法的方式归纳如下:代表是应该(必须)按照选民的愿望来行动,还是应该(必须)按照他认为*佳的方式来行动?一方面,那些强调民众指令的理论家认为,代表的行动应该为了民众的利益,代表有义务按照选民的愿望行动,使其行动就像是选民自己在行动一样;另一方面,那些强调代表行动之独立性的理论家则认为,代表的行动应基于他自己的判断,他之所以被选为代表就是因为他具有特殊的能力,他的职责就是将通过他的转换,使选民们特殊而分散的需求凝聚成**的福利。 在某种意义上,“指令与独立之争”*令人吃惊之处在于,这一争论一直在持续,但却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双方的支持者们都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但各自的论证都是自说自话,缺乏真正的交锋,其结果就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有些学者将这一争论没有取得进展的原因归结为该问题的“规范性”特征,或者说,是由于它承载着“价值的负担”(valueladen)。根据这一判断,他们建议不要再在此问题上刨根问底了,应该满足于经验和历史的探究,看看代表们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即可。 但是,不幸的是,历史的和经验的证据同理论分析一样含混不清。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议员们*到授权的约束;但在另外一些时候,人们又期望他们能独立行动。在对当代的议员们进行调查时发现,有些议员支持指令的立场,有些议员则支持独立的立场;在对普通民众进行调查时,当他们被问到“您希望代表如何行动”时,同样出现了两极分化。 对代表进行概念分析的人认为,这种持续而似乎不可解的矛盾状态源于一个哲学悖论,源于“代表”概念本身含义的复杂性。将指令和独立这二者对立起来,这种方式本身就使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很难让人满意。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研究和经验研究亦难以有所助益,因为它们会遭遇同样的困境,将概念本身的复杂性编织到欲探究的问题当中。很显然,指令与独立之争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混乱问题,它与现实政治行动和政治制度的一些重大议题关联在一起。但是,概念上的困难确实存在,而且,它还会影响我们明智地把握那些现实的议题。 我倒愿意认为这是事实,但令人吃惊的是,争论的双方常常真的是求助于概念上的界定。他们拒**方的立场,似乎对方的立场理所当然地与代表的实际状况及其含义无法相容。站在指令立场上的人会说,如果代表所为老是与其选民的愿望相违背,那他就不是真正的代表;这样的人即使仍有正式的代表身份,他也并没有真正代表选民,徒有其表,并无其实。同样,那些站在独立立场上的人会反驳道,如果代表毫无按照自己独立的判断来进行决定的自由,而仅仅只是其选民的一个傀儡,根本不能采取真正的行动,那他真的不能算是代表。如果选民们想要直接采取行动,将代表当做一个毫无生命的工具,那么代表就不是真正的代表,这就像我在拾起地上的一只铅笔时,说那只手在代表我行动一样。尽管一个代表不采取任何行动也能作为一个符号或基于描述意义上的相似性而成为选民的象征,但就我们此处所关心的行动意义上的代表而言,他是不称职的。 面对这种局面,有人可能会认为双方都有一定道理。一个代表如果其行为和选民毫无关联,他不能算是代表;如果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行动,那他也不能算是代表。当然,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在形式上可能仍是某个群体的代表,但其实质已然流失。但这两种似乎无法相容的立场怎么可能同时为真呢?前文已述,在某种意义上“代表”*核心的内涵是使人或物呈现出来,而无需他/它真正在场。我相信这个自相矛盾的要求——它要求一个东西既出现又不出现——就是“指令与独立之争”中一再出现的问题所在。那些支持指令立场的理论家们努力向我们证明,除非缺席之物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真的出现,否则无物能被称为代表。如果代表的行为与其选民的需求、利益、愿望或福利没有任何真正的关联,乃至与之相冲突,那么,他的行为是无法将选民的需求、利益、愿望或福利呈现出来的。而那些支持独立立场的理论家们则一再强调,如果缺席之物真的出现,自己代表自己,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被称为代表了。它只能通过某种中介之物呈现出来,它必须在某种意义上保持缺席状态。除非代表有足够的独立性,可以自由地采取行动,否则,其选民就无法被代表,而仅仅是在行动中被呈现出来。愿意认为这是事实,但令人吃惊的是,争论的双方常常真的是求助于概念上的界定。他们拒**方的立场,似乎对方的立场理所当然地与代表的实际状况及其含义无法相容。站在指令立场上的人会说,如果代表所为老是与其选民的愿望相违背,那他就不是真正的代表;这样的人即使仍有正式的代表身份,他也并没有真正代表选民,徒有其表,并无其实。同样,那些站在独立立场上的人会反驳道,如果代表毫无按照自己独立的判断来进行决定的自由,而仅仅只是其选民的一个傀儡,根本不能采取真正的行动,那他真的不能算是代表。如果选民们想要直接采取行动,将代表当做一个毫无生命的工具,那么代表就不是真正的代表,这就像我在拾起地上的一只铅笔时,说那只手在代表我行动一样。尽管一个代表不采取任何行动也能作为一个符号或基于描述意义上的相似性而成为选民的象征,但就我们此处所关心的行动意义上的代表而言,他是不称职的。 面对这种局面,有人可能会认为双方都有一定道理。一个代表如果其行为和选民毫无关联,他不能算是代表;如果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行动,那他也不能算是代表。当然,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在形式上可能仍是某个群体的代表,但其实质已然流失。但这两种似乎无法相容的立场怎么可能同时为真呢?前文已述,在某种意义上“代表”*核心的内涵是使人或物呈现出来,而无需他/它真正在场。我相信这个自相矛盾的要求——它要求一个东西既出现又不出现——就是“指令与独立之争”中一再出现的问题所在。那些支持指令立场的理论家们努力向我们证明,除非缺席之物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真的出现,否则无物能被称为代表。如果代表的行为与其选民的需求、利益、愿望或福利没有任何真正的关联,乃至与之相冲突,那么,他的行为是无法将选民的需求、利益、愿望或福利呈现出来的。而那些支持独立立场的理论家们则一再强调,如果缺席之物真的出现,自己代表自己,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被称为代表了。它只能通过某种中介之物呈现出来,它必须在某种意义上保持缺席状态。除非代表有足够的独立性,可以自由地采取行动,否则,其选民就无法被代表,而仅仅是在行动中被呈现出来。 政治代表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的关键理念和制度。**理想的落实全在代议制度的设计和实践上。政治代表如何可以独立行事,又能真正代表民意?西方政治代表理论遭遇的问题与挑战,将得以一一澄清和梳理,《代表理论:问题与挑战》是西方政治代表理论不可多得的入门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