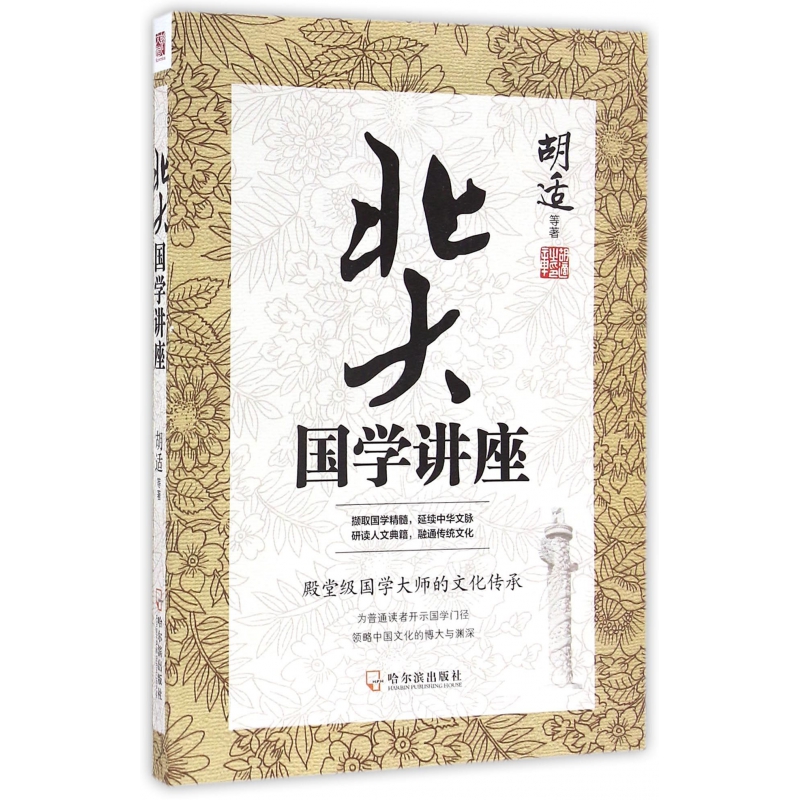
出版社: 哈尔滨
原售价: 39.80
折扣价: 23.48
折扣购买: 北大国学讲座
ISBN: 97875484289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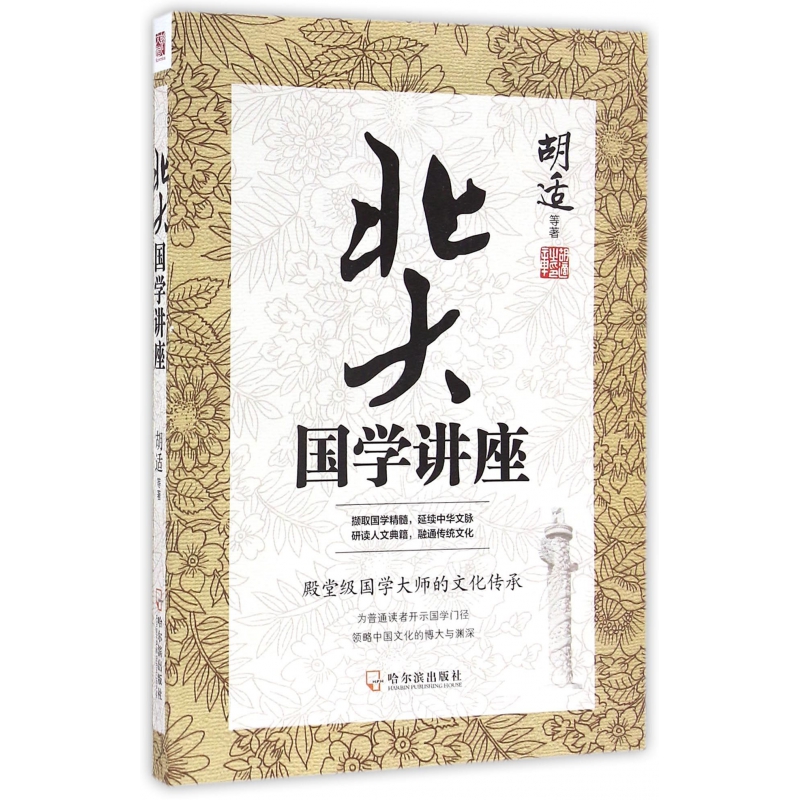
国学之进步 中国学术,除文学不能有绝对的完成外,其余的 到了清代,已渐渐告成,告一结束。清末诸儒,若曾 国藩、张之洞辈都以为一切学问,已被前人说尽,到 了清代,可说是登峰造极,后人只好追随其后,决不 再能超过了。我以为后人仅欲得国学中的普通学识, 则能够研究前人所已发明的,可算已足,假使要求真 正学问,怕还不足罢!即以“考据”而论,清代成就 虽多,我们依着他们的成规,引而伸之,也还可以求 得许多的知识。在他们的成规以外,未始没有别的途 径可寻,那蕴蓄着未开辟的精金正多呢!总之,我们 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非但守着古人所发明 的于我未足,即依律引申,也非我愿,必须别创新律 ,高出古人才满足心愿。这便是进步之机。 我对于国学求进步之点有三: 一、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 二、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 三、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毕竟讲来,文 学要求进步,恐怕难能呢? 清代治经学较历代为尤精,我在讲经学之派别时 已经讲过。我们就旧有成规再加讲讨,原也是个方法 。不过“温故知新”仅“足以为师”,不足语于进步 。我们治经必须比类知原,才有进步。因前人治经, 若宋、明的讲大体,未免流于臆测妄断;若清代的订 训诂,又仅求一字的妥当,一句的讲明,一制的考明 ,“擘绩补苴”,不甚得大体。我们生在清后,那经 典上的疑难,已由前人剖析明白,可让我们融会贯通 再讲大体了。 从根本上讲,经史是决不可以分的。经是古代的 历史,也可以说是断代史。我们治史,当然要先看通 史,再治断代的史,才有效果,若专治断代史,效果 是很微细的。治经,不先治通史,治经不和通史融通 ,其弊与专治断代史等,如何能得利益?前人正犯此 病。所以我主张比类求原,以求经史的融会,以谋经 学的进步。如何是比类求原?待我说来!经典中的《 尚书》《春秋》,是后代“编年”“纪传”两体之先 源。刘知幾曾说“记传”是源于《尚书》,“编年” 是源于《春秋》,章学诚也曾说后代诸史皆本于《春 秋》。这二人主张虽不同,我们考诸事实,诸史也不 尽同于《尚书》《春秋》,而诸史滥觞于彼,是毫无 疑义的。所以治经:对于“制度”,下则求诸《六典 》《会典》诸书,上以归之于《周礼》《仪礼》。对 于地理,下则考诸史及地舆志,上以归之于《禹贡》 及《周礼·职方志》。即风俗道德,亦从后代记载上 来源于经典。总之,把经看作古代的历史,用以参考 后世种种的变迁,于其中看明古今变迁的中心。那么 ,经学家最忌的武断,琐屑二病,都可免除了。未来 所新见的,也非今日所可限量呢! 中国哲学在晋代为清谈,只有口说,讲来讲去, 总无证据。在宋、明为理学,有道学问、尊德性之分 ,自己却渐有所证。在清代专在文字上求,以此无专 长者,若戴东原著《孟子字义疏证》,阮芸台讲性命 ,陈兰甫著《汉儒通义》,也仅在文字上求、训诂上 求,有何可取!要知哲理非但求之训诂为无用,即一 理为人人所共明而未证之于心,也还没有用处的,必 须直观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王阳明辈内证于心, 功夫深浅各有不同,所得见解,也彼此歧异,这也是 事实上必有的。理,仿佛是目的地,各人所由的路, 既不能尽同,所见的理,也必不能尽同;不尽同和根 源上并无不合呢!佛家内证功夫最精深,那些堕落的 就专在语言文字上讲了。西洋哲学,文字虽精,仍是 想象如此,未能证之于心,一无根据,还不能到宋学 的地步,所以彼此立论,竟可各走极端的。这有理论 无事实的学问,讲习而外,一无可用了!近代法国哲 学家柏格森渐注重直觉,和直观自得有些相近了。总 之,讲哲理决不可像天文家讲日与地球的距离一样, 测成某距离为已精确了。因为日的距离,是事实上决 不能量,只能用理论推测的,那心像是在吾人的精神 界,自己应该觉得的。所以,不能直观自得,并非真 正的哲理,治哲学不能直观自得便不能进步。P33-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