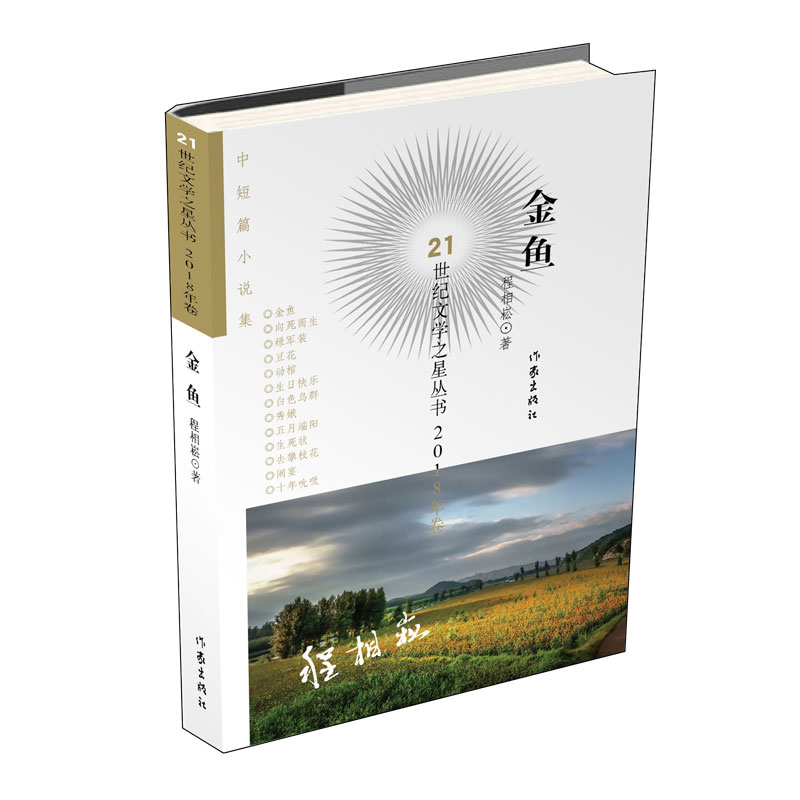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39.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金鱼/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ISBN: 9787521205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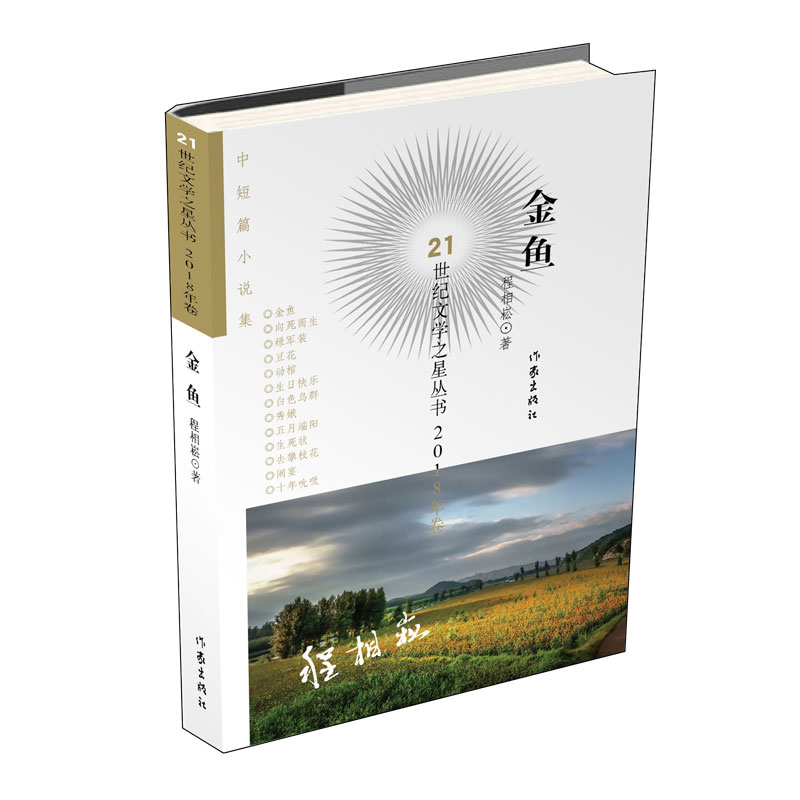
程相崧,山东金乡人。十六岁开始发表作品,至今累计发表小说、散文一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作家》《山花》《钟山》《大家》《西湖》《青年文学》《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纯文学期刊,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推介,有作品入选漓江版年度选本。
金 鱼 一 我开车回家接母亲时,她正在翻箱倒柜找那条金鱼。 她佝偻着背,把满是银发的脑袋埋进一口纸箱,双手紧张地扒拉着。那纸箱在家里保存了足有二三十个年头了,表面的牛皮纸已经泛白,上面还印刷着玫瑰牌缝纫机的机头和机身图案。从侧面看上去,母亲的样子有些滑稽,仿佛一个贪婪的人在挖掘着什么宝藏。实际上,箱子里满满的都是金鱼,她在从金鱼里找金鱼,就像从万千人海中找到她需要的那一个。那是一种用输液器上的输液管和调速轮做成的小玩意儿,式样各异,大小不一,全是母亲的杰作。年长日久,有些还能保持着透明的颜色和柔软的质地,有些已经被空气氧化泛黄。它们中的大多数,柔软的尾巴变得坚硬,上面剪出来的螺旋也没了弹性。它们是我和姐姐小时候的玩具,也是村里小伙伴们的最爱。因为它们,我和姐姐拥有着村里孩子们人人羡慕的好人缘儿。母亲一辈子编织过多少条这样的金鱼,我肯定数不清,毫不夸张地猜测,也有几千条上万条吧?母亲每一次出门,身上总要佩戴一条金鱼,从我记事起就是如此。有时候别在胸前,有时候挂在手链上,有时候当作项链坠儿。 “你忘了吗?就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玩儿的那条塑料金鱼啊,白色的身子,红色的眼睛。”母亲说。 我慢慢想起它来,眼前也浮现出最后一次看见它的情景。那应该是我少年时代的某个傍晚,在收拾文具和课本时,偶然发现它躺在抽屉的角落。我也许朝它瞥了两眼,也许没有。我敢肯定的是,那时候,自己就已经有些拿不准还能不能把它叫作金鱼。那条金鱼跟它的同类相比,并没什么奇特之处,我钟爱它,只是因为母亲把它视若珍宝。母亲说,那是她学会这门手艺之后编织的第一条金鱼,所以,她把它用红绸子包起来,放在了衣柜里。我在一次母亲换衣服的时候发现了它,并趁她不备,据为己有。当然,母亲发现之后,又把它悄悄收好,放了回去。我跟母亲为此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拉锯战。最终,母亲放弃了。在摆弄着它度过了童年和少年之后,我为难地不知该怎么称呼它。可是,不叫金鱼又能叫什么呢?谁也不能否认,它在刚刚编织成形时,的确是一条金鱼,一条精美的手工 金鱼。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母亲从年轻时候就喜欢编织,准确说是编织金鱼。她编织出来的金鱼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在我小时候,家中的这种金鱼已经盛满了两个大纸箱。只要能找到合适的材质,她就会不停地编织金鱼。她不分昼夜编织金鱼的那种架势,让人不得不怀疑,她是否已经打算以此为生。当然,在以后的日子,她并没有卖出去其中的一条两条,却因此被大家公认为心灵手巧。她不仅把自己编织出来的金鱼佩戴在自己身上,还做成小饰物,挂在父亲的钥匙链上;做成流苏,坠到我的皮帽子上;甚至做成耳坠,挂到姐姐耳朵眼儿上。 在村里,几乎所有人家的孩子,小时候都拥有过一到两条她编织的金鱼。他们拥到我们家,手里拿着输液管或者买来的塑料皮管,在母亲面前排起长队。母亲坐在堂屋门口的竹椅上,手里拿着剪子和小刀,脚下落满剪下来的碎屑。只要她心情不坏,或者不愿到镇上赶集,就会一整天乐此不疲。 那时候,在我们村,母亲除了喜欢编织金鱼,喜欢赶集是出了名的。每次赶集,她都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小姑娘。她早早起床,先从柜子里取出那块古色古香的花纸包着的檀香皂,放在洗脸架上。我跟姐姐趁她出去打水的当儿,总要把鼻子凑到上面,猛吸一口气。嗅完之后,姐姐会高傲而鄙夷地望我一眼,我则会惭愧而绝望地低下头去。因为,母亲说,臭男人一辈子只配用罗锅。这意味着,姐姐只要好好长大,迟早会用上这梦寐以求的檀香皂,而我却永远没有机会。母亲用檀香皂洗了脸,擦干,就会拿出那包牡丹牌雪花膏,挤在手心一点儿,然后往两腮沾一沾,额头沾一沾,再整张脸抹匀。母亲的脸光滑,涂上一遍,亮亮的,香香的。 母亲洗完脸,抹上雪花膏,就开始梳头。母亲的头发很长,一直到四十多岁都扎着大辫子。母亲先把睡了一夜有些发毛的辫子解开,让姐姐给她梳。梳头时,她会让我站在身边,帮她拔去出现在里面的白发。母亲对她的白发毫不留情,心狠手辣,恨不得斩草除根而后快。我总会趁着这机会,偷偷拔去她几根黑发。 母亲辫好辫子,换上那件天蓝色的卡其布褂子,穿上那件浅咖啡色裤子和那双半高跟皮鞋,便出门去了。母亲到镇集上之后,菜市上看看,布摊上瞧瞧,再到供销社大楼去逛逛。她做完这些,就要一个人去镇卫生院了。 她去镇卫生院不干别的,就是到那门前的沟里去捡废旧输液管。那时候,医院废旧医疗器械回收管理还很松懈,针头针管经常随随便便就倾倒了。那里堆满垃圾,常有捡拾废旧物品的老头老太太光顾。一身光鲜的母亲置身那种环境,总能引来路人奇异的目光和小声的议论。母亲旁若无人,把那些脏兮兮的输液管塞进随身带来的提兜,脸上还带着满足的微笑。在捡废品的老头老太太们充满仇恨的目光中,她每次总要来回逡巡两圈,才恋恋不舍骑上车子离开。 她带回那些针管,总要先用清水冲洗,再用沸水消毒,接着,分门别类晾干放好。餐前饭后,母亲的脸上活泛起来,家里的气氛也好了许多。那些管子在母亲手指间蹦跳着,拉长,穿插,环绕,就像老太太们纳鞋底时手里的麻绳,就像年轻妇女打毛衣时手中的毛线。有时候,材料紧缺,她也会用其他东西代替。例如麦秸秆、谷子秸秆,甚至干枯的地瓜秧。但是,她改用这些材质时,兴致明显大减,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她会停下来,把纸箱里那一条条编织好的金鱼倾倒在床上,捡起来,托在手心欣赏,或者挑拣出不如意的,拆开重新编织。 那时候,我健壮如小牛犊,皮实得像个石头孩子,为此,经常感觉愧对母亲。我真想得上一场大病,挂上一两回吊瓶,好让母亲能够及时用到新鲜的材料。记得第一次打吊针是在十一岁那年。我得了腮腺炎,脸肿得像气球,涂满黄色的药膏。村里的赤脚医生王喜云给我挂了吊瓶。起了针,在手背的隐隐疼痛中,我看见母亲欢喜地捡起了那条输液管儿。这样的事情多年以后在我的儿子身上重演。前些年,母亲住在城里,帮我照顾着儿子。儿子第一次挂吊瓶。母亲照看着孙子,眼睛却紧盯着那还在滴着液体的针管。儿子的吊瓶刚打完,母亲就抢先一步,接过护士手中的输液器。那脸上的表情,是满足,不,简直是欢天喜地。 这些小说由乡野写实出发,力图抵达对人的现代乃至后现代境遇的洞察和想象。在展现乡土农村的物质与精神的裂变后,引发出对于自我生存困境的追问和思考。其中,反应都市人生活困境和情感危机的内容,则可以看到当下各色人等的困惑和纠结。小说基于真实、传统和现代三个层面,来书写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人文遗落,所呈现的无疑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缩影。它有着复杂的形态,体现了人的精神回归和对信仰的呼唤与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