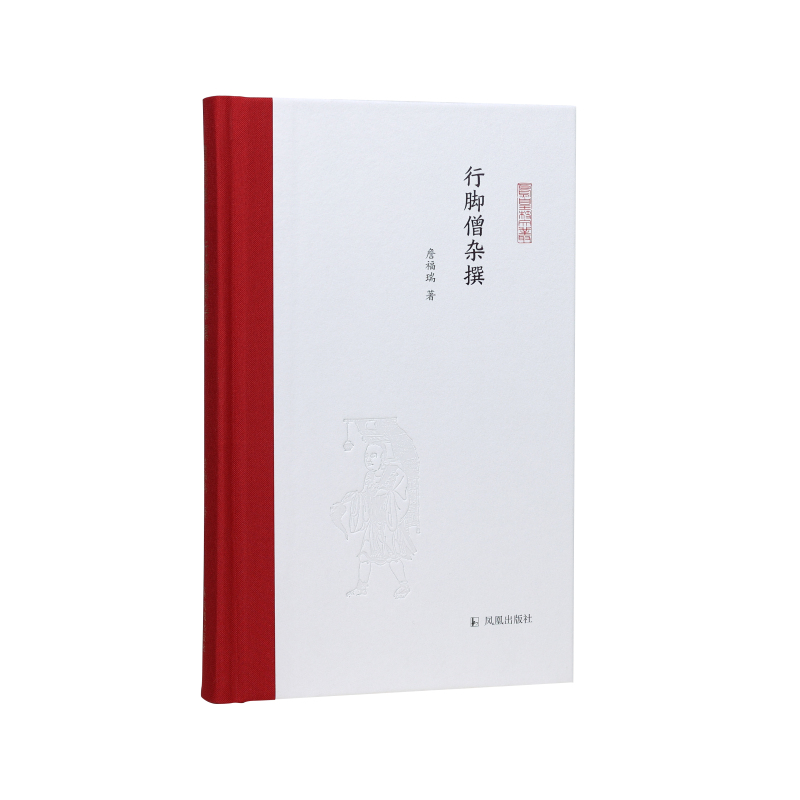
出版社: 凤凰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3.60
折扣购买: 行脚僧杂撰(凤凰枝文丛)
ISBN: 97875506430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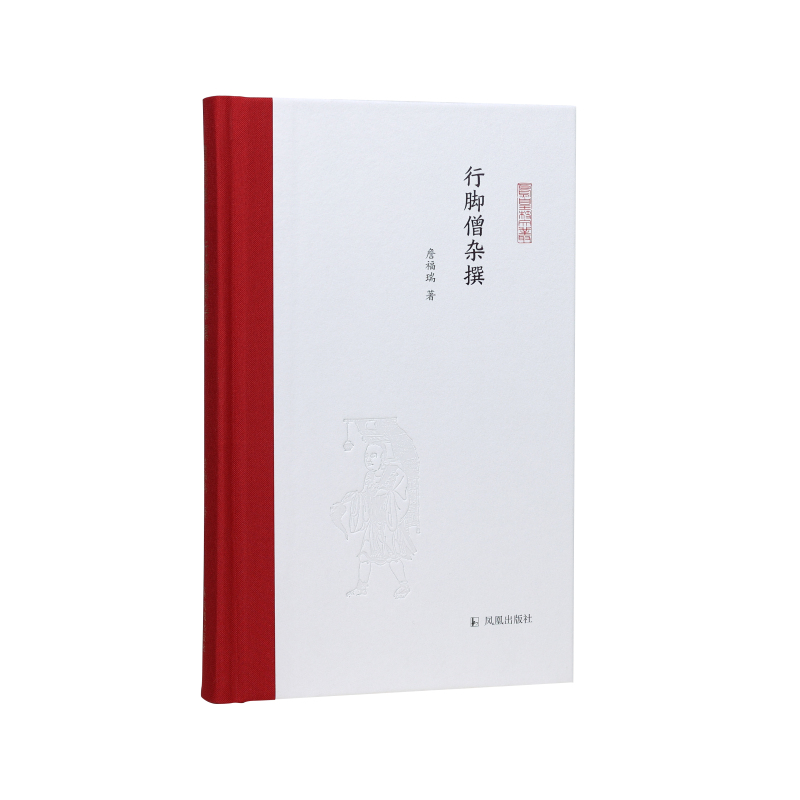
詹福瑞,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导。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第四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 长,中国《文心雕龙》研究会会长。在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唐诗研究和李白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出版有《南朝诗歌思潮》《论经典》《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合 著)、《李白诗全译》(合著)等著作多种,组织整理出版“唐诗选本丛书”多种。
第一辑 问道学文 詹锳先生的学养与治学路径 业师詹锳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文研究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詹锳先生研究李白与《文心雕龙》,注重文献整理、作家与诗文考证,《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和《文心雕龙义证》,融乾嘉朴学研究方法与现代科学态度为一体,为学界的李白和《文心雕龙》研究提供了厚重的基础性研究成果。而他的《〈文心雕龙〉的风格学》《刘勰与〈文心雕龙〉》两部著作,又借镜欧美现代美学观点与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掘和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与王元化先生的研究路数极为接近,成为《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一派。詹锳先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第二代学人的代表,梳理并研究詹锳先生的治学路径与研究特色,相信不仅可以教益同门师生,也可从学术史的视野一窥那一代学人走过的道路及其形成的学术传统。 转益多师——“我是个开杂货铺的” 詹锳先生谈到自己的治学思想时说过一段这样的话:“我一生所学可称得上是个杂货摊。……我的知识是大杂烩,不取一家之言,也不是从一个角度出发,我希望能做到实事求是,能采取各家之长。”看似自谦,其实是夫子治学自道。证明詹锳先生那个时代的学风是开放的,他们所接受的是兼容并蓄的知识体系,形成学术素养自然也是自由探索的。 詹锳先生五岁上私塾,读《四书》《诗经》《左传》《唐宋八大家古文》等。他没上过小学,直接考入中学。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二年转入中国语言文学系。七七事变之后,北京大学南迁昆明,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大。詹锳先生随校到昆明求学。詹锳先生先后就学于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遍受名师指导。在北京大学时,他从赵万里先生修史料目录学,从余嘉锡先生修目录学,从郑天挺先生修校勘学,从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学习语言学、音韵学,还在罗常培先生的指导下翻译了法国汉学家马伯乐(Maspero)所著的《唐代长安方言》的下半部。从胡适、罗庸、闻一多修古典文学。在西南联大,他有幸又听了原清华大学陈寅恪、钱穆、刘文典、朱自清、冯友兰诸先生的古典文学、史学和哲学课。他曾向陈寅恪学元白诗,向闻一多学《诗经》,向刘文典学《庄子》,向朱自清学陶诗,向罗庸学杜诗。除中国文学,詹锳先生对外国文学也很感兴趣,学习英语之外,还连续学习了3年法语,旁听过英国小说,并从梁实秋修莎士比亚戏剧。从詹锳先生所选课程看,20世纪30、40年代的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校风开放,学风也是自由的,学生可以自主选课,而教师为学生开设的课程看起来五花八门,实则既坚持传统,又广纳新学。这样的校风和学风,不仅为学生搭建了科学的多元知识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潜移默化地使学生树立起不拘一格、自由探索的精神气质。 1939年7月,詹锳先生曾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西南联大时期的文科研究所前身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是北京大学所设文史哲科研与研究生培养的学术机构,初创于1918年,1921年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称北京大学研究所文史部,1934年始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其研究范围大致包括历史与考古、文学与语言、哲学等领域。七七事变后,北大西迁,与清华、南开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文科研究所业务中断。根据《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记载,1939年5月27日,傅斯年到北京大学,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自任主任,并请郑天挺出任副主任。导师有罗常培、李方桂、丁声树、唐兰、罗庸、杨振声、汤用彤、陈寅恪、姚从吾、向达、郑天挺、贺麟等。研究生招生分两批。第一批招生名额为10名,截至7月15日接收论文27篇,也就是说有27人报名。经两轮审查进入初审及格名单的10人:桑恒康、杨志玖、汪篯、傅懋 、陈三苏、马学良、王丰年、逯钦立、詹锳、周法高。8月5日考试,最后考试结果,10人中只有詹锳先生未被录取。第二批研究生准考者有王明、王叔岷、任继愈、翁同文、刘念和、阎文儒、阴法鲁7人。经9月15日笔试,9月16日口试,参加考试的7人,除了翁同文没有参加英语考试之外,其余6人,全部录取。詹锳先生未被录取的原因,他自己从未提及。任继愈先生与我说,文科研究所1939年招生,科目分史学、语学、中国文学、考古、人类学五部分,修业期限两年。出人意料的是,詹锳先生报考的不是自己所学的语言、中国文学,而是史学。面试的主考官就是陈寅恪先生。考生信心满满,考官也丝毫不让。考官问一题,考生答一题。你来我往,直到把考生问到无言以对。任继愈先生分析,詹锳先生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却去报考史学研究生,可见詹锳先生年轻时过于自负,而这也正是陈寅恪先生问倒詹锳先生的原因吧。詹锳先生报考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失利这件事情,不只反映出他年轻气盛的性格,还可据此了解到詹锳先生的学术观念。在詹锳先生的心中,也许本来就没有历史与文学学科的藩篱,所以鼓足勇气去闯陈寅恪先生这道大关,这也印证了他治学“开杂货铺的”风趣比喻。 1948年8月初,詹锳先生赴美留学。先进入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半年后转入教育心理学专业,1950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心理学,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心理学的导师就是美国教育心理学之父桑代克(Edward Lee Thomdike)的儿子小桑代克和其高足盖茨·洛奇(Gates Lorge),又向Aeten Watker学习统计学,1953年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1953年7月回国后,在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前身)教育系任心理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心理学教学与研究,发表一系列心理学论文,尤其对巴甫洛夫的心理学有深入研究。另外,与人合译了鲁季克(Pyduk)的《心理学》,1959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1958年心理学被打成“伪科学”,成了批判的对象,詹锳先生于1961年调到中文系,回到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当时的美国,心理学属于自然科学,这是詹锳先生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特殊之处。 詹锳先生读书的年代,正处于中国社会激烈动荡之时,他的学习过程充满颠沛与艰辛。但不幸中亦有幸运,那就是在旧学向新学转型之际,他遇到了一批旧学新学兼修、中西贯通、满腹经纶的学术巨擘为师,他自身所受的教育也是新旧、中西俱备。所以其后从事学术研究,既非轻弃传统,亦不盲目排外,同时亦不迷信洋人,迷信权威,呈现出开放的、兼容并包的姿态。 把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文史 詹锳先生为学,尚无征不信。这种治学观念,既有乾嘉学派的基因,也融入了五四以来学术界崇尚的科学实证精神。 乾嘉学派做学问,提倡汉学,疏离宋学,以考证问题为主,立义必凭证据,推求本原,实事求是,不为空谈。钱大昕说:“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 一位当代学者十年来在学术道路上的努力前行和心路历程